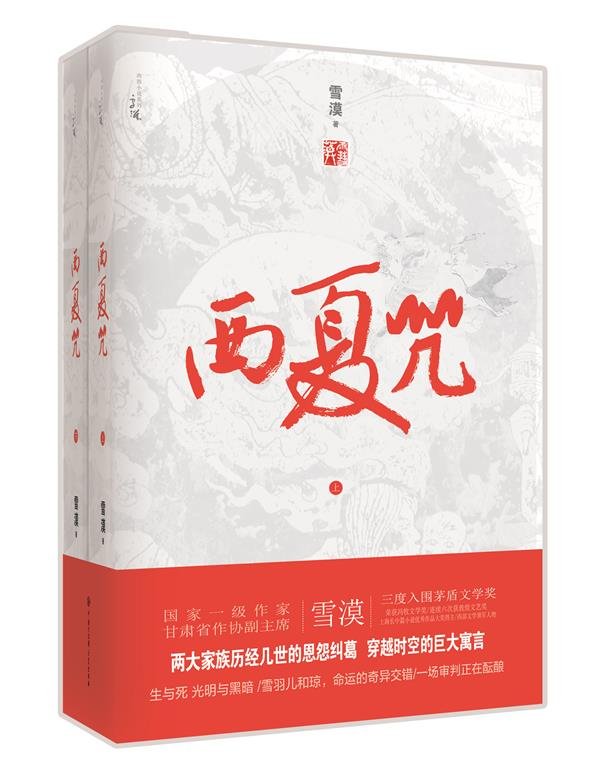
《西夏咒》 雪漠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灵魂的流淌——《西夏咒》番外篇(上)
雪漠
沿着漫长的时空隧道,
我苦苦寻觅。
我历经汉唐的繁华,
我沐浴明清的烟雨,
生命的扁舟,
在生死中漂泊不已。
岁月的大风强劲地吹来,
吹走我一个个躯体,
却掠不去灵魂的寻觅。
1
春天,醒来了,这是个恋爱的季节,缠绵而又充满了诗意。如《拜月的狐儿》中的那些情诗,里面的爱情多美,美得令人心碎;也如书中的那些道歌,道出了世上的沧桑变化和诗意。
不过,我的那些小说,虽也有浪漫,但总是在浪漫中显得沉重,有时,还沉重得如一座座大山,令人望而却步。即使偶尔调侃一下,也像那骆驼的叫声,即使在笑,却也像沉重的叹息。没办法,这也是基因所致。
2000年,《大漠祭》出版之后,我就开始了《西夏咒》的创作。同时创作的,还有《猎原》《白虎关》等。其实,我的很多小说都是同步进行的,其构思都是在二十多岁时播下的种子,随着成长,慢慢地在发芽、开花、结果。
《西夏咒》和《大漠祭》《猎原》《白虎关》一样,写作初期,它就成了我活着的理由。我觉得,要是不完成它们,这辈子就白活了。也正是因为这一点,这四本书,占据了我人生中的二十多年时光。它们成了记录我“成就”的另一种版本,一直伴随了我的成长。
自2010年《西夏咒》初版以来,已经过去七年了,期间,《西夏咒》还获得了“第四届黄河文学奖”和“第七届敦煌文艺奖”。在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的《白虎关》《西夏咒》研讨会上,北京大学的陈晓明教授说:“读了《白虎关》,有一种感动;读了《西夏咒》,则让我意识到,雪漠不但是一个被低估了的作家,而且是被严重低估了的作家。雪漠是大作家。”目前,《西夏咒》已被美国纽约洲立大学陈李凡平教授翻译为英文,她对这部作品非常喜欢。她说,这是最让她感到震撼的一部作品。
《西夏咒》和《西夏的苍狼》《无死的金刚心》一起,构成了我的“灵魂三部曲”,标志着我的写作进入了一个大的转折期,从展示生活进入了灵魂求索,从现实世界进入了灵魂世界。在这三部书里,读者会看到很多陌生的人物、陌生的事件,有种魔幻的感觉,甚至会随着主人公进入另一时空,体验另一世界。是真实?是梦幻?说不清。它如大自然一般,一片混沌,却不乏壮美。
我写《西夏咒》时,完全就是一种混沌状态。因为那时,我感受到一种比人类更伟大的存在,说不清这个存在到底是什么。无论你用什么样的标准、什么样的定义去界定它,都不对,它不是能被定义的东西,也不是语言所能企及的境界。这就是所谓的“不可说,不可说,一说就错。”
我的所有小说,在艺术追求上,也许《西夏咒》最有价值。写作时,我的心中总喷涌着一种诗意,让我欲罢不能。北京大学中文系的一位博士称之为“神作”。直到今天,从文学、艺术及各个方面来看,我认为最值得研究的就是《西夏咒》。
但是,《西夏咒》也总让国内的一些批评家失语。原因在于,这完全超出了他们的期待和经验,一般人进不去。但陈晓明教授对它评价非常高。他在《文本如何自由:从文化到宗教——从雪漠的〈西夏咒〉谈起》一文中说:“这部作品可能会让大多数读者摸不着头脑,但只要读进去,这部作品无疑是颇具内涵品质的。如此多的历史文化思考、宗教信仰、生与死的困苦、坚韧与虚无、时间之相对与永恒等等,这部名为小说的作品居然涉及这么多的内涵,这显然是当代小说中的一部奇书,可能小说这样的概念都要随之变化,至少对我们当今小说的美学范式提出了严峻挑战。”因此,陈晓明教授将这种写作称为“附体的写作”。同时,还有人将这种写作状态,称之为“天启写作”“神性写作”等。
在我的所有作品中,艺术的探索,思想的高度,以及激情的饱满,都集中体现在《西夏咒》中。作为一个小说家,作为一个作家,它是让我感到自豪、觉得没有白活的一部作品。比起“大漠三部曲”来,它毫不逊色,虽然读懂它的人不多,但它是一个闪烁着巨大光芒的寓言。其中,诸多的生命体验、诗意的描述,以及诸多的思想火花,都是不可替代、不可复制的。
2
很多读者都知道,我在文学上的“顿悟”,源于我的苦修和灵魂重塑。那苦苦的追求和寻觅,在我的长篇自传体散文《一个人的西部》里可窥见一斑,其艰难程度被人视为实现了一个“神话”。现在看来,那个过程,是我生命中必须经历的,少了这个过程,我的作品不会那么饱满和厚重。
我在《无死的金刚心》里说:“世上欲建大功,先须有大破。没有打碎,哪有超越?”我说的打碎,也即打碎自己的贪执,实现无我,实现一种真正的大超越、大升华。这一切,都体现在《西夏咒》中琼的寻觅和追问中。
琼,也是《大漠祭》中灵官的生命延展。灵官走出大漠之后,一直走,一直走,就走进了《西夏咒》。本来,写《西夏咒》时,我还沿用着灵官的名字,但是,后来有人说,雪漠,你再不要写灵官了,读者会有审美疲劳的。于是,我就将灵官换成了琼。而在写琼的时候,我心中晃动的,却是另一个人物,他就是《无死的金刚心》里的琼波浪觉。从灵官到琼,从琼到琼波浪觉,其实都是我成长过程中的一个载体而已。所以说,《西夏咒》同样投入了我全部的灵魂。
没有追问就没有寻觅,没有寻觅就没有成长,没有成长也就没有超越。没有超越,我也就写不出《西夏咒》。能写出《西夏咒》的雪漠,必定是实现了超越的雪漠。与其说,灵官实现了人类生存层面的一种超越,那么,琼便实现了形而上的精神层面的超越。你看,书中充满了诸如此类的“梦魇”和神奇,如“梦魇”之“诛法”,“梦魇”之“剃度”,“梦魇”之“怙主”,“梦魇”之“涅槃”等,这些有着宗教名相的词汇,却渗透了真正的宗教精神,读来,或是很有趣,或是在挑战读者的智力。
可见,《西夏咒》演绎着世上另一出大戏。戏中有逍遥自在的久爷爷,有忍辱负重的吴和尚,有寻找光明的琼,有大爱化身的雪羽儿,他们或入世,或出世,或隐或显地演着一个个灵魂如何在浊世中历练的故事。
同样的,我也是演戏者。只是,我的角色有时固定,有时不固定,随机应变。世界需要什么,我就是什么。我说过,我是一缕风,随缘迁入心。充当的每个角色,我都是认真的。往往因为太认真,反而总是被人神化,于是,我就赶紧再糟蹋一下自己,让自己和光同尘。
同时,我又自号“大痴”。有人曾问我,为啥叫“大痴”?我告诉他,我想在无常中创造永恒,我想在虚无中建立存在,我想在虚幻中实现不朽。我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不是大痴,又是啥?
就如有人问我那个“见人落水”的问题,自己不会游泳,周围又无任何助缘,那么,作为一个修行者,是眼睁睁看着落水者沉底,还是义无反顾地跳入水中去救人?我告诉他,当然要救人,还要想尽一切办法去救人!
我就是这么做的,我自称“大痴”,就是因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否则,修行也罢,菩提心也罢,都是在自欺欺人。救不救得了,另当别论,就算你没有救人的能力,也要有一颗救人之心。人活着,要有一种精神。
和我一样想法的,还有《西夏咒》里的黄健牛。在那个人吃人的饥荒年代,雪羽儿为了不让村人饿死,冒着被枪毙的危险去偷村里的战备粮,放在每户人家的门口,但在最后一次偷粮时,却被谝子抓住了。在全村没有一人说情的情况下,她被罚用车轱辘砸断腿。这个使命就落在了黄健牛的身上,因它心生一善念,不想让雪羽儿成为第二个瘸拐大,所以它故意装疯卖傻,惊了,连同那辆破车一起滚了洼,没去碾压雪羽儿。虽然黄健牛最终没有救了雪羽儿,但自己的腿却被折断了。后来,雪羽儿成道之后,黄健牛被人称为“护法神牛”。
面对整个疯了的世界,《西夏咒》中有大段大段的心理描写,写了当时拉车的黄健牛,它的力量很弱,很有限,面对强大无比的人类,它救不了世界,但它仍有一颗救世的心。它的这种精神,让它从畜生群里脱颖而出,升华了自己,赢得了敬仰。它的选择和行为,让它实现了一种超越,成了图腾般的一种存在,被人画入唐卡供奉。它用短暂的死,换来了相对永恒的生;它用短暂的失,得到了其他耕牛所不能实现的尊严。
我的小说里,写了很多动物,它们和人一样,都是“活”的。我同样写出了它们的灵魂,如“大漠三部曲”里的兔鹰、骆驼、白狐、狼、老山狗;如“灵魂三部曲”里的熊、黄健牛、大蟒、枣红马、苍狼,还有《野狐岭》里的蒙驼、汉驼。曾经,有个评论家看完我的《猎原》初稿后,对书中描写的母狼灰儿——一个失去孩子的母亲——提出了强烈的抗议,他感到不可理解。理由是,雪漠又不是狼,他咋知道狼的想法。
那么,动物的灵魂世界,我又是怎么进入的呢?
这得益于我的灵魂修炼。当我破除了执著,破除了二元对立,跟大自然达成一味时,我没有了自己,我是无我的,我能进入任何我想进入的世界。写沙漠时我就是沙漠,写骆驼时我就是骆驼,写狼时我当然就是狼。当无数的声音、无数的灵魂,都一起向我涌来时,我就成了它们,我和它们是一味的。不是我在写它们,而是它们自个儿在跳舞,我仅仅是大自然的出口而已。我所有的作品,都是这样喷出来的。西北师范大学的张明廉教授,称我的创作像火山喷发一样,真是这样的。
我写作的过程中,总有无数的东西涌来,涌进我的心,涌进我的灵魂,不是我在编造什么,也不是我想表达什么,而是它们通过我的手指喷涌而出。我的心灵可以进入任何一个时空,可以跟自己希望与之交流的任何一个个体对话。这不是我的想象,而是在那种状态中,我自然就会觉得万事万物都是有生命的,我可以和它们任意交流,甚至交融,我也可以变成它们。这种交流不一定通过语言,更多的是心灵与心灵的触摸、品味、撞击、胶着。我感受到的那种巨大存在,是当代文学无法表达,无法定义的。
那么,我如何在这种状态下创作呢?我仅仅是安住于一片明空,安住于和大自然融为一体的清明,让文字从自性里流淌出来,真像火山爆发那样,不可遏制。在流淌的过程中,我的脑中没有一个文字,我不知道自己要写什么,也不知道自己会写出什么,我所做的一切,就是打开电脑,把手放在键盘上,然后任由手指随着心中巨大的诗意跳舞。这个过程非常快乐。它是一种大乐。
《西夏咒》就是这大乐的产物。
(未完待续)
附:雪漠亲子阅读,伴您一年时光
https://weidian.com/item.html?itemID=20853998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