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当时还是国民党时期,你就知道了“民主”,可见在最封闭的西部,进步的声音也在走进幼小的心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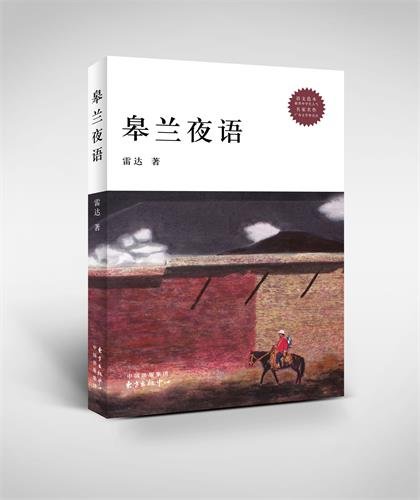
《皋兰夜语》 雷达著 东方出版中心 2014年7月
黄河远上
文\雷 达
一
我六岁那年,1949年8月,亲历了解放战争中西北战场最著名的恶战与决战——兰州战役,其时我只是一个孩童,却始终没有远离火光硝烟的现场,亲见了尸横街头,血流如注,这也算我人生的一大奇遇吧。与我经历相似者恐怕少有。
有人或会问,你当时那么小,很多事何以能记得那么清?我要说,千万不要低估一个孩子的记忆力,所有当时情景全是我的清晰记忆,毫不掺假。现在的叙述当然是揉合了后来的一些传闻和材料,但仍以自我的亲历、体验为根本依据。有一种说法,说人到老年,越是以前的事会记得越清,而眼前的事总是糊涂,看来确有道理。
战前马步芳说,兰州是攻不破的铁城,不算太夸口。兰州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有“西北锁钥”之称,它是一溜四面环山的长条形河谷盆地,惟有一条黄河穿过,惟有一座铁桥可通南北。当时环山已筑好坚固的防御体系;而马家军作为一支有宗教精神支撑、有家族血缘纽带连结的豪强武装,有“随军阿訇”相跟,凶顽悍勇,当年就围歼过水土不服的西路军。这支队伍人称“青马”,以示与偏软的“宁马”有别。所以,马步芳的骄狂其来有自。然而,他还是低估了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战斗力。
那时我家住兰州东郊红山根的农校,就在皋兰山脚下。战前已是每天听着先如一根铁丝颤悠,紧跟着一记晴天霹雳般的爆炸声,窗户纸被不断地震破。有一天,国民党飞机在农校上空炫耀,我正在操场上玩,飞机忽然哒哒哒地向地面扫射了几下,大人急向我呼喊,我向教室狂奔逃避。现在回想,那是无聊的飞行员戏弄惊吓一个孩子,真无耻。他们不败亡,世无天理!起先农校是国民党伤兵的临时救护站,每天运来一车车在外围战中负伤的残兵,多系“国军”,还不是马家军。我在路边,望着 “垛”满人肉的卡车,一路滴血而来,缠满绷带的血头颅和断了手脚的白骨一齐撑在车外,血红撕拉地赫人。接着的几天,马步芳最精锐的骑兵日夜不息地绕皋兰山转移,不时有马匹与人从高山上滚落下来。再接着,皋兰山与附近的狗娃山、窦家山、营盘岭、沈家岭一带就响起了越来越密集的大炮、迫击炮、机枪、步枪、冲锋枪们混合的声音,到八月下旬,战斗推向了高潮。
后来才知,兰州战役是由彭德怀亲自指挥的;战前毛泽东来电告诫彭德怀:“打马是一个严重的战役,要准备付出较大的代价,千万不可麻痹大意”。8.23到8.25的三天,解放军与马家军在沈家岭、狗娃山一带相持不下,形成拉锯,双方死伤惨重,基本是一比一,各自死伤者多达四、五千人。彭德怀在给毛泽东电文中说,“我伤亡相等,敌人很顽强”。为征服对方,占领制高点,解放军中出现了多位“马特洛索夫式”的英雄,按其事迹,真不亚于董存瑞。曹德荣手托炸药包,炸开钢筋水泥的地堡,杀开了一条通道,壮烈牺牲。另一位佚名英雄,已受伤,就浑身绑满手榴弹索性滚入敌阵,炸起了一大片肉酱。最后,只能以白刃格斗方式解决战斗了。解放军中有位勇者,平时苦练武功,此时一人用长矛剌死了八、九个挥舞马刀的敌人,成为佳谈。沈家岭被解放军一拿下,马步芳就知道大势已去,坐飞机逃往重庆;解放军一围攻城区,马家军兵败如山倒,马继援又逃之夭夭。我的一个朋友上世纪80年代在台湾偶遇马继援,席间,马说,“我们实在是打不过,我们机枪的枪口都打红了,人还是一层一层往上冲”。
那时大人小孩都彻夜睡不成觉。8.25半夜,兰州北边天空忽然烧红了,有人大吼,铁桥着火了!铁桥着火了!我赶紧跟着大人登梯子上房——我是被抱上房顶的,只见铁桥方向燃起熊熊大火杂以繁稠枪炮声。后来听说,成千上万的马家军欲过桥逃往青海老巢,不料一辆过桥弹药车被枪炮击中,发生大爆炸,引燃了铁桥上的木板;木板烧尽,桥变成了铁架子,溃军前涌后推不息,纷纷掉入黄河。这帮不会游泳的“旱鸭子”只能淹死。据统计,“淹毙者近二千人”。
这里有必要说说兰州老铁桥。它叫中山桥,位在白塔山下,金城关前,号称“天下黄河第一桥”。现在看来它可能是世界桥梁史上的一个奇迹。1907年由德国泰来公司包建,材料全从德国运来,甚至一个小螺钉。总耗资约30万两白银,于1909年建成。德商承诺“保固80年”。这座桥,承受过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遇上过黄河“起蛟”的盖顶洪峰,在兰州战役中又饱尝了枪林弹雨,火烧炮轰,居然无恙。现已一百多年了,虽有过几次加固维修,仍屹立于洪波之上,雄姿不减当年,怎不令人生出赞叹。
是夜,解放军虽已取得皋兰山南山攻坚战的胜利,但下山攻城,攻东岗,攻南城,皆攻不动;于是转到西关,据说是,拉了一车西瓜,扮成马家军模样,让会河州土话的战士喊话说,弟兄们,辛苦了,阿们给你们送西瓜哈来了。时值八月酷署,马军渴极,相信了,打开城门,解放军遂蜂拥而入,展开激烈巷战,直至彻底胜利。
8.26清晨,天亮了,红旗插上皋兰山主峰,从山顶到城里,到处是“缴枪不杀”的喊声,口音多是外地的,有点侉。我胆子不小,曾偷偷跟着大人们溜进城里看热闹。沿途可见沟壑里倒着死马和马军士兵尸体,血水沿着沟渠潜流着。没有枪拴的枪、未爆炸的手榴弹、各式剌刀、榴弹炮的炮弹、子弹袋、军用水壶,满街都是,要捡多少有多少。在水北门的城边,我看见一个年轻的马家军伤兵面色苍白,浑身筛糠似的抖,极痛苦的样子,抬头欲起复又趴下。其时,解放军虽控制了全城,但一切还来不及清理。这就是我亲见的兰州之战。
二
那年我已经上小学一年级了。记忆中天总是黑的,人总是冷得打颤,我跟着姐姐出了农校校门,过一片小树林,走进路边王保长家孤零零的小铺。王保长是烙锅盔的,麻脸,无任何表情。我和姐姐各拿一牙锅盔,站着趁热吃了。母亲给王保长说好了的,一学期一算账。这就是我们的早点。那时根本没什么牛肉面。多年后我用阶级斗争头脑在想,王保长作为保甲长,是要管人的,是要搞破坏活动的,可周围荒凉无人,有时还有狼,他是怎么管的呢。王保长及其锅盔铺什么时候消失的,我都想不起来了。
从兰州农校到兰师附小,须经祁家烟坊,过左公东路,贴着邱家大院墙根走,穿过天主堂什子,再过养园巷,到小梢门,就到了。兰师附小是兰州最好的小学。
就在1949年春天,兰州解放前夕,发生了血洗邱宅的灭门大血案;不但轰动了兰州,轰动了大西北,甚至轰动了全国。邱宅在我们上学的必经之路上。它看上去并不豪华,是一般的四合院,院墙还是干打垒式的土墙,不过常有汽车出入。后来才知,里面住着新疆盛世才的老丈人邱某一家。那时盛世才杀够了人,到南京当什么部长去了,同样在新疆双手沾满鲜血的邱老爷子,却选择到兰州隐居,当起了寓公。但是,怀揣血海深仇的人们并没有忘记他。于是在春天的一个夜晚,有杀手潜伏,里应外合。邱家人当晚有去听戏的,有去吃酒席的,一个个归来迟,正好来一个杀一个,全用冷兵器处置之:邱老爷子被一刀封喉,他自知罪孽深重,无言;他在西北长官公署当大官的儿子来不及掏枪即被捅翻,他求饶说,我知道弟兄们缺钱,我这里有,多多的拿上,花去,花去。杀手们却铁青着脸说,不要钱,要命!儿媳费某回来的晚,撩起旗袍一下洋车即被剌倒。杀手们一气杀了十多个人,盛世才的外甥女因事留住在同学家,成了惟一的活命者。金银珠宝仍被席卷一空,然后泼上汽油放了一把大火。杀人者是从新疆过来的,潜伏多时了,都是盛世才和邱老爷子的刻骨仇人。此案密令限时侦破,却多日未果,后来是一个涉案的小角色到市集上销赃,露了馅,致使主犯落网被处死;但随着解放战争节节推进,大多数从犯皆不了了之。这是我事后听说的。
出事那天早晨,我们虽是小孩,也被宪兵堵住,一个个搜身;放学回来,又搜一遍身。我们什么也不知道,吓傻了。从此,一过左公东路临近邱家,我们就飞奔起来,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直跑到天主堂门口才停下来。
天主堂也许值得一提。它是一座高大庄严的建筑,对上学路过的我们来说,颇神秘。我有幸随信教的舅母进去过一回。院子里,有各色花木盛开,端庄娴雅的外国修女在走动,大厅里,管风琴悠扬,鹰钩鼻子深眼窝的外国牧师在布道,气氛肃穆,我大气都不敢出。这里好像黄尘滚滚的兰州的一个世外仙境。可是不久,镇反运动中天主堂的内幕被揭开,还办了个展览,我得以第二次进去。据揭露,教堂里有潜伏特务,教士用发报机指挥飞机轰炸,指挥暗杀,破坏抗美援朝,还活埋婴儿,而且不守清规,强奸妇女,罪行累累。不过,展览会后,牧师修女们大多还住在里面,没有全抓起来,只是大门关得更严了。
三
再往前一直走,就走到我们兰师附小的大操场了。我至今能听到当年“踢毛旦”的喧嚣声。西部的孩子有他们自己的玩法。“毛旦”是用布头缝制的圆球,比网球略大,北宋高俅踢“鸳鸯拐”的那种球,亦称蹴鞠,大约就是这个样子。几十人满场子追毛旦,扬起阵阵尘埃。后来又改成了手抛毛旦,空中接力,几十人又争抢得人仰马翻,场面与今天的橄榄球无异。我小时的好友、同班同学王世强回忆说,一年级时成立小足球队(实为毛旦队),让大家给球队起名儿,我居然提出叫“民主”,老师也同意了。他感慨道,当时还是国民党时期,你就知道了“民主”,可见在最封闭的西部,进步的声音也在走进幼小的心灵。
当然,要论场面的激烈、火爆,还得说“碰斗鸡”,也叫“叠罗汉”。那是冬季的另一民间玩法。方法是,把一条腿盘起来,手扳住膝盖作为武器,另一条腿则“金鸡独立”,跳跃旋转自如;人们抱定各自的膝盖,或下压,或对冲,或由下往上猛顶对方。只见大雪飘飘中,上百个男孩旋转冲撞,见谁顶谁,混斗成一团,个个汗流浃背,不时有人被顶翻或压垮,狼狈退下。屋檐下则嘻笑着一排助战的女生。我的膝盖多次被人顶破流血,濡湿了棉裤,我仍乐此不疲。我的膝头上至今留有当年疤痕。
我也曾在这个操场上与人“血战”过。六年级时,我的同桌S,高个子,年龄比我大,白净长脸,在班上有势力,他多次和他的追随者们欺负我。一天,他又为桌面上的地盘肘击我,我们从折断对方的铅笔头发展到咬牙切齿地拧干了对方墨盒里棉垫的墨汁;他揪住我的脖领欲打,因老师进来了作罢。他挑衅地约我放学后在操场上见,说有种你就来,不然就怎么怎么,话难听之极,决无退路,我冷笑,点头。当晚在空操场上我们打得天昏地暗,没有观众,双方衣服都撕破了,脸上都挂了彩,他眼窝开了花,我鼻子大量流血——多年后诊断鼻梁骨骨折过。为此我鼻窦炎了一生。我耗尽了所有力气,他略胜一筹。他走了,不再趾高气扬,我垂头坐在台阶上。月亮上来了,有一人气咻咻找来,是姐姐。她带着哭腔说,有一天你教人打死了我们都不知道。我至今记着姐姐眼角的泪。
但也有些事很好笑,终生难忘。操场东面有个小门,出去就是兰师礼堂。有次大型集会,我竟自告奋勇登上主席台,唱了一支歌,叫《我们是民主青年》。这让所有的人惊讶,我至今也不明白我何以有此勇气。姐姐描绘说,当时我背着快掉到屁股蛋下的书包,忽然蹿上台,面对麦克风,先擤了一把鼻子,把鼻涕抹到鞋帮上,在哄笑声中唱开了。那时我只有八岁。我母亲是音乐教员,她教会了我这支新歌。看来,我是想自我表现啊。要是后来,或现在,我是绝对不会有这种“不成熟”的表现的。
那时和稍后,我们爱唱的歌大致有“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嘿啦啦啦嘿啦啦啦天空出彩霞呀”,“戴花要戴大红花呀”“是那山谷的风”,“王大妈要和平要呀么要和平”,而大合唱最起劲的是《歌唱井冈山》:“罗霄山脉的中段,有一带雄伟的高山,苍松翠竹常年青,山洪流水永不断”。它们与现今所说的“红歌”还不同,似乎可以叫新民主主义文化。
更难忘的是,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那个清晨,在操场举行了追悼大会。我虽是小孩,也知道斯大林的厉害。那时的墙报,期期都在宣传斯大林,名字多写成“史達林”、“史大林”。他去世了,自然是天大的事。那天追悼会全体肃立,三月的天气冷硬,操场上寂静如死,默哀时间拖长到五分钟都不止。也许是坚持不住了,我突然笑了,笑不可抑,愈忍愈笑,眼泪都迸出来了。我的笑传染了周围的人,王世强也吃吃地笑了。一位女老师赶过来,低声喝道,不准笑!你再笑,你再笑!我自知闯了大祸,却怎么也控制不住自己,不得不噙着泪花儿,死死地咬住上衣领子,涎水湿了一片,这才止住了;可一松口,又乐不可支,继续格格地大笑。仪式结束后,我没防备,一个男老师从我背后猛地一脚踏下来,我一个趔趄就弹出了队列。我被关在一个房间里反省了半天。
应该说,学校对我的处罚并不重。我一直在想,我为什么笑,笑什么呢,其实,这笑什么内容也没有,完全是下意识的,是神经质的,或美尼尔斯症之类,或者是觉得这么多人这么长时间不出声,太寂静了,太可笑了。早有同学提醒我,说我在上学路上,也经常自言自语,嘴唇动得飞快,有时还笑,看上去怪怪的。这种莫名其妙的笑,突如其来的笑,以前也有过。比如,在上学路上,经常碰见一个敲梆子卖油的老者,瘦高个儿,敞着怀,挑着担儿,露出搓板式嶙峋的胸骨。我和王世强看着他的排骨胸就笑起来,越笑越凶,笑出了泪,笑疼了肚子。从此一见卖油老汉从街角一闪出,大笑就开始了,我们只能以狂奔狂笑赶快逃离。我实在无法解释自己的这些行为,我只知道,随着年龄的增长,成熟,我在渐渐丧失笑的能力,我能完全控制住自己了。像这种无意义的笑,永远也不会再有了。
(续)
雷达散文代表作《皋兰夜语》此处有售: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0.0.0.0.EW0SNr&id=41000485038&qq-pf-to=pcqq.c2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