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娑萨朗》/序:不合时宜的气象
1
我常自我调侃,自己没有苏轼的酒量,却有他一肚子的“不合时宜”。几十年的写作生涯,竟都没踩上潮流的节奏点。先锋小说流行时,我不合时宜地埋头二十载,磨砺“大漠三部曲”,等二十年铸就一剑时,人家早到了火箭时代;先锋文学过气二十年后,我的《西夏咒》才出版,它虽被北京大学的学子称为神品,但曲高和寡,至今也不过几万册的销量;等文学上刚赢得了一些掌声,我却又不合时宜地写了一批文化作品,在一些人眼里,分明是不务正业了。瞧,在时下流行碎片化阅读时,我又写了一部更不合时宜的大书:《娑萨朗》。
它岂止是不合时宜,还不合地宜呢!
因为,这是一部史诗。有很多次,我一边写,一边骂自己傻~~~这年头,谁还读史诗啊?
有朋友问,你为啥写这书?我说,写一种情怀,写一种气象。我的《大漠祭》们有生活,我的《西夏咒》们有才华,我的《空空之外》们有思想,我的《老子的心事》们有学养,我的《野狐岭》有咱“呼风唤雨”的能力,我的《娑萨朗》,则有我的气象和境界。正如一位批评家朋友所说:“《娑萨朗》一出,在气象上,您真的独步文坛了,它是东方智慧的集大成。”
这话,我爱听——呵呵,这种话,谁不爱听呀?
也有朋友说,这时代,谁还有读史诗的心情呀?
于是,我说,我的《娑萨朗》不是写给你读的,而是写给你供的。有些书,你只要供了它,就能体现你的价值。呵呵,这当然是针对这位不读书的朋友的。供咱的书,总比供那欲望和铜臭好一点吧?
史诗距离人类已经太遥远了。那是人类文明童年时代的歌谣。它充满奇幻的想象,充满诗意的田园生活,充满激动人心的战斗,更少不了令人敬仰的英雄,还有荡气回肠的爱情。《吉尔伽美什》《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伊利亚特》……它们是人类文明的乳汁,伴着人类,度过了奇绝或梦幻的童年。人类文明的少年飞快地长大,那些童年的歌谣,也随着耳边呼呼的风声,散落在历史的尘埃中。偶尔,那童谣还残留着些许气息,若有似无地萦绕,形成几个间断的旋律——《罗兰之歌》《格萨尔王》《神曲》《失乐园》……
长大的成人们不再唱响那儿时的童谣,他们甚至会羞于自己曾喜欢过它们,将那儿时的诗意当成幼稚。儿时的人类相信在生活之外,还有一个奇幻的世界,相信有超越肉体的高贵精神,相信英雄,相信对永恒的追寻。而长大的他们开始怀疑梦想,开始觉得滑稽,开始嗤之以鼻,便弃之如敝屣了。
对史诗的遗忘,某种意义上,正是对梦想的遗忘。就像是对童谣的遗忘,某种意义上,正是对童真的遗忘。
于是,童真在成人世界便不合时宜,史诗在如今的时代——甚至在过去的很多个时代——更是不合时宜。
不合时宜的我,写不合时宜的作品,倒也算是很合宜。

2
说中国文明的童年时代没有童谣,令人一下子生起情感上的凉意和心酸。没有童谣的童年多么不温馨!我们怎么可能是童年不幸福的孩子呢?我们当然有民族史诗,我们有蒙古族的《江格尔》、藏族的《格萨尔王》、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但汉民族有没有史诗?有人认为汉民族没有史诗,不但没有史诗,就连大部头长诗,在汉民族文化中都一向稀罕。也有人认为,《诗经》《楚辞》便是汉民族的史诗,后来发掘的明代流传下来的《黑暗传》,也算是一部史诗。
不管人们怎么争议,我自己,却不知不觉走到了一个想唱童谣的年岁了。
对,唱一首远古的童谣,写一部生命中的史诗。
这个决定一做出,我自己先把自己嘲笑了一顿:现在,谁还会读史诗?何况人类文明的童谣可不是好唱的。它确实单纯,可也气魄宏大;它确实质朴,可也极其丰富;它确实明了,却也蕴含至高的智慧。最关键的是,它还足够长篇,这意味着够我写好几部小说的时间,却只够写这一部史诗。回想这部书的写作和打磨过程,仿佛是经过了漫长的远征。一百多万字,每修改一遍,八个月的时间便倏然而逝,前前后后已有不下六七遍,这还是以我“喷涌”的方式完成的。不然,还不知要磨秃多少笔头。
在五十多岁的黄金生命里,咋想,这都是一掷千金般的挥霍。
值得吗?每次,我都会这样问。
每改一遍时,我也会笑问一句:现在,还有人读史诗吗?
但我也只是一问而已,那答案根本不重要。因为,我不在乎。
我写了,读不读是别人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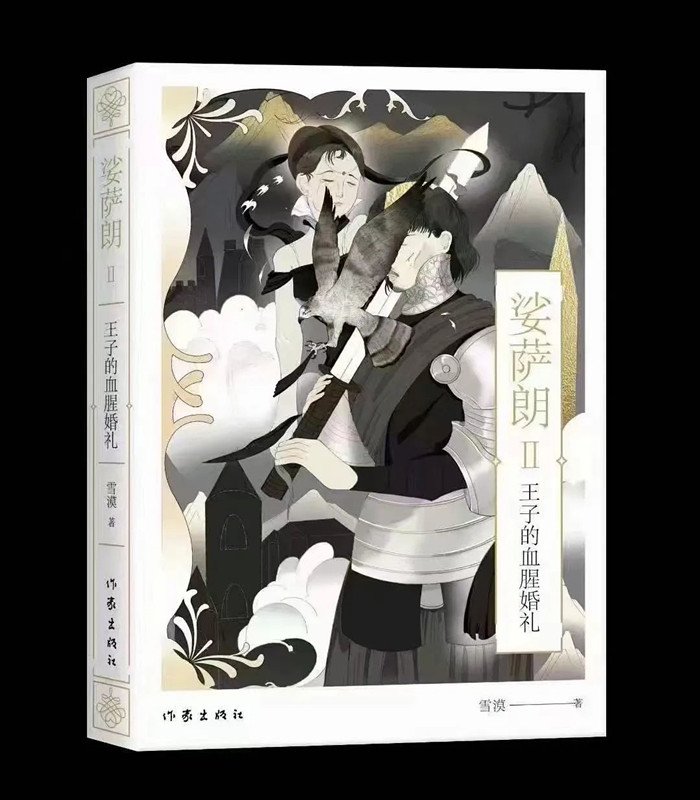
3
如果说史诗对应的是文明的童年时代,那么神话就是文明的婴儿时代。史诗中从来不乏神话,因为那些神话正是史诗的发源。如果说神话像是一颗颗天然的珍珠,那么史诗便是那光彩熠熠、巧夺天工的珍珠衫,并且这珍珠衫上还点缀了其他的各色珍宝。
正因为此,当有人说我写了部长篇神话时,我没有刻意纠正说是史诗。因为他们看到了这部史诗中的神话元素,比如生活在天界的天帝、天女、天兵天将;有各种神通能为的魔王和总是死了又复活的巫师;不老女神的彩虹般身体和娑萨朗秘境;奶格玛一个念头便可穿越任何时空;幻化郎用神奇幻身施展各种本领;一颗蕴藏无穷能量的空行石和神秘空行人;还有传统神话中的战神刑天留下的宝藏……
这些神话元素随处可见。
又或者说,在我的世界中,这些被认为是神话的东西,恰恰是另一种真实。也许,我写出的世界,才是至高的真实呢。当然,你可以当成一种文化的真实。
史诗《娑萨朗》讲了一个并不复杂的故事。
一个因沉迷享乐、过度开发而濒临毁灭的星球上,有五位背负拯救家园重任的力士,投入地球的红尘中,在觉醒与迷失中挣扎,在升华和欲望中纠斗。一个勇敢智慧的小女神,为了母亲和家园,深入红尘唤醒迷失的五位力士。五力士遭遇了各种各样的磨难~~~情关、生死关、名利关、魔王的考验、恶势力的破坏,最终找到了他们要找的永恒。
故事很简单,剧情很精彩,因为精彩的剧情,永远来自人物的内心,那里有坚定的向往和永不放弃的倔强。
在这部史诗中,我注入了广大深厚的文化内容,贯穿整部史诗的中心人物便是五位力士,他们代表着东方古老哲学认为的五种能量;那娑萨朗秘境、天界、修罗道,是东方文化对宇宙世界的另一种解读;世界的成住坏空如何演变,以及时间的极长与极短的相对,给我们展示了一个更宏阔的观察空间,也让我们从造物的视角观看了无常的变化;书中对多维时空进行了前所未有的详尽描述,当然不是为了渲染字里行间的某种气氛;欢喜郎、威德郎和密集郎对于建功立业、青史留名的渴望,这不正是儒家积极入世的折射吗?
尤为珍贵的是,本书中还呈现了另一种难得一见的文化,它不仅体现在了义的智慧之中,还体现在具体的方法论上。我相信,一定有人能够识别出,那是多么珍稀的宝藏,它是关于生命的真相。

4
很小的时候,我就很爱听各种各样的神话。长大后,我才明白,我对神话的喜欢,表面上看是因为它们的故事很奇幻,真实世界里不可能看到——夸父追日、精卫填海、刑天舞干戚,多么不可思议!实际上,我喜欢它们,是因为它们隐含了一种我很喜欢的精神特质——追寻,永不放弃的追寻。夸父追寻着太阳的光明,精卫和刑天追寻着自己所认为的一种精神,他们都有一种想要在最不可能中达成可能的勇气和心力。这种强大的心力,某种程度上打动了我,因为不合时宜的人,总是做不合时宜的事,难道不也需要一些勇气和心力吗?
《娑萨朗》史诗的主题便是追寻。
它寻找的东西,是永恒。
这可谓是最不可能达成的寻觅。世间万事万物皆不能永恒。
就有了对于永恒的寻觅。有的人在寻觅永恒的不死肉身,于是滥用权力,不惜劳民伤财,最终还是灰飞烟灭;有的人在寻觅永恒的事功,可不过数十载,事功就成了风尘中的黄叶;有的人在寻觅永恒的声名,希望能永远留在历史长河中,可一眨眼,就被历史长河的浪花淹没;有的人在寻觅永恒的爱情,想要它活到天荒地老、海枯石烂,它却往往活不过一个春去秋来。
在对永恒的寻觅上,人类落败得很彻底,就像是生来就是要被打败的那样。好在人类的记性普遍不怎么好,所以倒也没有觉得尊严荡然无存,依旧在孜孜不倦地寻觅各自想要的永恒。
我当然不会笑话上面的那些追寻者。尽管我知道,他们追寻的物事无法永恒,但他们有他们追寻的乐趣,那体验何尝不是一种财富?更何况,我不也在做着同样的事情么——我也在追寻永恒呀!只是,我追寻的是另一种永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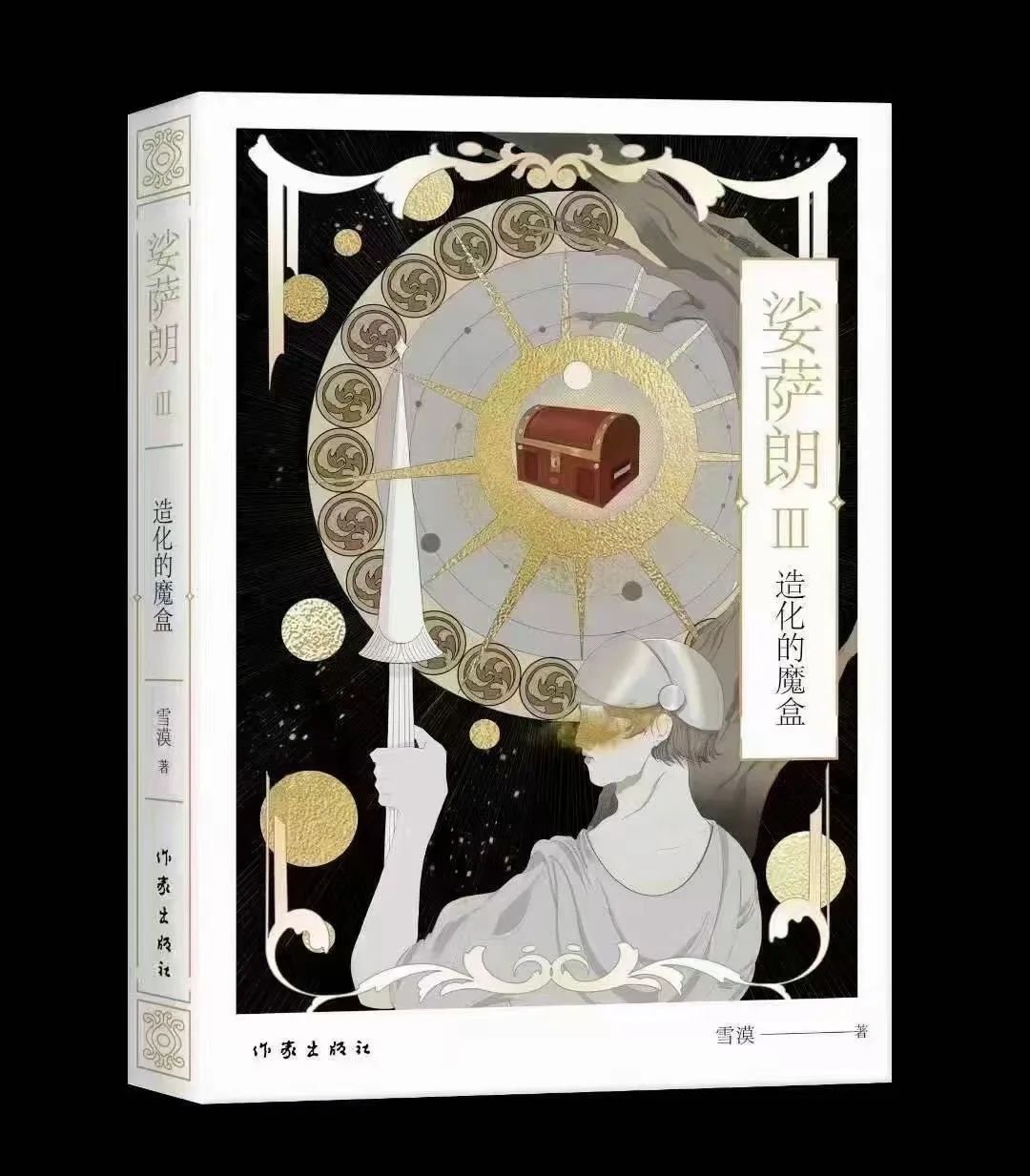
5
史诗的另一大重要元素,是悲剧。以西方史诗的文学审美眼光看,没有悲剧色彩的史诗,简直就像没有绚丽颜色的世界,只剩下灰扑扑的一片。
这部书中,同样不乏悲剧色彩。
不过,与一些刻意安排悲剧的创作者不同,我无须刻意安排角色的悲剧,就已经发现了这个世界太多的悲剧。最令很多读者牵心的一出悲剧,便是欢喜郎的爱情。本是一个充满和平理想的善良青年,只想与爱人过平淡的日子,可他还是一个王子,并且有一个尚武的父亲。他的懦弱平和与父亲对他的期待,产生了强烈的冲突,冲突最终引爆,将一个幸福的婚礼,变成了一个血腥的悲剧。从此以后,他蜕变为嗜杀的恶魔。而另一出赚人眼泪的悲剧,主人公是华曼公主,她原本是一个高贵纯洁的女神,可以为了信仰而拒绝婚姻,然而,却遭遇恶徒沦落风尘。
一个最不愿杀戮的人,却成了嗜好杀戮者;一个最不愿亲近男性的人,却被迫人尽可夫。多么戏剧化的反转,但我并不是有意如此安排。尽管有人说,悲剧的真谛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还有人说,只有悲剧才能激发人的崇高情感。
这些,都不是我的意图。准确地说,我没有任何意图。我只是真实地呈现了那必然会发生的真实,而它们却被人们名之为“悲剧”。在还未实现超越的二元世界中,极端地追求某一端,必然会落到它相对的另一端。这不是我的安排,而是二元世界的规律。也许,这才是悲剧的真正原因。
但悲剧显然并非一无是处,自我纠结善恶缠斗的欢喜郎,最终走上了寻觅光明之路;体验过最纯洁,也经历过最肮脏的华曼公主,最终也找到了自己的中道智慧。
那么,对永恒不断追求却不断落败,算不算悲剧?
我觉得它不算真正的悲剧,比起寻觅的失败,也许错误的寻觅才更像是悲剧。譬如,在沙漠中寻觅绿洲的人,苦苦追寻,耗尽一切,最后却发现追寻的只是一片海市蜃楼。无数的人这样追寻过,整个人类都这样追寻过,或者说,依然在追寻着。
如果非要我给悲剧一个定义,那就是这样吧。但实际上,无论悲剧,还是喜剧,都不是这部史诗的主题。
它的主题依然是寻觅,寻觅一种永恒的光明。

6
不知在什么时候,我突然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整个人类历史中,追寻本身比追寻的对象更加恒久。一代代人的功名利禄、恩怨情仇,被时光的朔风吹散,零落成泥,但一代代人对功名利禄、恩怨情仇的追寻,却生生不息~~~执着的另一面,何尝不是坚忍不拔?
既然人类的天性如此执着于追寻,如此地坚忍不拔,为何不去追寻某些真正值得追寻的东西?值不值得,各有各的评判标准,但至少我们都很清楚,海市蜃楼总是会令人失望的。
《娑萨朗》史诗中的奶格玛,正是一个苦苦追寻者。她虽然是天人,有着彩虹般的身体,还有无想定的心灵功夫,但她依然是个苦苦追寻者。在这一点上,她和普通的地球追梦人,很是相似。唯一不同的是,她要寻觅的不是千秋功业,不是喧天声势,不是诱人的爱情,而是永恒。据说,只有找到永恒,才能拯救她垂老的母亲和濒临毁灭的家园;据说,那永恒在地球人的心中;又据说,地球人自己却并不知道。因为,他们从来不向心内追寻,永远都在向外追寻。方向错了,于是南辕北辙,徒劳无功。
奶格玛最终找到了永恒。她发现,那永恒原来是一种智慧,它更像是一种自我发现和觉醒。这是一种究竟真理的净光。找到它,就找到了永恒。而在找到它的同时,她也成了光明本身。光明的本能是照耀,它既不追寻,也不遁藏,它只是在那里照耀。
也许,真正能完成追寻的,是无须追寻,它一直在那儿。它不是发明,它只需要发现。
这部史诗的故事,是整个人类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
我也一直在追寻。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从我发现无常的时候起,我就开始寻找永恒。我像啼血的杜鹃,一口口血,出自寻觅之心。
我是那个唱着童谣的人,也是那个听着人类文明童谣长大的孩子。
人类文明的童谣,总是有着自己独特的风味。有的像是在寻根,有的像是作某种预言,还有的就是为了歌颂英雄。
史诗中多的是英雄,也许是因为英雄最喜欢做不可能的事,做成了,便成了英雄。所以英雄也有可能是傻子。《娑萨朗》史诗中,也有一个憨憨傻傻的人——流浪汉——身藏大力却不自知,待人率真实诚,甚至是太好骗。几乎谁都可以骗他,可以欺负他,因为他什么都相信,你待他好三分,他恨不能待你好百分,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巫师用傀儡变出的那个慈眉善目的老太太,用一碗面条就让他如同见到了母亲;恐怖凶恶的夜叉女,变成了一个美丽温柔的女子,那点点羞怯与柔情,瞬间便灼热了他的心,即便是暴露了夜叉的真面目,也无法将他从痴情中震醒;好兄弟为了自己的利益,要他做出生命的付出,他也甘之如饴;每一次众人陷入艰险的困境,总是他豁出命来启用空行石的能量,众人才能化险为夷,他却数次挣扎在生死的边缘,直到最终真的逝去……还有一个关于他的、令人感到不公平的秘密,他至死都不知道。
他真的是书中最傻最傻的人。
有个看过书稿的朋友说,作为角色的塑造者,我对流浪汉有欠公平。我说,流浪汉就连公平不公平的概念都没有,他根本不计较这些。他完成了他自己。书中我最喜欢的英雄就是他。说真的,那也是我自己。
其实,《娑萨朗》史诗中,每一个战胜了自己的人,都是我。当然,也是每一个人。

7
在我眼中,永恒也可以换成另一个词:意义。
对意义的追求,伴随了我的一生。随着我对追求意义的拓宽,我的生命也在变化。
从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起,我就在寻找一种死亡后消失不了的东西。后来,我发现,它也是艺术的价值。因为人死去之后,他创造的艺术世界能相对地实现不朽。
有二十多年的时光,我在关房的书桌上,一直放着两张照片:一张是雷达老师,代表文学;另一张代表信仰。它们伴我度过了二十多年的闭关岁月。
这两张照片都有意义,但代表的意义不一样:一种是形而下的意义,一种是形而上的意义。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的灵魂总是在纠结,忽而文学占上风,忽而信仰占上风。当文学占上风时,我就喷出一些文学作品;当信仰占上风时,我就喷出一些文化作品。这就是两种力量纠斗的结果。在我五十多岁的时候,这两种东西却神秘地相遇了,这便是史诗《娑萨朗》,它完美地整合了二者,成为我生命的另一个纪念碑,也是我一生的标志性建筑。
不同的人,会看到不同的《娑萨朗》。
《娑萨朗》的另一个缘起,就是死亡。
从很小的时候起,我就经常会想到死亡,总拿死亡做生命的参照物。这在西部,已成集体无意识了。雷达老师生前也这样。每次,我谈出版他文集的事,他就拿死亡说事。一谈死亡,许多意义便仿佛消解了。于是,我对他说:“雷老师,意义不在于你个体生命的消失与否,不在于作品有没有人读,而在于你是不是把这种精神传递开来。你曾经帮助过雪漠,你点亮雪漠之后,雪漠可以点亮其他人,这就是你的意义。”所以,作品的意义是可以传承的。当一部作品影响了一个读者,影响了一个作家,影响了一个家庭时,它就有了精神的传承性,这种精神会传播开来,或传承下去,这就是意义。
不过,话虽如此说,雷老师去世后,我却忽然不想写作了,觉得失去意义了。时不时地,我就会像祥林嫂谈阿毛那样说,雷老师都不在了,我的写作有啥意思?心头总是会涌上浓浓的沧桑。为啥?知音没了,所有的演奏都像是失去了意义。
师母杨秀清却说:“雪漠,你还年轻,还是要写下去,雷老师在天有灵,还是希望你能写出更好的作品。再说,你还有那么多读者。”
她这一说,我才觉得又有了写作的理由。
当然,《娑萨朗》的写作,还有一个理由,我想保留一些不应该消失的东西。因为这世上有它,就定然会有人获益。对于一些读者,它是有意义的。当然,一个人觉得有意义的东西,另一个人却不一定觉得有意义。所以,意义只存在于跟你有关系的人之间,于没有关系的人是没有意义的。在老祖宗的说法里,这就叫缘。
对于文学,我也一直在寻找一种缘。我的第一部小说《大漠祭》出版,就与西部那块土地有了关系。所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西部,很多东西已经消失了,但因为有了《大漠祭》,那个时代就被定格了。所以,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在谈《大漠祭》。而我的作品意义之一,就是定格一个时代。
第二个意义是生活的意义。
首先,文学让我感到快乐。写《娑萨朗》时,我很快乐。死神总在远处发着笑声~~~从我有生之日起,它就笑个不停~~~一进入写作时,死神的笑就远了,我的生命诞生了超越死亡的东西。我创造的艺术世界,定然是超越死神的。一想到这,我就感到幸福。这就是写作对我个体生命的意义。
接下来,要是读了我的书,能给读者带来快乐,那么,对读者来说,我的写作也就有了意义。无论世界也罢,读者也罢,要是因为我的存在,有了一种不一样的变化,那么我就写。没有这个意义,我就不写。
你可以看出,这意义的确定,其实也是我存在的价值。什么是意义?什么是价值?我追求的意义是:我的追求在我的肉体消失之后,还有存在的价值。如果那价值随死亡消失,意义也就消失了。
从这一点上看,《娑萨朗》是有意义的。无论对于中国文学,还是东方文化,它都有创造性的价值。读者读了之后,会明显感到一种升华。
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陈晓明教授说,雪漠的作品很奇怪。很多作家的作品,一看就是“他”的,变来变去,本质难变。但雪漠的每一部作品都不一样,都是另一个东西。
为什么?因为,我自己在变,我在追求一种升华。我时时在打碎过去的自己,时时在创造一个新的自己。体现在雪漠作品里的,总是新的雪漠。我跟我的作品一起成长。就是说,我总在成长,我必须成长,我必须打碎自己,所以我的作品也必然变化。这部《娑萨朗》,也是我打碎自己后的产物。
当我发现自己在某方面非常成熟时,我就一定要打碎它。当我发现待在凉州能很好地生活时,我就离开它,走向一个新的地方。当我发现岭南很好,我可以很滋润地生活时,我就一定要走向一个新的陌生。当沂山书院已经建好,我又会选择到更远的地方去。所以,我一直在走,一直在打碎自己,让生命有一种新的可能。这也是一种意义。它会让我变得大气,因为我可以接触任何一个世界,可以融入任何一个群体,可以面对任何一种境遇,可以创造出不一样的东西。
此外,我还在追问更高的意义。我一直在追问,我的作品对人类有什么意义?因为人类终究会消亡——恐龙都消亡了——那么,我们的作品,我们的写作,对人类有什么意义?我一直在追问,所以,我对我的作品有两个要求:第一,世上有它比没它好;第二,人们读它比不读好。做到这两点,我就写,做不到,我就不写了。
《娑萨朗》做到了这两点。
此外,《娑萨朗》还做到了另一点:为往圣继绝学。
西部有个全真派老道长,八十多岁了,叫冯宗夷。前些时,他在临死前,打电话给我说:“雪漠,你赶紧过来,我有东西传给你,我今天晚上就要走了。”我说,你不能走,等着我。于是,他就等着我。等我过去时,他便将他一生积累的东西传给了我。然后,他了无牵挂地走了。冯道长有几大绝学:邵子神数的心传钥匙、道医、祝由科、内丹等等。几十年中,求者无数,他就是不教。临终时,他只想教给我。为什么?因为他知道,我会传承下去。所以,文化传承很重要。
在《娑萨朗》中,有无数这样的绝学。有一些,像风中之烛那样传承了千年,到我这儿,才形成了文字。
不管是文化还是文学,一定要有一种精神的传承。复旦大学陈思和教授说:“在中国作家中,雪漠和张承志是最具有精神性的。”的确,对精神性的追求,是我作品的重要基调。这一点,在《娑萨朗》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雷达老师也是这样,他虽然走了,雷达精神却传递给了很多人。我们现在还在缅怀他,我们会像他那样做人,会像他那样面对这个世界,会像他那样利于这个世界,这时候雷达精神也就有了传承。
这《娑萨朗》,同样也是诸多文化传承的载体。
我的作品很多,各种版本共计八十多部。每一类读者都能找到一个入口,找到我想创造的那个意义。因为,我所有的文学作品、文化作品,都想给世界带来一种光,都想照亮有缘的你。
当你是萤火虫时,你就先照亮自己;当你是火把时,你就能照亮身边的人;你慢慢长大时,你的光明会越来越亮,就能照亮更多的人。等到有一天,你能照亮世界,拥有整个世界时,你就是太阳。这也是《娑萨朗》中诸多人物的命运轨迹。
我之所以能走到今天,写了那么多书,秘密只有四个字:战胜自己。所以,在任何时候,我都在做一件事情:战胜自己。很小的时候,就是这样,越是长大,战胜自己越麻烦,但我一直在战胜自己,战胜欲望,战胜愚痴,战胜仇恨,战胜来战胜去,自己也越来越强大了,作品也就多了。
《娑萨朗》中,同样也充满了灵魂的纠斗:灵与肉的纠斗、个体与社会的纠斗、生存与命运的纠斗、自我与他人的纠斗……这类无量无尽的纠斗,同样充满了人类的天空。
我的人生中,也充满了纠斗,充满跟自己的战争~~~我天生是一个作家,有着各种欲望和纠结,但我又想超越一切,于是就免不了纠斗。我的生命,就是在这种纠结中成长的。直到有一天,哗的一声,我的世界一片光明。
《娑萨朗》写的,同样也是我的纠斗和升华。因为它探入灵魂深处,就有了与时下的文学不一样的气象,虽然不合时宜,但日照江河,气象万千,滚滚滔滔,源远流长。
《娑萨朗》中所有的人物,也跟我一样,都在追求永恒和不朽。这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实现的梦。因为,世界是无常的。在无常和永恒中间,有一种不可调和的东西。这种一言难尽的纠结,构成了作品异乎寻常的复杂和博大。
直到今天,我仍然在寻找永恒。明明知道,永恒不可能,世上哪有什么永恒?除了一种永恒的精神之外,个体生命的永恒是很难实现的,但我总想实现。我总想在肉体消失之后,留下一些不朽。这也是我一直在努力的原因,就像堂吉诃德斗风车一样。于是,我献身艺术,献身信仰,其目的,就是想在无常中建立永恒。
我的智慧告诉我,世界总会变化,一切总会过去。一切都在变化、变化、变化,消失、消失、消失。而我的向往却让我总想在消失之前,留一点消失不了的东西。我选择了艺术。我需要一种与世界沟通的方式,需要一种能被这个时代接受的叙述方式,需要在个体生命的丰富与世界的丰富之间建立一座桥梁。
我一直在努力,《娑萨朗》就是努力后的成果。
《娑萨朗》是一个契机,它能够把艺术世界与世俗世界、信仰世界与现实世界结合起来。有了这个契机,我们会多一种可能性。
我追求的成功,其实还是战胜自己。就是将自己彻底打碎,融入一个巨大的存在,或者成为一个巨大的存在。这就是我自己的追求。
当然,与世界沟通时,我有我的方式。我先是吸纳。跟几乎所有人的相遇中,我都能学到东西。一个人低到极致时,只要你足够大,你就能成为大海。人低为王,水低为海。三人行必有我师,不要有成见,完全地包容,完全地接受,完全地汲纳,不懈地学习。然后,把学到的东西化为营养,创造价值,分享出去~~~用世界能够接受的方式分享出去。我的行为就构成了我的作品。随着我的成长,作品就越来越丰富了。
《娑萨朗》也是学习的产物。它用一个作家的方式,向人类历史上的那些伟大史诗致敬。

8
很小的时候,我就逃离了家庭,一个人待着,尽量与世隔绝。我永远逃离人群,留给自己一个灵魂的空间。直到有一天,我不用再逃了,因为我在人声喧嚣之中,也如处旷野,没人再能影响得了我,一若《娑萨朗》中的胜乐郎。
写《娑萨朗》之前,没有“娑萨朗”,我只有让自己成长,到最后,我成了它的时候,就让它从心里流出来。所以,我不是在创造它,而是我成为它。这需要时间。我用了二十年,让自己成了“大漠祭”们;用了三十多年,才让自己成了“娑萨朗”。
在书中,我找到了永恒。
还有人问我,《娑萨朗》史诗故事的时间背景是什么时候?我说,任何时候。
无始以来的追寻,依然在继续;无数人的寻觅,定然还会有无穷尽的续集。时间只是一个幻觉,空间只是狭隘的秩序规则。在《娑萨朗》中,空间有很多重。人类的心灵有多丰富,世界就有多少层空间。当你不再习惯性地,试图将故事钉在某个确定的时间坐标点上时,你能得到的,反而更多。
更何况,我说的原本也不是某个时间点、某个空间点的故事。
之前写很多书时,特别是写“大漠三部曲”时,我的意图是定格,将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地域、特定的人群和生活,像定格画面一样定格下来,为的是在飞速逝去的时光中,抢回一点历史的碎屑。
但动与静,定格与流淌,何必只执其一?
我既可以定格特定的历史横剖面,也可以流淌经久不息的历史歌谣~~~过去、现在、未来,哪个不是历史?《娑萨朗》就是这样流淌着的歌谣,它是过去,是现在,也是未来,或者说,无所谓过去、现在还是未来。
如果你喜欢,就跟我一起唱这首关于永恒的娑萨朗之歌吧。
2019年4月14日初稿于尼泊尔雪漠图书中心
2019年5月1日定稿于甘肃凉州雪漠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