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下关怀与终极超越
——雪漠小说《白虎关》的生命叙事
袁田野
(北京语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部)
[摘 要] 雪漠的代表作品《白虎关》阐发了对生命的悲悯情怀与追寻终极的道心。通过对小说的生命意象、死亡叙事的分析,发现隐含作者对“痛苦”的叙写是以传统哲学中的“苦谛”思想探求苦的因缘,以寻找解脱的智慧。小说中几处火葬场景和疾病书写呈现出了生命空性的寂灭之美。另外,小说借鉴比喻、暗示等手法融入生命哲学的妙悟,以“月光”“灯光”等意象阐释“无明”和“自性”,通过对“呼吸”的凝然描写阐释“生灭”与“无常”,构成了一种透彻玲珑的妙境。
《白虎关》是雪漠发表于2008年的一部长篇小说。作为“大漠三部曲”的收尾之作,《白虎关》被作者称作是“用了最多的生命积累,耗费了最多生命体验,投入了最独特生命感悟”[1]491的作品。“白虎关”有三重含义,其表层含义是西部的一处。另外两重含义则具有象征意味。在民俗文化中,白虎与白色及杀伐之气相关,“白虎关”在民间也就被视作是一重难以度过的关煞。此外,古人有“东青龙、西白虎”的说法,“白虎”在方位上位于西方,在五行上属“金”,而小说中的金矿被发掘于白虎关。因此,雪漠对小说的命名已隐含了小说的意蕴,人生的境遇中总会遇到命运设置的关煞,人该如何突破生命的终限,获得超越痛苦的智慧。

一、苦谛:无常砧板上的灵魂
整部小说的内容围绕着两条线索展开,一是“开金窝子”,二是“换亲”。双福在白虎关挖到了金矿,引发了淘金热,白虎关的劳动力都下井当沙娃,再用血汗钱开金窝子,白虎关的地皮也开始上涨,“金钱”逐渐打碎古老的乡村伦理规约,成为价值判断的唯一尺度。同时,对金钱欲求的膨胀则使得婚姻变成了彻底的交易,在这片土地上引发了焦虑与苦闷。为了大哥憨头娶妻,老顺的女儿兰兰嫁给了性格暴虐的白福,白福的妹妹莹儿则嫁给了性无能的憨头。新的经济形态导致了人性异化,西部封闭原始的生存环境束缚了人的心灵,尽管小说中隐含了一种对现代性与蒙昧的双向反思,但这却不是整部小说的主要着墨之处。
在雪漠看来,虽然这片土地即将消失于现代文明洪流中,但也是历史无常的一种体现,变化是世间万物的本质,只有通过叩问自身灵魂,才能实现超越。他选择融入到这片土地上农民的血脉里,以他们的视角去呈现其灵魂与命运。尽管在情感和精神距离上,他离他们很近,但他审视灵魂的目光却并未被遮蔽,修行者与作者的双重身份使他能够从俗世中超拔出来,以悲悯情怀去理解每个生命的痛苦。因此,这部小说并没有演变成反思现代文明或批判乡土现实的故事,而是呈现为一种寻觅治疗痛苦的良药,实现解脱的生命叙事。
这种生命叙事从对“痛苦”的叙写开始,雪漠在《爱与理想的喷涌》一文中提到自己对痛苦的写作是为了寻找解决“痛苦”的终极答案,“在《白虎关》里,这种疼痛,一直发酵,一直发酵,到了生命的极限,疼痛的灵魂便一泄而出了,发出的呼喊,有点撕心裂肺。所有的一切,都在叩问,那解除疼痛的良药在哪儿?谁能抚平一个个灵魂的伤痛?谁能给予回答和指引?”[2]2这种寻找体现了一种生命探求的深意。尽管“白虎关”这片土地的自然环境恶劣,经济贫穷,但小说并不关注人们吃穿住行的难处或日常生活中物质的匮乏,而是更侧重展现精神层面的痛苦。而隐含作者对种种痛苦之相的展现也与生命之苦的有着内在联系。总体上看,小说中对人物心灵痛苦的展现大致集中于这几个方面。
一是“求不得”之苦,这种痛苦主要体现在猛子身上。对于猛子这一人物,作者隐含的情感是复杂的,同情之中又融合了深沉的责备。叙述者常以全知视角介入猛子的内心世界,以展现这一人物勤劳朴实的内在本性。但在小说中,猛子的行动却与其内在本性相对立,他接连做出了套白狼、偷窃、掘坟等违背伦理道德的事情。通过对猛子的行为模式进行分析,发现猛子在所有事件中都是充当“接受者”这一行动元,即在事件中处于被动的位置,都是在别人的推动下才实施行动。在行动开始之前,原有的良知往往让他下意识拒绝行动,但别人三言两语的劝说就可令他动摇,而让良知让步的正是猛子心中的欲求。贫穷的家境让他无法娶妻,知识和能力的局限让他无法跳出贫穷的处境。“求不得”所带来的无能和自卑令他只能通过“偷”来获得报复的快感与虚假的占有感。但“偷窃”行为将他推向的是更深一层的“求不得”的空虚感,因为他得到的只是短暂的愉悦,能证明他生命意义与价值的事物却无法企及。
二是“爱别离”之苦。在小说中,“爱欲”是忧虑与恐惧的根源,与所爱离别,便可生种种微细之苦。“爱别离”的痛苦贯穿于主人公莹儿的命运,她因换亲嫁给了老顺的大儿子憨头,却爱上了老顺的三儿子灵官。憨头因病去世后,莹儿和灵官相爱,灵官却因对哥哥的愧疚出走他乡,两人从此离别。叙述者也刻意点明莹儿所受的苦是“爱别离”之苦,“她读过几本佛书,书上说苦有多种,有生苦、死苦、爱别离、怨憎会……后来,她才渐渐体会出苦了。不说别的,只那‘爱别离’,就叫她苦不堪言。”[1]167然而,莹儿与灵官特殊的伦理关系已决定了这是一种无法言说的痛苦。莹儿宣泄苦痛的方式就是唱花儿,花儿是广泛流行于青、甘、宁的西部民歌,其曲词粗犷而悲怆,在作品中与莹儿的命运融为一体,如“哥哥走了我配瓜,手拿瓜花儿灰塌塌”,暗示了莹儿被迫改嫁的命运。又如莹儿常唱的,“白牡丹掉到河里,紧捞吧慢捞着跑了”,“花儿是小妹的护心油,要花儿不要命了”则是她自戕身亡的谶语。花儿的歌词贯穿了莹儿的痛苦心灵,在一种怆凉的美感中定格了一个西部传统女性的灵魂。而雪漠对莹儿痛苦的描写并不是通过一位出离者俯瞰的视角进行,而是潜入到人物内部,与笔下的莹儿共同感受着这种“别离”之苦与悲伤,甚至倾注了自己的心灵和情感,这也是其悲心的体现。
三是病苦,这一痛苦主要体现在人物月儿身上。月儿是小说中唯一一个离开乡土,走向城市的女性,而再次回到家乡时已身患梅毒。梅毒作为一种以性接触为主要传染途径的疾病,注定潜藏着一种性方面的道德评判。这意味着,这种疾病带给月儿的痛苦是多重的,除了肉体逐渐溃烂的痛苦,还需要承受生命逐渐消逝的恐惧、群体道德评判引发的羞耻感,以及他人的厌恶和远离带来的精神孤独。叙述者并不沉迷于描写疾病带来的肉体上的痛苦,而更侧重于呈现月儿心理上的痛苦。因为梅毒的传染性,月儿和猛子的亲密接触遭到了公婆的窥视。这种窥视带给月儿的是两种精神上的痛苦,一是在这种窥探之下,私密领域遭到无情的侵犯,被剥夺的是安宁与尊重。二是这种窥视将善良柔弱的月儿推向了一个施害者的位置,使她感受到沉重的道德背负与罪感,而这种罪感指向自身时,便剥夺了她与猛子相爱的勇气,甚至继续生存的力量。因此,疾病带给月儿的是恐惧、罪感与绝望交融的心灵之痛。从表层叙事上看,隐含作者揭示的是个人的苦难,每个人物都受到各自生活的束缚,身心饱受痛苦的苦恼。但从深层叙事上看,隐含作者所呈现的是一种“群己共苦”的本相。雪漠在小说序言中写道,“人类为什么会有疼痛?我告诉你,因为有死亡,因为有变化,因为一切都不能永恒。这是生命的真相。不管你是否明白,该来的终究会来,该去的终究留不住”[2]2。一切有情都生死有期,宇宙有成住坏空。生命无法脱离无常变化,所以人生一切皆苦。因此,这部小说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乡土小说,它呈现的是人类灵魂临的普遍困境。尽管苦痛具有宿命性,雪漠却非悲观的命运决定论者,他意在寻找一种生命智慧以解消痛苦,探求一种道心以超越命运的桎梏。

二、灭谛:凝视生命的无常
小说对灵魂苦痛的认识是建立在一种对生命无常的认识中。隐含作者通过对死亡的凝视和冷静观察,破除无常所引起的烦恼障碍,呈现出生命空性的寂灭之美。这种窥破虚幻,断灭痛苦的思想与传统哲学思想中的“灭谛”有着内在的精神联系。灭谛的“灭”是灭除烦恼根源,从生死轮回中解脱,从而达到一种寂净的境界,这需要对生死烦恼的根源达到一种透彻的知见。雪漠自觉将对死亡的哲性思考寄寓于小说中,认为对生命的体悟依托于死亡带来的修炼。因此,洞悉死亡首先就需要直面肉身的坏灭。小说中对死亡的书写就体现了面对死亡的一种本真态度,具有“向死而在”的意味。在小说中有两处对火葬场景的描写,一是王秃子杀人后,村民将他与被杀的孩子的尸体架在一起火葬;二是大牛在卤水池离奇溺亡后,法医解剖无果,工友们便将其火葬。
两处火葬场景皆凝然于人的肉身于火中的形态变化,没有那种悲死念生的怆意,而是一种肉身终归于空寂的无常感。其中,对大牛死后火化过程的叙述十分细致,隐含作者意图解消肉身,昭示无常。在小说中,大牛非常能干,一天能捞十吨盐。小说描写了他的强壮身躯,“他脸上虽瘦,但身上尽是腱子肉。出力时,腱子肉就鼓起来,一条一条的”,然而无论多强壮的身躯也无法抵抗死亡和火的消解。在传统生命哲学中,肉身为地、水、火、风四大元素因缘和合而成,分别代表了身体的坚性、湿性、暖性、动性。首先在火中消解的时身体的地大,“硬皮想顽强地守候自己本来的颜色,火却在顽强地舔,渐渐地,灰皮泛白了,变得斑驳陆离”,“大牛的身子收缩了”,“那火力,并没完全燎光肉。它仅仅是将肉变成了釉状物”[1]422,美丽的皮相终将改变颜色,坚硬的骨肉终将崩解消融,肉体的坚固性是不常存的。其后蒸发的是身体的水大,“肉皮上的灰斑渐渐洇渗开来,冒出了一股水液,但火很快就气化了它们”,“肉变成了硬皮,贴在骨殖上,意味着火已消灭了大牛体内的水”[1]422,水本就无常态,人身体中的水更无法常驻,终将蒸发消散。燃烧身体的“火”本身就包含了流变的象征意义,火在燃烧的过程中,就在不断地变化,被燃烧的物体也无法保持固定的形态。传统典籍中以火喻无常,火宅喻三界无常危脆。若将身体视为苦集之宅,火葬场景也有身体无常危脆的警醒之意,就与佛典中的火宅之喻存在着微妙的联系。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写到大牛在下葬的次日就曝尸在外,“他贴在骨上的肉早叫啥动物啃光了。骨头虽叫烟熏黑了,但那一道道的牙印却啃出一线线干净的白。莹儿们边哭,边将散了一地的骨头收拢了,埋进黄沙”。[1]423这与传统哲学思想中的“十不净相”中的“骸骨相”有着冥契之处。在常人看来,“白骨黄沙”包含了悲怆和凄凉。隐含作者以出离的清醒看白骨,只是四大假合的色相遵循“成住坏空”自然规律所呈现的虚幻之相,落句平淡浅白,却给灵魂带来一种惊悸感。
小说中的两处火葬场景的描写在叙述无常的基础上,还内蕴了一种解脱之意。破除对肉身的执着,利于破除“我执”,不再执幻为实,也就不为贪嗔痴所恼,从而获得一种解脱之乐。在小说中,王秃子和大牛的火葬场景表现了两种不同的死亡境界。王秃子因贫穷受到村长的欺压,在一念嗔心之下,杀害了村长的两个孩子,最终自己也惨死于野兽之口,于是村民们将三具尸体架在一起火葬。在叙述者的冷眼观察中,火中人一生因执着于强弱贫富,此时却一死万事空,因此对尸体的描绘也显出一种冷嘲的口吻,“娃儿胖些,身上的油淋漓着。秃子瘦些,没多少脂肪,只剩那个黑木似的身子。这是富的大头儿子和穷的王秃子的唯一区别。毛旦就把秃子身子,拨到两个娃子身上,叫娃儿那富油去燃那瘦身。”[1]288。火化之后,王秃子和娃儿的骨头混在了一起,凶手和被杀者亲热地拥抱了。叙述者借老顺之口评论,“要是王秃子知道骨头会拥抱,还杀人不?”无论强弱贫富,死后一切世俗虚像都一扫殆尽,拥抱的骨头也体现了人与人原本互相依持的缘起思想。虽语调中带了一丝冷嘲,却也是隐含作者以悲心直指生命的迷象。与王秃子的火葬场景不同的是,对大牛的火葬场景的描写则具有一种灵魂升华的仪式感。火化大牛时,柴是“急不可耐地腾起一团亮亮的火焰”,帮助大牛“完成最后的升华”;火是“欢快地呼呼着”;当“汽油完成了它的使命”,大牛的肉体也加入了这场生命的仪式。火、柴、汽油以及大牛身上流出的“燃料”都像是带着迫切的希望以完成某种使命。叙述者将火比作乌鸦,“它们是一群狂欢的乌鸦。它们一口口叼走了绒单,叼没了衣襟,将白皮肤舔成了黑色”[1]4222,这种比喻具有一种神秘和肃穆感,体现了灵魂脱离死亡的色身之后,获得的一种净化与解脱。在描写大牛身上流出的液体时,也透出一种怪谲而又寂净的美感,“一滴一滴,从一晕晕散开的灰色中渗出,先是水汽般的晕纹,渐渐凝成一滴。那‘滴’越来越大,终于流下发黑的躯体,在火中溅出一团光华”[1]422。油入火中化作光华,恰如滴水入海,尘归大地,一切回到本源,这种美感是无常之美,也是一种寂灭之美。
除了对死亡的书写外,对疾病的书写也形成了另一种对“生命无常”的表述。在小说中,月儿身患梅毒,这种疾病因其传播途径而被人们视为是“脏病”,它造成的肉体溃烂也在视觉上与美相去甚远。但在雪漠的笔下写来,却并不让人觉得“脏”,月儿身上反而透出一种洁净之美。隐含作者对月儿这一人物饱含着怜惜之情,描绘她苍白的脸、瘦小的身体、淡淡的愁容,并透过猛子的视角呈现她那充满了青春和温柔气息的身体,从而唤起了猛子的爱怜。然而,交替呈现的也有月儿被疾病侵蚀的身体,小说也写到她的病处流着黄水的软烂的疮、腿上溃烂的洞。
这种笔法颇似于《红楼梦》中的风月宝鉴,一面演示着美丽的肉体,一面演示着濒临死亡而溃烂的肉体。佛教的“不净观”以九相图观人的肉体从死亡到骨骸化灰的九个阶段,以对治人的贪欲。这种贪欲既指男女之间对彼此肉体的贪爱,也指对自身肉体的贪着。月儿的身体也由此示现了两种境界,一是让猛子从欲念中出离,在无常中体会到永恒。在与月儿结婚前,猛子贪着于肉欲。月儿让迷茫流转于欲念之中的猛子豁然清醒。小说有一处便体现了猛子对无常的体悟,“那白虎关,终究也会叫那搅天的黄沙填了,或叫无常吞了,或在若干年后宇宙命尽的时刻,变成一抹消散的烟雾……猛子能感受到那种远去,那觉受瞬息万变,却又恍然在永恒里。”[1]483月儿美丽肉体的消陨是无常,沙丘的扩大、家园的失落都是无常,即使是承载了众人淘金梦的白虎关也终将消失,世界在生灭变化,就连人的心也变化不居。猛子与月儿此时的相爱是实在的,但在这无常中又不过是电光石火。这种对无常的体悟让猛子从种种“求不得”之苦中清醒,珍惜眼前的爱人,却也不贪着于这种爱。
月儿身体示现的第二重境界是“处染而不染”的寂净境界。月儿之所以给人以洁净之美,正是因为她的灵魂未被污染,且心中存善,虽身染梅毒,却犹如花不着身,处染而不染,处秽而不秽。最初得知她患病,村里人见她就躲,认为她得的是会传染人的脏病,但他们也逐渐被月儿的纯善和坚定的意志力所打动,慢慢的骂声稀了,甚至还对她生起了恻隐之心与善意。当月儿和猛子坐摩托车回村时,沙娃们为他们欢呼,村里人都来探望。这时,在众人眼中,身患梅毒的月儿已无所谓净与秽,她灵魂的纯善也涤净了他们的心灵。最终在火中结束生命的月儿也获得了一种肉体的解脱与灵魂的升华,定格了“善”的美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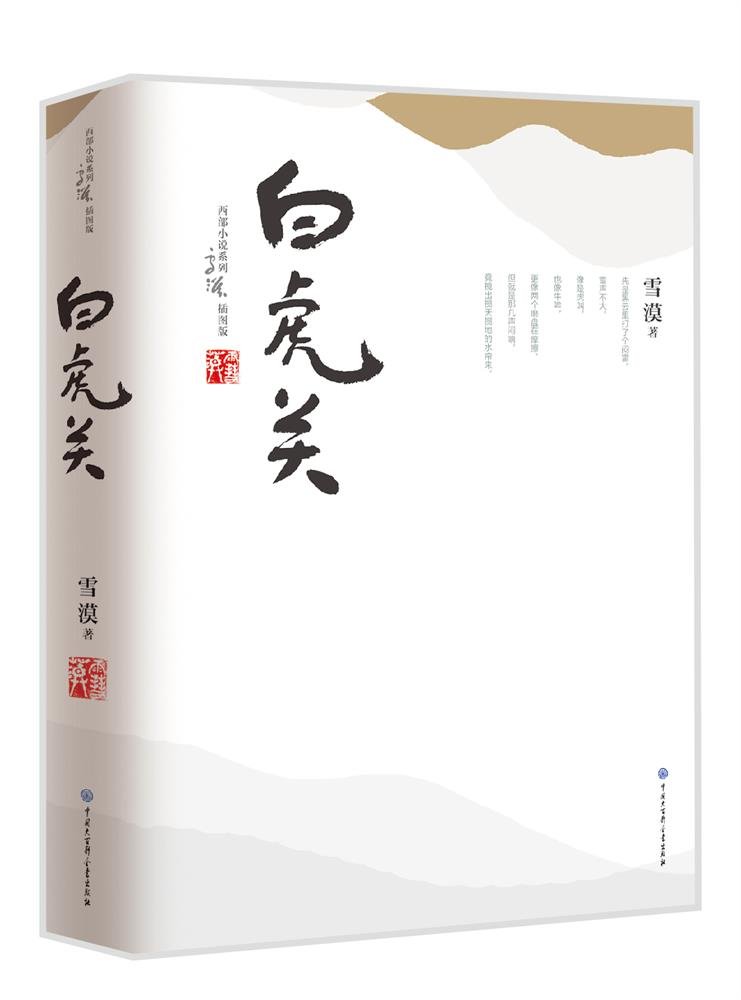
三、道谛:超越命运的桎梏
在这部小说中,作者对灵魂的痛苦有一种深刻的体悟方式,这种方式来源于佛教“生命无常”思想的影响。雪漠在这部小说的序言中写道:“寻觅是我永恒的功课,明白之前的寻觅,是为了自己的明白;而明白之后的寻觅,是为了让更多人的明白”[2]2。“明白”即是一种观照的智慧。寻觅则是对道谛的寻觅,即探求一条超越无常命运的道路。小说中的道谛也体现了一条旨归,即通过以自性观照当下、自力修持、信力坚定这三种主体精神超越无常苦痛。作者对道谛的理解从他笔下塑造的人物即可看出,他分别为莹儿和兰兰这两个人物铺设了两条不同的信仰之路,从而呈现了迷与悟两种不同的生命境界。
一些学者对小说中莹儿的自戕结局表示质疑,认为莹儿是把爱情视作精神图腾的,在还未等到灵官回来时,是没有理由放弃生命的。雪漠在《呼唤的灵魂》一文中回应了这个疑问,“如《白虎关》中的莹儿,她之所以后来没有走出命运,就在于她的心仍是一片黑暗,灵官给她带来的那点光,很快就被黑暗淹没了,因为那是灵官的光映射到她身上的,而不是自己生命中真正焕发出来的光。”[2]490在雪漠看来,将男女之爱作为信仰是有限的,小爱只是个人的觉受,转瞬即逝。他强调的是“自性”,也就是“生命中真正焕发的光”。因此,没有勘破情爱无常,未能开悟自性的莹儿终将被命运的黑暗吞噬。
在小说中写到莹儿借着月光和灯光观察睡着灵官,这一情节就具有“观”和“照”的象征意味,其中,“观”与“呼吸”联带在一起,与“照”相应的则是“灯泡”的隐喻。首先需要注意的是光的隐喻,“观照”的“照”是透过自性的光明,对事物进行透彻、笼照的了悟。人人都有“自性”这盏具有智慧光明的心灯,只在点燃与否,真正的至暗是心中的无明。在小说中,莹儿有关生命的启悟都来自于灵官的外在灌输,正如她需要借助月光或是灯泡的光才能观察灵官,灵官出走后,爱情图腾的微弱的光也消失了,她也失去了把握生命的方向。
其次是“观”中“呼吸”的隐喻。莹儿观灵官“鼻翼的翕动”、“胸部的起伏”时所感受到的“奇妙韵律”是一种生之韵律,通过凝神观察,莹儿的心灵与灵官的一呼一吸合为一体。在佛教思想中,“出息不还则属后世,人命在呼吸之间耳”,“呼吸”蕴含着“生灭”之义,生命处于呼吸往来之间,有生即有灭,有灭即有生,呼吸的本质即是无常,执着于肉体生命即执着于幻相。但莹儿的“观”既未显示出清醒者对沉睡者的透视,她完全被灵官的肉体所散发的生命气息所吸引。在莹儿看来,肉身也是情感的载体,身在则情长在,唯有将情感投射于五感可及的肉体生命,才能确信对“情”的真实拥有。因此,灵官的出走使得莹儿丧失了灵魂的依怙,“她的精神快要崩溃了。屋里的一切,总在提醒她:这儿,曾来过个鲜活的肉体”。小说反复写到莹儿对灵官那鲜活肉体的眷恋,当无法抵御现实的苦痛时,她只能借助回忆和想象填补内心的虚无。
雪漠的思想受到传统哲学“梦幻观”的影响,在作品中意图勘破莹儿的“迷”,以点明情爱的无常本质。在对莹儿与灵官爱情线索的构思中,处处体现出一种虚幻意识。从时间上看,莹儿与灵官的爱情事件发生于过去,对莹儿记忆的追述则在莹儿的感觉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交替,从而模糊真与幻的边界。小说中两次写到莹儿送灵官远行时的场景,在送行的场景中,叙述速度如慢镜头一样被延缓,从而呈现出许多细节,如莹儿所立的沙丘、身旁的黄毛柴、灵官所走的灰线似的小道,甚至是莹儿送灵官远去时所唱的“眼泪花儿把心淹了”的歌。尽管场景的细节真实且情感真切,叙述者却又以一种外在的权威声音打破这种真实性,点明此前一切皆出于莹儿的感觉与想象,“但真实的故事是,莹儿没送灵官”。一方面揭示出莹儿的幻境和梦都是感觉世界的产物,因情而生,并非实相,不应执幻为真;另一方面又借灵官之口反复强调“爱情是一种感觉”,点明爱情是因缘而起,性本空无。在小说结尾部分,叙述者深入到莹儿的内心世界,发出更深一层的追问,“莫非,人生的一切,真的仅仅是感觉?又想,生死,不也是一种感觉吗?这身子,比那尸体,多了的,还不是感觉?”从而由身无常,推至爱无常,终至人生无常。人生如大梦,梦中之情何以为真,而莹儿因情所陷的幻觉性的思念情绪和恍惚、痛苦,更如梦中之梦。
作者更多地将超越性的精神倾向投射到了人物兰兰身上。与莹儿不同的是,兰兰通过生死轮回这一机缘,走上了一条“悟”的路。兰兰的“悟”首先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心无杂染的修持,二是坚定无畏的道心。小说中凡是写到兰兰修炼的部分,都浸透了一种生命的超然体验,“那散了的,还有心,还有身子,还有那个叫兰兰的概念。时不时地,就只有空灵了。有时,空灵也散了。”[1]134这段描写其实是兰兰悟到空性时的一种体验,从中可感受到一种生命的平和欢喜。烦恼、痛苦、期盼、心、身体、概念等都由执着所生,皆是心造的幻想。当兰兰专心念心咒时,不生妄想,不生我相,原本遮蔽心灵的无明烦恼刹那悉皆消散,自性清明开始显现。这使得兰兰能够挣脱束缚,获得一种心灵的宁静与自由。小说用了大量文字对这种体验进行描写,“兰兰的生命需要这韵律。在心里盛满了苦难,盛满了泪水,淹没了希望的时候,这韵律,便该在灵魂里响了。”[1]134这种体验给予了兰兰的慰藉,涤净了心中的苦难。渗透在这部小说中的生命意识不是苍白的说教,而是在破除我执后精神上的自在感受和超越意识。兰兰修行的目的也由最初的出离痛苦,转变为体会禅乐。兰兰并非通过繁琐的仪式彻底膜拜神灵,而是返归自己的内心找到一种禅定的力量。
小说中写到兰兰和莹儿前往大漠中的盐池,却一路屡陷绝境时,构成了一种生命的寓言性。她们一路上遭遇了豺狗子的扑食,损失了一头骆驼,又陷入流沙,失去了水和干粮,死亡的阴影笼罩着她们,又兼疲累和饥渴交迫。在此过程中,莹儿不堪其苦,起初她还试图凭借对爱情的幻想来抵消痛苦。对于以爱情作为精神支柱的莹儿,隐含作者冷眼审视,并直切地指出其虚幻性。因此,当莹儿发现爱情也只能作为一种暂时的幻觉,在饥渴交迫的生存需求下逐渐消失时,她几次想要放弃生的挣扎,把自己埋入黄沙,听天由命。与之不同的是,兰兰在困险面前表现出了冷静与坚定,她用枪和火在豺狗群中开辟出一条生路。在水和食物消耗殆尽时,努力寻找芦芽、锁阳等植物维持生命,也一次次把莹儿从死亡线上拉回来。当陷入流沙时,她并未表现出悲伤或恐惧,而是平静地将大漠的生存法则教给莹儿,“你最大的敌人就不是沙漠,而变成了你自己。”[1]301这是整部小说的核心主旨之所在,也正是隐含作者想要表达的一种无畏的道心。
小说通篇都在描述人在生命中面临的一道道“白虎关”,要摆脱生命的桎梏和险境,就需要以作者所言的“自己生命中真正焕发出来的光”彻照一切虚幻表象、障碍因缘,以坚定的道心壁绝攀跻。道心以信根为基础,信根即是人人本具的“自性”,也即作者所言的“自己生命的光”。若能保持对“自性”的信根无动转,则不畏生命中的万难千劫,烦恼妄想。以主体自性的独立、宁静、大自在追求生命的绝对自由,这也是作者想要找回的一种自我超越的精神,正如雪漠在小说后记中所写的,“这个时代,是一个众神缺席的时代,教徒们仍在顶礼膜拜,但被膜拜的神却不见了”。[1]501
参考文献:
[1] 雪漠. 白虎关[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
[2] 雪漠. 大漠三部曲:白虎关[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7.
——发表于《河西学院学报》第38卷第6期(2022)
作者简介:袁田野,女,江西萍乡人,北京语言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女性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