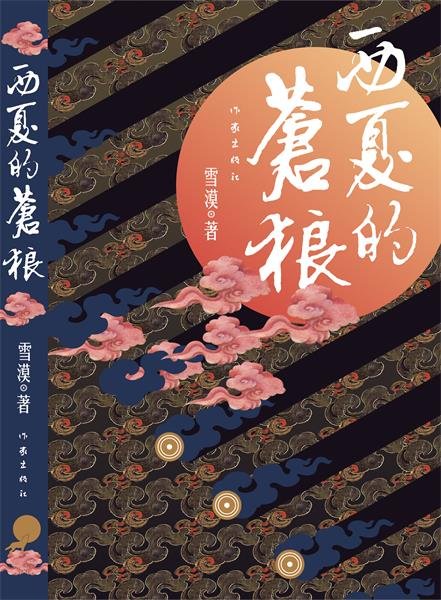
论《西夏的苍狼》中的象征
杨琪琪(90后,硕士研究生在读)
摘要:《西夏的苍狼》是作家雪漠的“灵魂三部曲”之一,其中出现多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信仰载体,成为作品中的核心文化元素。作品从现实空间转换到虚幻空间,塑造了多个人物形象,用超现实主义的手法展现了一个虚拟的西部神幻世界,也展现了作者对于世俗的超脱和对永恒追寻的理念。
雪漠作品一直主要以描绘西部文化为主要特征,而从《西夏咒》到《西夏的苍狼》开始,他的创作风格出现了转型,不再是以介绍西部文明为主,开始从乡土文学转向纯文学,作品主要内容也开始不再局限于西部,而是转向现代化文化视野。不同于他早期创作的《大漠祭》、《猎原》、《白虎关》(大漠三部曲)等描述西部乡土文明的现实主义作品,《西夏咒》、《西夏的苍狼》、《无死的金刚心》(灵魂三部曲)则是象征文学作品的体现,后期作者的创作风格逐渐转向带有西部宗教、信仰、传说等具有神秘文化倾向发展。[1](P128)以《西夏的苍狼》为例,他并没有局限于西部凉州,而是将视野扩大到南岭东莞一代,采用混合交叉式的地域性描写介绍了两个地方的习俗、宗教、信仰之间的异同,从关注现实的维度上升到关注精神世界。
《西夏的苍狼》分为两条主线、场景进行展开叙述,一条是以紫晓为主线,展现了她逃离现实生活,寻找内心安宁,追寻灵魂纯净的向往之地。另一条是以黑歌手为主线,展现了他寻找内心的“娑萨朗”,追寻永恒的精神家园。《西夏的苍狼》中现实场景和虚拟场景不断切换,叙述视角和叙述空间的频繁转换,甚至存在异时空的灵魂对话,让雪漠的作品具有先锋派文学的特色同时,又具有自己的写作风格。本文认为,雪漠以西部的文化视角为出发点,通过人物、环境以及空间的象征关系,来展现作者想要塑造的精神世界。
一、《西夏的苍狼》的环境象征
《西夏的苍狼》中的外在环境包括以紫晓为主的两个环境和以黑歌手为主的两个环境进行分开展述,且文中所具有的独特的西部文化元素更是极大的增强了作品中象征的隐喻性,更加凸显了作者塑造的双重世界的多元性和选择性。
《西夏的苍狼》中的环境象征主要包括与紫晓有关的两个环境,第一个是童年时期父亲营造的家庭环境,第二个是紫晓和常昊生活的樟木头。这是世俗中的两个典型环境代表,第一个是父亲营造的禁锢和压迫,世俗中无形的牢笼,是不自由的象征。第二个是紫晓逃出原生家庭之后,与常昊私奔至的樟木头,这里居住着形形色色的人们,这是我们现实世界的缩影,象征着浮华的现实世界。这两个环境是对现实生活的真实描绘,是世俗世界的象征。这里生活的形形色色的人们象征着混沌的现实世界,作者以紫晓为化身,将人们在混沌、浮躁现实中的挣扎状态显示出来,然后以第三者的姿态审视着这一切,渴望能找到一种答案,能让世间的苦难化为灵魂的自由。而紫晓在现实世界中的表现,则是作者想要传达给世人的想法。为挣脱世俗的枷锁,紫晓表现出追寻自由的反抗精神,寻找自由过程中的升华和救赎,继而获得生命存在的意义和最终的自由和快乐,是作者想要达到的终极目标。面对父亲压迫下的牢笼,她选择的对抗方式是逃离家庭,走上和父亲期望完全不同的道路,渴望追寻内心的自由,打破了父亲对于紫晓的美好期盼,这是紫晓的第一次自我救赎。在选择和常昊住在楠木头大杂院后,紫晓看似过上了自由放纵的生活,但后期常昊近乎禁锢式的爱情,尤其是婚姻也充满着政治意图时,这对于她那颗追求自由和安宁的心来说几乎是压迫式的威胁。所以她选择和常昊离婚,勇敢的追寻黑歌手和“娑萨朗”,释放自己的爱,选择自由,这是紫晓的第二次自我救赎。长期以往,紫晓在不断寻找灵魂的救赎,渴望获得自由和安宁。不论是父亲营造的生活环境,还是逃离居住的大杂院,都是作者笔下外在的现实表征,都是灵魂不安的源泉,更是禁锢人心灵的世俗象征。
以黑歌手为主的环境象征主要包括凉州城、“娑萨朗”。长久以往,西部一直存在着关于“娑萨朗”和奶格玛的完整文化,即光明大手印。光明大手印是从古印度传入中国,经过西部的同化和发展,在臧戏、凉州贤孝、民歌之中依然可以看见其精神文明传承的印迹。[2](P23)在《西夏的苍狼》中,黑歌手一直寻找的“娑萨朗”,紫晓踏上西部寻找的奶格玛文化,就是西部文化中的光明大手印。雪漠认为西部文化可以划分为西部民俗、民歌的物质层面的世间法文化,还有超脱物质外化的另一种追求心灵、灵魂、精神层面的超越文化,而光明大手印是西部的超越文化。紫晓和黑歌手都是受大手印文化的影响,他们是受者和传者的典型代表。紫晓曾两次受到指引去寻找内心的精神世界,第一次是受姐婆的影响,紫晓和常昊前往月亮潭,第一次踏上了寻找内心净土的旅程。第二次是受黑歌手的影响,在于黑歌手接触过程中,从信仰变成了一种爱,从而挣脱世俗一切去勇敢的追求爱,而这种爱是上升到灵魂的高度超脱的爱,是作者认为的大爱,正是这个过程使紫晓的灵魂得到真正的安宁。一直出现在黑歌手叙述中的“娑萨朗”和凉州城,是黑歌手心灵净土的象征。黑歌手从刚开始传唱《娑萨朗》,出现的不安,到后来的信服、感动,直到他将自己心中的爱用歌声传递出来,他是幸福的。在黑歌手的眼中,“娑萨朗”就是凉州城的镜化。在黑歌手踏上寻找“娑萨朗”的旅程前,他对凉州城有着特殊的感情,由于他的坚信和执着,在他的心中已经存在了一个关于凉州城的幻象,是一个存在于他追寻中的虚幻精神世界。以至于在最后,他跨域了时间和空间的界限找到了传说中的“娑萨朗”。黑歌手追寻的“娑萨朗”,是心灵的净土,是灵魂的救赎,是大爱的传承,这是他追求灵魂清凉的方式。雪漠认为不论是凉州城还是“娑萨朗”都是人们所向往的世界,想创造的东西,人们心中都存在着一个“娑萨朗”,是超越现实的一种心灵世界。这表明“娑萨朗”是每个人心中所塑造的精神世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幻化,是一种精神信仰。如果说“娑萨朗”是象征着精神世界的博物馆,那么凉州城就是博物馆中的活化石,凉州城象征着变化中的精神世界。[3](P76)所以,这里的“娑萨朗”不仅是现实生活中投影,也是心灵世界、精神世界的象征。
樟木头象征着世俗的现实世界和黑歌手追寻的“娑萨朗”象征着追寻的精神世界,在文中形成了强烈的反差。紫晓所在的世俗世界是灵魂不得安宁的源泉,是象征着权力、欲望、贪婪的牢笼,而黑歌手的“娑萨朗”,则是心灵的净土,是灵魂安歇的彼岸。《西夏的苍狼》中的外在环境象征具体两面性,一种象征着外在的压力和束缚,另一种象征着内心的释放和自由,其中的象征性的隐喻将作者的中心理念完美的展现出来。作者将自己的想法借黑歌手的传唱,把心中追求的理想传达给世界,希望黑歌手带给世界的是光明和自由,也希望世人能找到心中的“娑萨朗”,成为自己的救赎,让世人成为像黑歌手一样成为太阳,在生命中发光发热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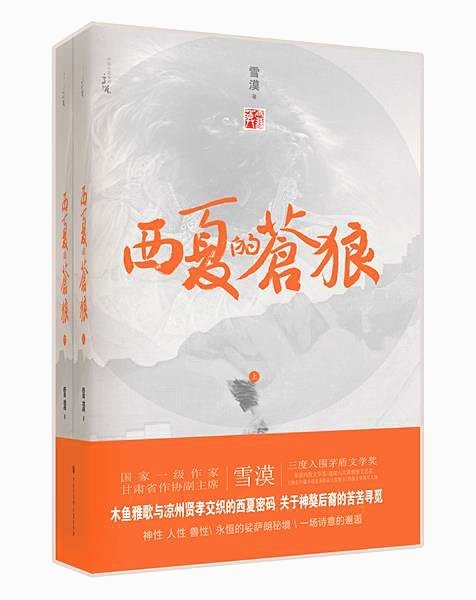
二、《西夏的苍狼》的人物象征
《西夏的苍狼》中也出现较多的人物象征,主要包括紫晓、黑歌手、白轻衣等其他相关联人物。紫晓作为主人公,不仅是全文的中心,也是作者想要传达的一种重要精神的体现。作者巧借紫晓的经历将他想要象征永恒的“娑萨朗”文化传递给世界。不同于被世俗中被权力、欲望、贪婪所侵蚀的人们,情节设定中紫晓在心灵和灵魂上的清明,是紫晓超脱现实和获得自由的必然性因素。尤其是在面对不安宁、不自由时,她表现出的反抗精神,更是作者想要追求的“清醒”。她没有在世俗中沉沦,懂得追寻灵魂的安宁,所以才可以一步步超脱现实。作为岭南人的紫晓在受到象征着西部文化元素木鱼歌的影响下,逐步前往西部寻找黑歌手和“娑萨朗”所代表的大手印文化,踏上了一场灵魂之旅。在这些已有的外在文化因素的影响下,紫晓和黑歌手有着一样的信仰,这成为她去寻找心灵慰藉的一种重要原因。在这个过程中紫晓已经成为了和黑歌手一样的朝圣者,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就是心灵永恒自由。这样的人物形象塑造,让紫晓既有现实社会的缩影,又有“娑萨朗”文化的光环。所以,紫晓既是现实社会的象征,也是一种智慧的象征。
文中还有很多与紫晓相关的人物,比如紫晓的父亲。由于无妄的牢狱之苦,父亲将他内心的怨恨发泄在紫晓和家人身上。父亲的刻板和怨恨让姐姐患上抑郁症,紫晓见证了父母的争吵,她的童年是不自由的,在这里父亲的形象是现实中的怨恨的象征;而父亲由于自己人生的失意,导致他对紫晓的教育是偏执的,甚至是压迫式的,这里父亲也是执念的象征;在樟木头里的靠杀鸡攒钱的老王爷,最后却掉进了粪池里淹死了,积攒的钱财被瓜分,这里的老王爷则是贪婪的象征;柳莺和梁子之间,注定柳莺的付出是得不到回报的爱情,这里他们之间则是欲望的象征;还有常副市长,在政治圈里的叱咤风云,在这里则是权力的象征。作者采用反讽的艺术手法将他们前后结局形成了对比,这些人并没有获得追求的“理想世界”,反而这些象征着怨恨、贪婪、欲望、权力的东西在最终都是消逝的结局。紫晓是父亲打磨的完美作品,但最终父亲却因为紫晓追求自由而导致美梦破灭,这是执念的幻灭;老王爷用尽一生力气积攒的钱财,却无福消受,自己却意外身亡,这是贪念的幻灭;柳莺将自己的积蓄供养着梁子,渴望获得爱情,最后是爱情的幻灭;常副市长在成为副市长之后,却因为一场车祸,失去了市长的职位,最终丧命,这是权力的幻灭。在作者笔下,这些在现实中的“追求”都指向了一个结局——虚无。作者认为现实世界中这些东西最终都会消逝,所有的一切都将会成为记忆,所以想要现实世界中寻找永恒,就必须创造出一个独一无二的精神世界。[4](P364-365)
而文中最重要的一个人物便是黑歌手,他在在文中是处于一种寻找永恒的状态。他是一个出生在现实世界,却拥有者超脱世人的大爱和悲悯之心,想要将自己心中的永恒播种到现实世界,渴望建造一个心灵城堡的朝圣者和指引者。黑歌手是人们心灵的向往的人,是自由和安宁的象征。他传唱的《娑萨朗》其实都是想向世人传达的大爱和自由,他追寻的“娑萨朗”是一种心灵向往的精神世界。黑歌手虽然是黑将军的精神载体,但是和黑将军相比又有所不同,他拥有着一种现代文明,是黑将军精神进化发展的继承和传播者,同时他也是被作者赋予了新时代文明的精神寄托,是作者精神的具体显现。作者认为黑歌手是西部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和宗教精神的综合体,他是一种全新思想的象征。雪漠曾说,这世界需要一种声音,需要像黑歌手这样的人,将心中的大爱、巨大的悲悯、怜爱传达给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让人的心灵得到震撼,让人的浮躁得以消解,让每个人都得到爱,这是雪漠所想要创造的精神世界,而黑歌手则是连接现实世界和精神世界的纽带,指引人们追求大善、大美、追逐灵魂的解放,寻求内心的欢乐和幸福,也是一种大爱的象征。
在文中也有一直出现的白轻衣,她出现在紫晓的日记中,出现在黑歌手的梦中,出现在博物馆中。在紫晓日记中关于白轻衣的记叙,白轻衣自己的自述以及黑歌手的叙述形成了一个完整叙事结构,而最终她们的叙述都指向永恒。这种在结构上形成的“复调”,更加明确了作者的指向。从白轻衣的叙述中,她引导着紫晓和黑歌手的相遇,让紫晓找到信仰的道路和追寻的精神世界,紫晓遇到黑歌手后所达到的释然,使她的灵魂得归于宁静。白轻衣可以是魂魄,可以是紫晓的另一个化身,也可以是黑歌手梦中的女子。在白轻衣在和黑歌手的对话中,她讲述了在世俗中受的痛苦和失落,这时的白轻衣是世俗受苦难的世人象征,而黑歌手于她就是苦难中的光明,是救赎的唯一道路。白轻衣也告诉黑歌手,这个世界不仅需要一个真正的黑歌手,也需要一个行者,需要黑歌手成为一个有完美人格的人,这样“娑萨朗”才更有意义,这样的黑歌手才是世人眼中的烛光。黑歌手在遇到白轻衣之后,他的心境也明显发生了变化。在黑歌手的自述中:“我的生命便是因为这白衣女子而变成了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我是歌手;后一阶段,我是不着袈裟的苦行僧。……此前,我知道自己不需要戒律,因为我觉得自己不会犯戒。此后,我却觉得自己需要戒律,因为这个世界需要我这样。我要让世界看到一个真正的黑歌手,一个真正的《娑萨朗》的代言人。”[4](P292)这里的白轻衣对于黑歌手而言,是牵引着他继续追寻“娑萨朗”的信念,同时也赋予了黑歌手存在的理由,让黑歌手继续在歌唱《娑萨朗》的道路上寻找真理,传播光明和快乐。在这里的白轻衣是紫晓和黑歌手朝圣的指引者,是象征着人们追寻真理道路上的指明灯。
正是由于有了世俗环境中人们苦难、欲望的象征,黑歌手和“娑萨朗”所追寻超越世界的象征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样的反差让黑歌手和“娑萨朗”的存在才更有意义,更能体现作者塑造理想世界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三、《西夏的苍狼》所塑造的精神世界
从文学地理学的角度,文学作品一般会受地域文化上的宗教信仰、文化习俗的影响,显示出浓厚的地域文学色彩,而《西夏的苍狼》则是将西部和南部的文化和宗教信仰结合起来,建造了一个超脱于现实世界之外的“娑萨朗”。故事主线从主人公紫晓为主的现实世界到以黑歌手为主的虚幻世界不断转换,具有了神灵结合的超现实主义色彩,最终实现用宗教和信仰来达到灵魂的救赎,将宇宙奥妙和生命的意义归结于自身的超脱,这是作者塑造的独特精神世界。
作品中的人物象征和环境象征都饱含着丰富的韵味,作者将这些象征延伸到一种精神文化追求之上是《西夏的苍狼》要传达的精神理念。在俗世中,紫晓是无法安宁的状态象征着心灵浮躁,找不到存在价值的人们,他们失去了人本身所具有的纯真和质朴。而黑歌手所在的世界是超脱于现实世界之外的精神文化象征,是一种救赎的希望象征,是一种精神寄托。紫晓所处的环境使她作一个朝圣者的姿态在不断追寻自由和灵魂的清凉,在现实生活中逐渐实现超越,寻找自由和幸福。紫晓寻找的苍狼与黑歌手寻找的“娑萨朗”以及奶格玛寻找的永恒在本质上一样的,都是在追寻自由的栖息地,追寻精神上的永恒。这种精神不仅是生命延续的需要,也是灵魂滋养的需要。
在西部文明中,光明大手印一直广为流传,是西部文明的重要元素。而雪漠笔下的光明大手印不仅仅是局限于宗教信仰,而是将其脱离了宗教形式,成为了他心中一种理想净土的代表,是一种心灵上的慰藉,是一种永恒和自由的象征。雪漠说道:“大手印哲学中,永远是以塑造自己的灵魂为主。这个“灵魂”的“灵”字就是我们谈到的“灵性”,文学真正追求的正是这个东西。灵性和灵魂跟物质关系不大,当人类基本的生存条件满足之后,幸福、自由、快乐都取决于心灵的明白与否。”[4](P366)这里紫晓和黑歌手自述中的永恒便跨越了时间、空间,他们的情感、命运、追寻糅合在一个整体故事中,塑造了一个超脱世俗之外的精神世界。这里精神世界是以“娑萨朗”为代表的一种超脱意识,有着分外的包容、慈悲、大爱、怜悯,是世人追求的灵魂安宁和苦难消解之地。而这种精神世界不是传统的宗教信仰,是作者从大光明手印中汲取到的精神,是以“娑萨朗”的方式存在人们的灵魂深处,是可以消解内心的贪恋、愚昧和仇恨,是将西部文化传承结合起来的一种新的文化符号。《西夏的苍狼》中共同塑造的“娑萨朗”不仅是西部文化的传承,更是作者的精神信仰,是作者追求超越现实和欲望的一种精神世界。作者也表示希望用文学带给人们心灵的滋润,让浮躁归于宁静,“娑萨朗”就是作者塑造的安宁之所,这就是作者塑造的精神世界的核心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1]贺仲明:《从“肉”到“灵”从“他”到“我”:评雪漠近年来的小说及创作转型》,《当代作家评论》,2018年3月。
[2]孙英:《论雪漠文学创作及其时代精神》 ,《兰州大学》,2012年5月。
[3]鲍秀文、张鑫:《论石黑一雄〈长日留痕〉中的象征》,《外国文学研究》,2009年3月。
[4]雪漠:《西夏的苍狼》,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