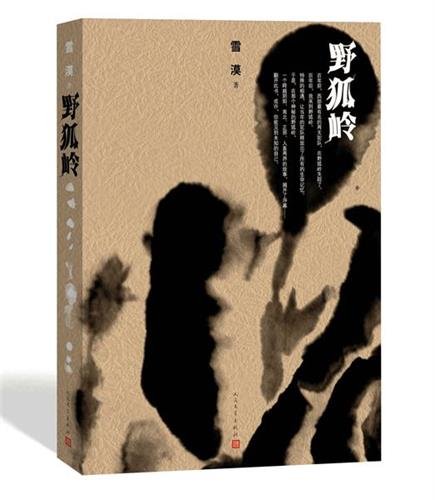
从苦难中觉悟——雪漠小说中女性形象的一次超越
文\刘楠
[摘要]在雪漠新作《野狐岭》中,莹儿、兰兰、月儿、豁子女人、雪羽儿、紫晓、木鱼妹是雪漠笔下典型的女性形象,她们集温柔、善良、坚韧于自身。一方面,在男权社会的桎梏下,女性自身的奴性地位和极度的贫穷状况,使得她们承受着巨大的苦难与不幸;另一方面,雪漠并非一味地书写苦难,而是让雪羽儿、紫晓、木鱼妹在爱与宗教的滋养下实现证悟,从而摆脱苦难,实现超越。
雪漠的小说为读者塑造了一系列震撼人心的女性形象,不论是“大漠三部曲”、“灵魂三部曲”,还是雪漠最新力作《野狐岭》中的女性,她们遭受的苦难令人反思:女性为什么总是不幸的载体,为什么不得不去承担超负荷的苦难?当然苦难并没有摧毁这些女性寻找解脱之道的意志,也没有使她们停止改变自身命运的脚步。雪漠在“大漠三部曲”之后的“灵魂三部曲”以及新作《野狐岭》里,刻画了一群由“寻觅”到“解脱”的女性。这些女性经历了无尽的苦难后最终逃离,她们找到了活着的价值与意义,从无望到觉悟,实现了生命的升华与超越,这或许也是雪漠本人的超越。在《西夏咒》后记中雪漠说:“我可悲地发现,一切都没有意义,……于是,我曾许久地万念俱灰。这种幻灭感的改变在我接触到佛教之后。”[1]
一、深陷苦难与不幸的泥淖
雪漠笔下的女性无一例外地遭受了巨大的苦难。如“大漠三部曲”中晶莹剔透的莹儿,为了哥哥白福的婚姻牺牲了自己的感情,换亲给老实憨厚、患有阳痿的憨头,这是她苦难的开始,也为她与小叔子灵官偷情寻欢埋下了由头。悖逆纲常的媾和给她带来的愉悦终究是短暂的,灵官最后的出走终止了她的幸福。天真的莹儿本想靠着对灵官的爱和盼盼安稳度日,但现实打碎了她的梦想,她不是被自己的婆婆要求嫁给灵官的二哥,就是被自己的母亲逼迫着嫁给一个打跑了自己媳妇的屠夫。就像一件物品似的,她被别人掌控着归属权,自己没有选择生活的权利。但她并没有妥协,她与嫂子兰兰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徒步穿越大沙漠,历经千难万险与生死考验,终于抵达盐场。她希望换回哥哥再娶妻的彩礼钱,以改变自己再次被交换的命运,但美好的愿望却被现实撞得粉碎。一个纤弱的女子却从事着超负荷的繁重劳动,最后不仅没有赚得“赎身”钱,反而被沙漠里的豺狗子吃掉了一峰驼。但她依然顽强地去赚钱,尽管愿望仍旧没有实现。最后,她依然没有放弃,穿上嫁衣嫁给了屠夫,选择了以死抵抗,“我知道,不能涅槃的我,只有幻灭了”[2]
在新作《野狐岭》中雪漠以浓墨重彩刻画的女性——木鱼妹,也是饱尝苦难和艰辛。为了使疼爱自己的阿爸能买得起他自认为珍贵的木鱼书,将自己嫁给了脑子不清楚的驴二爷的小儿子,充当着照顾他的丫环。面对驴二爷的色欲,木鱼妹将自己给了当时爱的人——驼把式大嘴哥。正当她陷入幸福的眩晕中时,却被她的小丈夫捉奸在床,慌乱中他们杀害了那条生命,这也是她不幸生活的真正开始。接着她的全家被大火烧成了灰烬,她也由此满怀仇恨,走上复仇之路。一个女子从中国东南的广东东莞徒步走到了西北的甘肃凉州,如她所言,“在千里的途中,我遭遇了很多事,多次挣扎在生死线上”[3]。为了报仇,她毅然用“肮脏”遮蔽了美丽的容颜,日夜不间断地苦练能杀死仇人的武功。一次次刺杀,屡败屡战。令人叹息的是,命运之轮并没有向她倾斜,家仇未报的她竟然深爱上了仇家的儿子——她所刺杀的对象马在波,这使她陷入矛盾的漩涡而无法自拔。
无论是“大漠三部曲”中的女性,如温柔善良的兰兰、纯洁美丽的月儿、有情有义的豁子女人,还是“灵魂三部曲”《西夏咒》中行侠仗义的雪羽儿,《西夏的苍狼》中小家碧玉的紫晓,她们命运的起点都是不幸的,经历了无尽的苦难,甚至与死神擦肩而过,但“苦难,压不垮凉州女人”[4],她们并未因此就甘愿承受这样的苦难与不幸,而是凭借着她们从西部土壤里生长出的坚韧与苦难相抗争。这正是西部女性的真实写照,即便遭遇再大的苦难也不轻易向命运屈服。
二、超然出世,实现觉悟
从“灵魂三部曲”第一部《西夏咒》开始,雪漠具有“灵性”的笔便终结了女性的悲剧命运,在追寻中实现证悟,超越苦难。如《西夏咒》中的雪羽儿,在经历了为拯救濒临饿死的族人而使母亲被族人煮食、经历了自己差点被制造成宗教法器的皮子之后终于觉悟了。世俗之人凭借着行侠仗义是无法被救赎的,他们不会忏悔自己犯下的罪恶。她最终选择与琼双修,放下执著,出世修炼,证悟得道,“终而打破了欲望魔咒,升华为西部文化中的智慧图腾”[5]。《西夏的苍狼》中的紫晓,在寻觅苍狼和黑歌手的过程中,渐悟到家人、爱人对她所谓的爱其实并不是爱,而是对她身体的桎梏、心灵的摧残和灵魂的操控。于是她看破了世俗的一切,超然出世,摆脱烦恼与牵绊,追随黑歌手的脚步,共同寻觅心中的圣地娑萨朗,走向朝圣之路。
在《野狐岭》中,复仇的意志起初支撑着木鱼妹的生命,为了报仇,她经历了常人无法想象的苦难。可是从小烂熟于心的木鱼歌如咒子般不断消解着她的仇恨,她不得不每日修炼仇恨,用仇恨化解心中的善。正是由于这善的牵引,她一次次错失刺杀仇家驴二爷的绝佳时机。如,她怕破坏驼羊会的喜庆味,不想败了父老们好不容易得来的兴,便没对仇人下手。如,在大年初一,她不想摧毁当地人在乎的缘起——“要是在大年初一不顺利,一年会不开心的”[2]167,于是再次错失良机。这木鱼歌如同佛语劝她放下仇恨,释放善心。并且随着与纯净、虔诚的佛教徒马在波接触频繁和深入后,她心中的善更是日渐苏醒,日趋强大,以至于仇恨渐渐式微,她不得不逼迫自己铭记恨意。她在野狐岭面对着世界末日的降临,面对着仇人的儿子,却突然发现自己根本下不了手,连报仇的念头都在不知不觉中生不出来,甚至因仇家几缕淋漓的血而抽疼了自己的心。她证悟了,将自己从仇恨中解脱出来,实现了自我超越,最终和自己所爱的人,即自己的仇人马在波携手幸福的生活。澄心洁虑后的木鱼妹与马在波重回野狐岭潜心修行,参悟人生,升华自己,最终迎来了安宁、平和的后半生。
“灵魂三部曲”中的雪羽儿、紫晓和《野狐岭》里的木鱼妹们所经受的苦难仅仅是她们漫漫人生之路中的一段前奏与插曲,在不幸中,她们因某种机缘实现了觉悟,洞悉了生命的真相,证悟到是执著让她们迷失,让她们深陷苦难的泥淖不能自拔。在对信仰的求索中和对灵魂的叩问中,她们找到了解脱的方式。放下执念,释怀执著,超越自我,最终把自己从无尽的苦难中拯救出来。相对于只有苦难的莹儿、兰兰、月儿等,她们是幸运的。
三、苦难的深层根源
隐藏在女性苦难背后最根本的原因是女性几千年来的奴性地位。在男权思想的支配下,女性附庸于男性,成为男性的玩物。在婚姻选择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使得女性没有选择自己婚姻的权利,如莹儿、兰兰、木鱼妹。莹儿、兰兰为了各自哥哥的婚姻而换亲,给和自己没有感情基础的人当媳妇,而且在兰兰要结束与莹儿哥哥婚姻的时候,莹儿母亲为了给儿子再找一个媳妇不顾莹儿的意愿,便将莹儿许配给了有暴力倾向、且是最被人看不起的屠夫,最终导致莹儿的陨灭。“从父母看来‘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父母要完成的是他们的使命,于是不自觉地依循祖上传下来的规矩选择了换亲,然而女性却成了婚姻交换的工具和手段。”[6]在父母眼里,女儿成了可以用来交换的物品,而不是人。在婚姻生活中,女性依附于男性,被男性所掌控,没有独立的空间,只能乐而从之。如紫晓在和常昊的婚姻生活中,如一只绳牵的蚂蚱,被常昊掌控,丝毫没有自由。更可怕的是,起初她竟然以为是常昊对自己爱得太深和对自己过于依赖所致。月儿,一个本想在城市中寻找出路的有梦想的女孩,终因自己的弱小而不得不在绝望、痛苦中走向沉沦,导致自己悲剧的一生。社会更是一个弱肉强食的地方,一个柔弱的女性想在社会上立足谈何容易。
贫穷也是导致她们苦难的原因之一。一方面,中国西部的自然环境恶劣,物质的匮乏操纵着贫困地区人们的生活。他们无法改变现状,从而招致许多悲剧的发生。“可以看见贫穷像一个无法摆脱的梦魇,几乎所有的不幸都与它有关。”[7]女性婚姻的不幸便是其一,若不是因为穷,莹儿不可能为了哥哥娶不起媳妇而换亲,更不会为了给哥哥凑彩礼钱而历经生死磨难横穿沙漠去盐场驮盐。若不是因为穷,聪颖美丽的木鱼妹不会甘心嫁给驴二爷的憨儿子充当丫环。若不是因为穷,月儿不可能想着去城市寻找改变命运的出路,最终将自己葬送在城市。若不是因为穷,雪羽儿不会偷族里的羊去拯救快要饿死的母亲,而被迫藏在老山深处躲避惩罚。另一方面,与现实的物质世界相对应,女性的精神世界也是极度贫乏的,心灵的无着使得处于苦难的女性找不到继续生存下去的方向,找不到可以发泄怨恨的方式和活着的意义,不得已只能用死亡来求得解脱,这使得对现实绝望的女性,不得不通过极端的方式应对使自己愈陷愈深的苦难。莹儿,因为找不到其他可以改变现状的方法而最终选择吞噬鸦片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紫晓为了报复父亲的专断,而毅然决然地跟随给自己带来暂时快乐的常昊私奔,放弃自己原有的生活,走上苦难之途。
四、实现超越的缘由
爱,是女性摆脱苦难、实现超越的一个缘由。给人带来温暖与慰藉的爱使女性从生活的苦难中逃离出来,虽然物质上可能依旧贫乏,但精神上却可以得到满足。如,雪羽儿与修行者琼的爱情、紫晓与黑歌手的爱情、木鱼妹与马在波的爱情。正是这种爱,使这三位女性不再痛苦、不再孤独、不再仇恨。她们因爱的滋养而忘却了曾经历的苦难与折磨,体悟到人世间的美好与幸福。雪羽儿因与琼的爱情的滋养,在“她的脸上,写满了巨大的幸福”[8]。刻骨铭心的木鱼歌时刻为木鱼妹传递着爱,软化了她僵冷的心,消解了她心里的恨,使她不得不通过加倍的修炼来铭记不断被消解的仇恨。但同时,她对仇人马在波的爱又使她放下了仇恨,最终与之相濡以沫,潜心修行,走完一生,表面虽然看似平淡,但实则充实而有价值。是爱化解了矛盾,化解了仇恨,爱使这些女性充盈地直面生活。爱终结了苦难,开启了新的生活,在爱的滋润下她们幸福地走向光明的彼岸。
作为虔诚的佛教信仰者的雪漠,他在小说中为读者呈现了另一种女性超越的缘起,这便是宗教。不论是雪羽儿、紫晓,还是木鱼妹,她们爱上的男人都是虔诚的宗教修行者,在与这些人的接触中,她们翻看经书,开始对未知世界进行探索,最终求得证悟,皈依佛门,超度修行。从此她们远离了苦难,远离了尘世的喧嚣。如紫晓,她在追寻黑歌手的过程中,通过对灵魂的追求,最终“进入了一个‘最自由最隐蔽最神秘的世界’———信仰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紫晓的物欲被消解,灵魂得以净化而归于安宁和澄澈”[9]。木鱼妹也是如此,
她在潜移默化中受着一心向佛的马在波的熏染,只是她自己并没有察觉到,和那木鱼歌传递的善一样,她的仇恨渐渐地消解,最终放下并得以解脱。这些女性在静心修炼中逐渐去除了对世俗世界的执念,消解了欲望与仇恨,离苦得乐,获得了生存的精神动力和信心,求得了内在精神世界的解脱,放下对世俗的依恋,转而在宗教中找到了一条解脱之路,升华了人格,重铸了灵魂,为自己的灵魂找到了依怙。
五、结语
雪漠小说中的女性也是旧时代女性群体中的一个缩影。虽然雪漠为书中女性提供了两种解脱方式,但这是否能使女性最终脱离苦难与不公的境遇,还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
[参考文献]
[1]雪漠,《谈“打碎”和“超越”(〈西夏咒〉代后记)》,作家出版社,2010年第436页。
[2]雪漠,《白虎关》,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出版。
[3]雪漠,《野狐岭》,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出版第140页。
[4]雪漠,《凉州女人》,《延安文学》,2003年第05期第121页。
[5]雪漠,《光明大手印:文学朝圣:上卷 》,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出版第189页。
[6]许心宏,《基于空间诗学的女性书写与悲剧意识———从雪漠“大漠小说”的女性意象说起》,《华北电力大学学报》,2013年第06 期第115页。
[7]何清,《论雪漠小说的现实关怀精神》,《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06期第54页。
[8]雪漠,《西夏咒》,作家出版社,2010年出版第408页。
[9]陈永有,《<西夏的苍狼>:灵魂的清凉之旅》,《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12年第05期第8页。
——刊于甘肃广播电视大学学报第25卷第2期2015年4月
雪漠文化网,智慧更清凉!www.xuemo.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