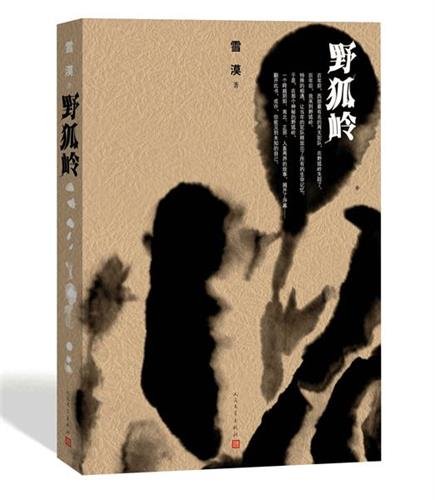
《野狐岭》 雪漠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7月出版
雷达:小说的“玩”与反小说
——2014年10月19日雪漠《野狐岭》中国作家协会研讨发言
《野狐岭》延续了雪漠小说一贯的主题,就是西部文化,包括西部的存在、苦难、生死、欲望、复仇、反抗等这些东西,而像《大漠祭》《白虎关》里那种大爱的东西,倒是有一点点淡化了,由大爱走向了隐喻。作者创作的意图很明显,要写一个真实的中国,定格一个即将消失的农业文明时代,这是他一贯创作中很重要的东西,其中很多东西,讲到了西部文化、沙漠文化、西部的传说、西部的神话、西部的民谣等等。当然,其中也包含了人和自然的关系,比如对骆驼的描写,骆驼怎么生殖,骆驼的死,都非常精彩。这部小说,你说它的主题是什么?很难说,但有启蒙的意义在里面。比如,小说里反复出现的一句话,像齐飞卿说的: “凉州百姓,合该受穷。”这实质上是对看客文化和麻木不仁的灵魂的一种批判。
其次,《野狐岭》突出了雪漠小说形式创新的追求。雪漠说,他要好好地“玩”一下小说,大家看他的后记应该注意到这一点,看它在雪漠的手里玩出个啥花样。玩小说本身的快乐,他着重强调创作本身的快乐,是一种非功利性状态下的心灵飞翔。他的“玩”主要是从小说的结构和形式上来着眼,这是更重要的特点。
从整体上看,全书有二十七会,这是比较独特的。首先,在当代文学史上,张承志的《心灵史》,以门来构成,其他长篇小说则基本以章、节为构成单位。独特的小说结构体现出雪漠创新的努力。从某种程度上看,小说的结构就是作家对世界的一种把握方式。雪漠的“灵魂三部曲”一度被看作是走火入魔,重要的原因在于,作者对宗教和灵魂超越的过分强调。《野狐岭》试验性的结构其实也是作家世界观的一个体现,以幽灵的集会与全化身来完成长篇小说的结构,有相当大的写作难度,这是我重点强调的。第二,以嘈杂错综的声音构成一部长篇,也可以说,《野狐岭》这部小说是由声音构成的。总体看来,小说每一会都以“我”的处境与幽灵们的叙述构成,而“我”的叙述节奏总是和幽灵的回忆有着某种内在的关联性和结合性,但实际上,不是只有两个声音,其实更复杂。小说内部构成单元的会,意味着聚会、领会、幸会,即意味着小说中所包含的各色幽灵的相遇。聚会、集会,本身就意味着小说的复杂性和多重性。《野狐岭》是适应这个时代的,如书中无形的杀手、痴迷木鱼歌的书生、复仇的女子、杀人的土匪、驼把式等,还有心思堪与人相比的骆驼,他把骆驼写得和人一样,而小说在此基础上加上了一个活在现实中的“我”,将他们串联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极其复杂而混沌的世界。
第三点,三个特殊人物值得注意: 第一,“我”。“我”在小说中表面看来是为了探寻百年前在西部最有名的两个驼队的消失之谜,但,“我”是灵魂的采访者、倾听者。“我”为了实现灵魂集会,并采访他们,来到了野狐岭。“我”在倾听幽灵叙述时,总想到“我”的前世,“我”没有弄清“我”的前世是谁,但“我”觉得那些被采访者可能是“我”。“我”的前世究竟是谁,这使得小说上升到一个哲学的层面,拓展了小说的思考空间。小说中的“我”在阴阳两界之间,喝了很多阴间的水,但最后还是活在人世上。采访结束之后,“我”发现他们开始融入“我”的生命,一个个当下都会成为过去,所以为了“我”的将来,“我”会过好每一个当下。齐飞卿,这样的民族英雄活在了传说中,而“我”却珍惜当下。第二,杀手。小说中出现的第一个幽灵就是杀手,他的面貌从来都是不清晰的,“我”完全可以通过“我”的法力来开启他的面目,但是“我”不想,这完全是一个现代主义的表现方法。其实,这个杀手可能是野狐岭上的一个幽灵,可能是木鱼妹人性中的幽灵,也可能是“我”,而小说中一直跟着“我”的狼也是一个象征的影像,它是每个人心中黑暗的表现。第三,木鱼妹,从岭南来到凉州,经历与亲人的生离死别,与仇家之子刻骨的爱情。小说中寻找的木鱼令,究竟是什么? 雪漠在书里没有明说。
雪漠讲到的很多东西都是说不清,道不明的,所以我在阅读的过程中经常会生起一个疑问,作者到底要表达什么? 说不清,道不明,这可能是一种追求。但,这个追求是什么? 作者也讲了,他不要主题,也不刻意追求什么,他不弘法,也不载道。
另外,这部小说充满了一种反小说的表现,碎片化的叙述,人物都是模糊的,不是像现实主义文学要求的人物性格刻画得很鲜明,没有一个完整的故事。现实主义和美学主义还有一个完整的故事,一个贯彻的意味,但在雪漠的小说里,这些都没有。所以,这部小说不是一个简单意义上的故事,特色性非常强。
——刊于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第28卷(总153期)
雪漠文化网,智慧更清凉!www.xuemo.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