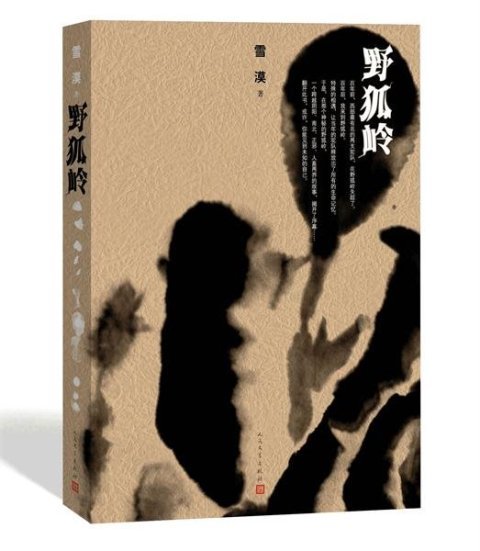
《野狐岭》的超越叙事与复合结构(2)
文\程对山
四
《野狐岭》汇聚了最不可思议的奇迹和最纯正的西部原生态的现实生活,借助“生死轮回”和人鬼共存的“二元世界”的神奇性,描绘了发生于西部大漠的离奇怪诞、神秘莫测的故事,从而产生出一种强烈吸引读者的似真似幻的艺术效果。一般常见的小说是以情节的流动构成人物性格成长的历史轨迹,即以情节的发展当作塑造人物典型的传统手段。而《野狐岭》的表现方式中没有由初始到完整的人物命运的发展趋势,而是以人物的叙述带出或推动情节,再以不相联属的板块化的情节片断拼结聚合出人物的性格特点。如前所述,这里面的人物不是现实生活中的正常人物,而是一个一个的鬼魂。《野狐岭》超越叙事的基点就是通过“能断空行母”传下来的古老的招魂方式召请来的鬼魂叙述还原了与野狐岭有关的传说故事。雪漠不是把鬼魂的活动当作真实来表现,而是把那个特定的苦难岁月里的现实当作幽冥世界里的故事来描述,因而才营造出吸引读者的似真似幻的神奇效果。此前已述,《野狐岭》之所以具有超越叙事的美感特征就是因为小说中确实存在一个“超叙事者”。《野狐岭》中的幽冥世界也就有了一种“超叙事者”刻意安排的假设秩序,把混乱无序的鬼魂活动纳入到假设秩序中,构成了作家贯通人鬼两隔的“二元世界”而精心建造的寓言模式,人们从中看到“鬼界”和“人界”的联系,并且启迪读者试图在虚华浮俗的生活现实中找到新的灵魂依怙的精神殿堂。
雷达指出,《野狐岭》“把侦破、悬疑、推理的元素植入文本,把两个驼队的神秘失踪讲得云谲波诡,风生水起。其对生命价值和意义的深刻思考,超越了写实,走向了寓言化和象征化”[10]。可以说,正是寓言化和象征化使《野狐岭》打上了超越叙事的烙印。于是,《野狐岭》中的人物形象颇具卡夫卡笔下人物形象的模糊与荒诞特征,人物生存场景迅速变幻的不确定性,人物性格成长过程的跳跃感和片断化,使《野狐岭》极具一种寓言和童话体式,带有一种支离破碎的沧桑之美。雪漠自己也说,“(《野狐岭》)甚至在追求一种残缺美。因为它是由很多幽魂叙述的,我有意留下了一些支离破碎的片段”。并指出《野狐岭》中的人物“其实是一个个未完成体。他们只是一颗颗种子,也许刚刚发芽或是开花,还没长成树呢。因为,他们在本书中叙述的时候,仍处于生命的某个不确定的时刻,他们仍是一个个没有明白的灵魂”[11]416。由于昔日的君子小人,志士凡夫已成鬼魂,鬼魂的叙事方式则自然带有“鬼魂”的明显特点。那就是前言不搭后语、破空而来、游移无定和断续无迹等。只有鬼魂才能听得懂鬼魂的声音,所以召魂时的“我”也就变成了鬼魂,读者随着阅读走进鬼魂的叙述故事时,仿佛也成了置身于幽冥世界中的鬼魂。这真是一场奇特的阅读体验,阅读中没有了作者,没有了读者,没有了人形,没有了一切……天地混沌一片,眼前只剩下野狐岭。《野狐岭》运用超越叙事的语言外壳,恰当地表现了西部大漠中充满神秘怪异、荒诞离奇的细节,并将野狐岭的凶险现象与胡家磨房的神话传说纠结在一起,表现出那个特定年代里社会生活动荡激烈,大自然异乎寻常的神奇怪诞的生活现实。
五
雪漠反复强调,《野狐岭》是一群糊涂鬼的呓语,是一个巨大的、混沌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存在,还有那混沌一团的剪不断理还乱的氛围,是一个充满了迷雾的世界。读者阅读时,也确实有这样的悬疑惊讶、探险神往的“挑战阅读智力”的感觉。但可以肯定的是,作家进行文学创作时,任何时候都有一种冷静的敏锐的“清醒意识”,雪漠当然也不例外。雪漠说“《野狐岭》跟《西夏咒》一样,是内容和境界决定了文学形式的产物”[12]417,《野狐岭》因为具备 “超叙事者”的清醒意识,将混沌气息串成片断,再将片断故事粘合成电影“蒙太奇”画面,最终给读者以立体的浮雕般的质感。就文本表述特征而言,《野狐岭》中以“鬼魂”为特征的人物形象其实是清晰分明的,而且作者也精心地设置了内容前后关联排列的“假设秩序”,完整的纪录了那个已经消失了的特定时代里人们生存的记忆和情绪。雪漠在“清醒意识”的支撑下,精心策划了《野狐岭》的艺术结构,如上所述的“假设秩序”可以看作是这种艺术结构的具象化体现。如果说,小说的叙事语言是标识作家艺术风格的重要密码,而小说结构框架的匠心创设,则反映出作家驾驭小说文本的创作能力和艺术造诣。如果忽略了小说的结构,那故事就只能是一般的故事而已,而非超越叙事的鸿篇巨制。什么时候语言和结构都是构成小说的最基本要素,因“西部写生”而打上现实主义创作烙印的雪漠肯定也深谙这些要素。所以,《野狐岭》采用了与超越叙事方式相匹配的独特的复合结构。这种复合结构在文本表现中,又呈现出心理杂糅和情节环包的两种结构类型。
雪漠不像传统作家那样强调故事本身,而是强调讲故事的人,作为叙事人“我”的形象在作品中有一种刻意化的突出与强调。于是,“我”时而飘忽、时而凝重、时而情绪化、时而哲理感的层面复杂的心理特征与鬼魂们有的愚痴、有的睿智、有的糊涂、有的明白的多重类型的心理状态搅成一团,构成了云遮雾罩、层叠堆磊的心理杂糅结构。比如《引子》中的“我”是一位跟着上师修成了“宿命通”的修行者,所以才有了和“鬼魂们”的“二十七会”,而在每一“会”中,“我”既是故事的叙述者,又是故事的参与者,甚至和那些阴冷的“鬼魂”产生了温热的感情共鸣。如第三会《阿爸的木鱼歌》中,当大嘴哥将马二爷欺负了阿妈的事告诉阿爸之后,木鱼妹讲述“阿爸的天就灰了”之后,她的叙述也就结束了。作者紧跟着描述了“我”的心理和情绪状态——
木鱼妹忽然寂了。/我感觉到她在哭泣。风吹来,在柴棵间扫出声音,噎噎的。/我说不下去了。木鱼妹说。/不要紧。我说,我可以等/。她说她难受极了。没想到,过去了这么长的时间,一想到往事,仍是这么难受。她说,多年来,她一直压抑着那种难受,她尽量不去想。她把那个皮球压了许久,但在生命的记忆中,它并没有消失。/我发现,东边的那线月儿亮了些,天上的星星在哗哗。我能听到那种水一样的哗哗声。那是天河水吗?还是另一些生命在喧嚣?[13]50
这里的“我”似乎忘记了自己是故事的讲述者,置身冥界,身临其境,描写中浸渗着浓郁的悲悯感伤情调,场景描述清丽婉约且富有人间的温度与气息,竟然能牵出读者隐然的泪意。在第五会《祖屋》中,大嘴哥叙述了和木鱼妹“见天日”之后,作者让“我”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发表了一段生硬的如同蛇足般的评论:“因为那是一种仪式。那仪式象征着彼此进入了对方的生命,结成了一种生命的契约”。以至于大嘴哥都及时进行了极不满意的制止:“先生,请别打岔。那时,我根本不知道啥仪式,我觉得她是我的心头肉”[14]92。但是,这段看似“蛇足般的评论”使“我”具有了“超叙事者”的社会评判角色的优越高度。在每一“会”中,“我”都以不同的角色参与其中,“我”有时候是故事的叙述者,所以冷静清醒、无动于衷。有时候“我”是站在故事边上的观察者,忍不住还要发出哲人般的评价判断。有时候“我”又成了故事中的角色,不自觉地沉溺于人物的喜怒哀乐中。随着故事情节的演进,叙事者“我”将自己的内心世界也逐一展示在读者面前。以至于在第二十七会《活在传说里》,“我”甚至产生了留下来的冲动,为了使这些故事不致于在岁月里消失的使命感,“我”终于走出了野狐岭。“我”以召请鬼魂的方式发现了故事,又融入到故事中,最后因为固有的使命感而又走出了那个魔幻神奇的故事。作者善于在不同情景的对比中描写人物的行动和内心世界,在固化的社会背景里插入细致的心理分析与灵魂剖白,于是,叙事者“我”的复杂心理层面与故事中“鬼魂”的多重心理类型扭结在一起,形成一种云遮雾罩、层叠堆磊的繁冗而杂糅的心理结构,使《野狐岭》又体现出与传统现实主义创作风格的明显差别。
六
因为选择了超越叙事的表现手法,《野狐岭》既有一种繁冗而杂糅的心理结构,又具备一种独特的情节环包结构。此前曾述,《野狐岭》没有传统小说那样一气呵成的连贯情节,小说中的人物是现实中的“我”和曾经在野狐岭中的鬼魂相遇。作者讲述他们在野狐岭中的遭遇,而这些鬼魂们又各自说起了自己的故事,就形成了“故事套故事”的情节环包结构。作者为了透彻地追寻且解析两支驼队消失的“野狐岭之谜”,又要详细解析齐飞卿、陆富基、马在波、巴特尔、大烟客、沙眉虎、黄煞神、大嘴哥和木鱼妹等这些人物前往野狐岭的复杂动因与隐秘目的,而每个人的故事又因为地域空间的变换而生化出许多另外的故事。如木鱼妹的故事里就有“岭南故事”“镇番故事”“凉州故事”“苏武庙故事”“野狐岭故事”等。其中的每一个故事又套着许多神奇的小故事,如“岭南故事”中又有“木鱼爸”“童养媳”“堵仙口”“岭南大火”“土客械斗”等。“苏武庙故事”中又有“时轮历法”“抄木鱼书”“双修相恋”“捉奸受审”“行刑被救”等。同样,齐飞卿的故事就包含“在凉州”“在镇番”“在野狐岭”“在邓马营湖”“在胡家磨房”等诸多故事。而每一个故事又包含着许多更小的故事,如“在凉州”的故事中就包括“关爷庙聚义”“鸡毛传帖”“凉州暴动”“羊庙藏银”“殒命大什子”等。“在野狐岭”的故事中又有“驼王争霸”“蒙汉械斗”“抢夺黄货”“熊卧沟会匪”“沙岭狼祸”“末日逃亡”等。《野狐岭》好比一个巨大的环圈,这个环圈又环套了许多以人物为标志的大环圈,每个人物大环圈中又环套着以地域空间为标志的单个独立的环圈,所有单个独立的环圈中又环套着无数个神奇的小故事构成的小环圈。又因为每个人物都在自己的故事里叙述着别人的情节,反过来又在别人的故事里补塑出自己的完整性格,于是这些更小的环圈之间就形成了彼此独立又相互牵扯的联络结构。这样就形成了《野狐岭》中“故事套故事”的情节环包结构。作品中的那些看似松散的片断其实是围绕着“我”而摆开的一面面旋转的镜子,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社会现实。故事情节不是精致严密的因果逻辑情节,而是松散的、开放的流动的鲜活的生存现实。现实的事件和幻想的故事、理性的思考和非理性的感悟、清楚的事实和模糊的印象、真善美的事物和假恶丑的现象都会在叙述过程中浮现出来,使人就像看到了原汁原味的生活本身一样。
《野狐岭》的情节环包结构中,作者着意加强了每个“环圈”的独立性和界限化,使每个看似关联的故事可以离开前后所写环境而独立存在,容易使人感到章与章之间似无显然的联络贯穿。全书是独幅式的画簿,翻开一页又是一页。“野狐岭之谜”又将前后贯通的故事作为“粘合剂”,再加“超叙事者”精心设置的“假设顺序”,把各个画页粘合成流动的电影“蒙太奇”镜头,然后才不致零乱倒错,循着这样的情节环包结构,读者才能在“挑战阅读智力”的精神游历中打开《野狐岭》中不属于日常经验里的那个繁复的瑰奇的神秘空间。
《野狐岭》让读者摆脱了被动阅读的命运,在喜怒哀乐之外,读者得到了久已渴望的那些智慧含量。从《野狐岭》里可以读出作家浸透于其中的焦虑心理、悲悯情绪、对现实的批判能力、对人性的思考以及对民俗文化的密切关注情怀。阅读《野狐岭》既有走进迷宫,游历梦境的迷茫之感,又迫使读者升华自己的阅读能力与灵魂高度,穿透小说背后的精神内涵,去明晰地思考“人”的来龙去脉、左右人间的“命运巨手”又在何方等这样一样玄奥的命题。雪漠采用了适合超越叙事方式的复合结构,使《野狐岭》带着“西部写实”和“灵魂叙写”的双重烙印,裹挟着一股经过文学涅槃和灵魂修炼之后的一种超越叙事的气象,大器傲岸地矗立于中国当代文学之林。
七
《野狐岭》的超越叙事和复合结构,并非只是机械的文学表达技艺,而是忠实地融合了普通众生的情感、理想体验而采用的一种综合性的高难度的艺术创造。笔者一直认为,只有尊重生命个体自由和发展的艺术构想才是理性和完美的,才能赢得广大读者的自觉认同;也只有真实鲜活的人性书写才能激活宏伟的历史和现实画面,才能展示时空大背景下饱满的文学审美张力。作家的审美取向和审美理想基于对普通众生的终极关怀和心灵超越为出发点,便容易抵达接近崇高的美学特征。从《大漠祭》到《野狐岭》,雪漠始终跋涉在对个体生命遭遇的深度挖掘和对众生心灵超越途径的寻觅道路上,视野越来越大,胸襟越来越广,其洞悉社会生活的目光也越加具有穿透力。超越叙事和复合结构使作品具有一种运动感和力量感,这种运动感推动和托举读者随着作者的灵魂流淌而升腾一种崇高超越之美,这种力量感又能揭去生命的伪饰,让人自觉检视自己的灵魂,为自己曾经的卑琐、粗俗、懦弱与苟活而羞愧不已。《野狐岭》洋溢一种人性的力量、文化的力量和依附文化而传承下来的信仰的力量,最终聚合融汇成命运的力量,击穿了地域、种族和恩仇的隔膜与界限,表现了超越苦难的爱与宽容的主题思想。雪漠说《野狐岭》“拒绝了那些显露的主题”,但紧接着又申明“当然也不是没有”[15]417。在笔者看来,“超越苦难的爱与宽容”就是《野狐岭》的“隐约”主题。在《野狐岭》中,木鱼妹因和大嘴哥偷情而误杀了马二爷的小儿子,马二爷又放火烧死了木鱼妹的父母。木鱼妹寻仇途中又爱上了马二爷的大儿子马在波,并怀上了仇人的孙子。木鱼妹寻找一切机会追杀马二爷,其子马在波却又费尽心血地整理完成了木鱼爸视为生命一样珍贵的“木鱼书”。对于木鱼爸而言,因为马二爷的原因,他对妻子心怀怨恨。但大火烧来,却置自己视为生命的木鱼书而不顾,最后拥抱着美丽的妻子双双于火海里化为灰烬。更令他难以相信的是以后自己的女儿竟然成了仇人儿子的情人,而自己的“木鱼书”最终又在仇人的儿子手中完成了宿命般的纪录和传承。在《野狐岭》结尾作者展示了一场铺天盖地而来的沙尘暴,使所有的生者与死者都汇聚到了胡家磨房,将生者、死者和虽生犹死者的形象一齐陈列在读者面前,供人们去审视和鉴别,带有极为浓厚的悲剧色彩和深刻的命运启示意味。可见,爱恨情仇不过就是个体生命在岁月长河里的瞬时体验,在人性关怀的背景下,文化、信仰和命运的合力最终会将这些生命的屑小感觉消融于无形,超越苦难的爱与宽容的主题之光便会始终闪映在芸芸众生的灵魂空间。
《野狐岭》一如既往的表现生存的苦难,记述苦难生活里顽强传承的生存意志和灵魂信仰,因而消弭了仇恨与罪恶,升华了超越苦难的爱与宽容的博大主题。《野狐岭》直面错采离奇的苦难生活本身,小说中潜隐着作家对个人命运如同浮萍般飘摇晃荡的深度焦虑和艰难如锥的现实对生命尊严逼仄的隐忧情怀,增加了小说的人文关怀和灵魂求索的思维厚度。小说中的木鱼爸饱尝饥饿与侮辱,仍能顽固地整理抄写木鱼书,但别人发现他的衣袍里“没穿裤子”时就要上吊自杀。陆富基意志刚硬,但受到“倒点天灯”的酷刑之后,觉得这是“最开不了口的事”,便不想活了。齐飞卿被刽子手用“胶麻缠刀”的方式锯死于凉州大什子时,发出“凉州百姓,合该受穷”的喟叹。马在波在亲生孩子被抢走受到胁迫和威逼之后心里涌起的无奈与沮丧等。所有这些细节既有平民受辱时的憋屈感受,又有英雄落难时的悲凉况味,传递着普通众生平凡而习见的苦难体验,让人有感同身受的切肤之感。如果说,《大漠三步曲》写了西部人民的苦难,而《野狐岭》则以超越叙事手段完成了南北贯通的巨笔构划,由西部人民的苦难拓展到对更为广泛的中国人民的历史岁月的记载书写。《野狐岭》将那一个特殊里代里中华民族底层人民共同的苦难生活体验呈现到读者面前,试图“写出一个真实的中国,定格一个即将消失的时代”,因而具有史诗般的时代性与真实性。乔伊斯曾说:“写头脑里的东西是不行的,必须写血液里的东西。一切大作家,都首先是民族的作家。正因为他们有强烈的民族精神,最后才能成为国际的作家”[16]143。从这个意义上讲,雪漠创造的野狐岭和其笔下的木鱼歌、驼户歌、凉州贤孝、镇番民俗、驼把式等民间元素已经融为一体,带有中国气派和中国特色的民族精神,如同鲁迅笔下的“鲁镇”、萧红笔下的“呼兰河”、 艾略特笔下的“荒原”和福克纳笔下的“邮票”般的家乡一样,将会成为带有特殊的地域文化意蕴的文学标本,在中国当代文学领域折射出璀璨而永久的光华。
参考文献:
[1]陈琳;吴越.雪漠新作《野狐岭》“重归西部”〔N〕.文汇报. 2014-10-08(4)
[2]雪漠.野狐岭[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423—428
[3]雪漠.野狐岭[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423—428
[4]雪漠.野狐岭[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423—428
[5]雪漠.野狐岭[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414—422
[6]傅小平.幽魂叙事打开被掩埋的记忆〔N〕.时代报. 2014-09-09(3)
[7]雪漠.野狐岭[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344
[8]吴波.清末民初甘肃哥老会述略〔J〕.宁夏社会科学,2006,(2):113—116
[9]雪漠.野狐岭[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416
[10]]陈琳;吴越.雪漠新作《野狐岭》“重归西部”〔N〕.文汇报. 2014-10-08(4)
[11]雪漠.野狐岭[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414—422
[12]雪漠.野狐岭[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414—422
[13]雪漠.野狐岭[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50
[14]雪漠.野狐岭[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92
[15]雪漠.野狐岭[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414—422
[16]杨建.乔伊斯论“艺术家”〔J〕.外国文学研究,2007,(12):141—149
——刊于《唐都学刊》2015年11月第31卷第6期
雪漠文化网,智慧更清凉!www.xuemo.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