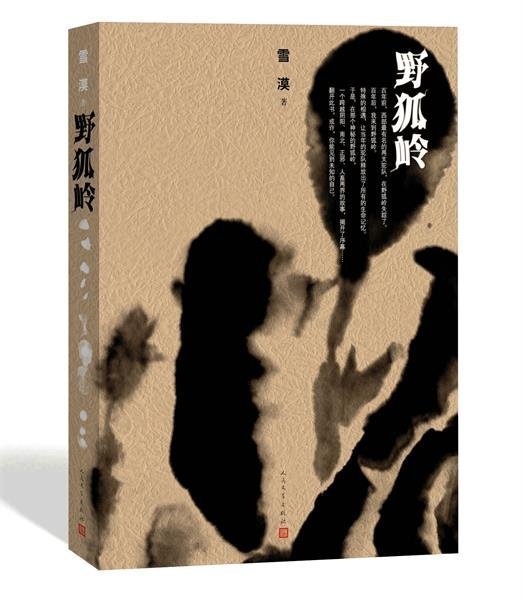
《野狐岭》的超越叙事与复合结构(1)
文\程对山
摘要:超越叙事是雪漠在写作生涯中长期坚守的一种创作信仰,是在灵魂和神性的高度照观下的一种超越了世俗世界的悲悯与反思,是一种通透与宏大的视角来表现生活与世界真相的创作观点。“超越叙事”力图在不完整的叙事结构中传递一种完整的气息和气场,传达一种超越空间、逾越时间的艺术概念,从而实现对传统现实主义叙事方式的一种文本超脱。《野狐岭》采用了与超越叙事方式相匹配的独特的复合结构。这种复合结构在文本表现中,又呈现出心理杂糅和情节环包的两种结构类型。本文在雪漠文学创作本体论的宏观层面下加以讨论小说《野狐岭》中“超越叙事”与“复合结构”的表现特征,努力发掘雪漠小说创作在当下文学建设中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
一
《野狐岭》是雪漠创作的第七部长篇小说,是《大漠祭》出版十四年后再次以西部大漠为叙事背景的“回归大漠”的首个作品。阅读《野狐岭》就会发现,雪漠的“回归大漠”绝非简单的“西部写实”意义的回归,而是一种超越了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全新而成功的回归。雪漠把扣人心弦的故事传说、新颖别致的文本形式、狂放不羁的想象联想融合在一起,在《野狐岭》中开辟了一片惊心动魄的艺术天地。其运用精心设撰的故事情节、叙述方式、心理结构等元素,将一个极富象征意味的关于寻找和超越的灵魂探险故事呈现给读者,具有厚重博约的品质和新颖大器的特点,标志着雪漠小说创作艺术方面的一次成功的超越与突破。著名评论家雷达认为,雪漠的此次回归,“不是一般的重归大漠,重归西部,而是从形式到灵魂都有内在超越的回归” [1]。笔者认为,“从形式到灵魂都有内在超越”的标志就是雪漠在“回归”中自觉地融入新的思想观念和新的创作方法,最明显的特征就是《野狐岭》的超越叙事与复合结构。
陈彦瑾在《从<野狐岭>看雪漠(责编手记)》中认为,《野狐岭》是打上“雪漠烙印”的一部小说,并进一步诠释,所谓“雪漠烙印”,就是体现雪漠文学价值观的“西部写生”“灵魂叙写”和“超越叙事”。但是,陈彦瑾在文章中仅将“作为众生的一种声音”的“超越叙事”特点作了阐述。认为《野狐岭》巧妙地运用了幽魂叙事,“由于脱离了肉体的限制,幽魂们都具有五通,其视角就天然具有了超越性”。并且进一步强调“《野狐岭》的超越叙事不是来自叙事者之外的超叙事者,而就是作为叙事者的幽魂们自己。当然,前提是这些叙事者是幽魂,他们本具超越功能”[2]427。对此,笔者不敢苟同。首先,《野狐岭》中“超越叙事”的主体并非“作为叙事者的幽魂们自己”,恰恰相反,《野狐岭》之所以具有“超越叙事”的美感特征就是因为小说中确实存在一个“超叙事者”。这个“超叙事者”不是马在波,也不是“我”,而是作家本人在进行写作时化身而成的“叙事者”。事实上,无论采用什么样的现代技巧创作的小说,作家本人化身而成的“叙事者”都是存在的。将作家本人“超叙事者”的文学功能弱化甚至湮灭,是虚诞而不足取的。其次,陈彦瑾将体现雪漠烙印的“超越叙事”的特征以“对号入座”的方式仅框定在“幽魂”叙述的话语层面进行论述,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作品整体的“超越叙事”的文本特点。说穿了,《野狐岭》中的一个个“幽魂”就是作家创造的一个个“人物”,作家将笔下的人物以“幽魂”的方式呈现,反使作品因“荒诞的真实”而产生一种令人心旌摇曳的魔幻引力。“幽魂”的叙说方式就是人物的语言特点,作品中的齐飞卿、陆富基、木鱼妹、大嘴哥、巴特尔以及被拟人化了的骆驼“黄煞神”等人物,因为具有不同的性格特点,人物话语方式也各呈异彩。陈彦瑾在文中也说,“《野狐岭》里,木鱼妹、黄煞神、大烟客等幽魂都有属于自己的超越叙事”[3]427。只是将体现人物不同性格特点的话语方式说成属于人物各自的“超越叙事”,就显得有点儿大词小用或大而不当的嫌疵。无论如何,文学作品中人物的话语方式只是作家在创作时考虑到的一个细节因素,不能将 “超越叙事”硬性地摁到人物话语方式的创作细节方面论述。笔者认为,作为体现“雪漠烙印”的主要特征之一的“超越叙事”,必须要将之当作《野狐岭》的整体文体特征来研究阐发,必须放置于雪漠文学创作本体论的宏观层面加以讨论,既要考察其历史渊源和文化传统,又要努力发掘超越叙事在当下文学建设中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
二
由此来看,超越叙事应该是雪漠在写作生涯中长期坚守的一种创作信仰,是在灵魂和神性的高度照观下的一种超越了世俗世界的悲悯与反思,是一种通透与宏大的视角来表现生活与世界真相的创作观点。对此,陈彦瑾在上面提到的文章中也有一定的论述,从其复杂的论述中笔者拎出了关于超越叙事的轮廓般的概念。超越叙事是一种基于“超验之维”而萌生的一种“超越视角”,并由之升腾诞生的“灵魂辩论”[4]426。其指出雪漠的超越叙事是有着为中国文学“补课”的价值和意义,这样的论述倒是中肯而准确的。如果说传统叙事的目的在于完整地讲述一段或几段故事,那么雪漠创作中的“超越叙事”则是在不完整的叙事结构中传递一种完整的气息和气场,传达一种超越空间、逾越时间的艺术概念,从而实现对传统现实主义叙事方式的一种文本超脱。
《野狐岭》确实存在一种不完整的叙事结构,全书除“引子”外, 通过鬼魂在“二十七会”里的叙述,试图揭开百年前西部最有名的两支驼队在野狐岭神秘失踪的谜团。但是,鬼魂的叙事方式自然带有“鬼魂”的气息,那就是前言不搭后语、破空而来、游移无定和断续无迹等特点。只能通过他们释放出的残缺不全的生命记忆,经过互补和引证才能完整地还原出那些贯通阴阳、正邪、人畜两界的野狐岭故事。可以说,当年驼队如何走进野狐岭、迷失野狐岭、困厄野狐岭、走出野狐岭并在胡家磨房实现了灵魂的涅槃与升华等情节均有一种不相联属的残缺性和片断性。可是,内蕴其间的神秘感和荒诞性又构成了小说叙事结构中完整的气息和气场。雪漠在《杂说<野狐岭>(代后记)》中也说,“(《野狐岭》)里面有无数的空白,甚至是漏洞——复旦大学的陈思和教授称之为‘缝隙’——它们是我有意留下的。那是一片巨大的空白,里面有无数的可能性,也有无数的玄机”[5]416。由此可见,这种“不完整的叙事结构”得当地体现了作者超越叙事的艺术追求。雪漠特意设置“空白”“漏洞”或者称为“缝隙”,就构成了叙事方式的板块化和跳跃性,更能激发读者的想象力和阅读的好奇感,从而使《野狐岭》传达出一种超越空间、逾越时间的艺术观念。因为超越叙事方式,使《野狐岭》打上了悬疑小说的印迹,读者在并不轻松的阅读过程中,始终感觉到这些鬼魂们的叙述却也悬念叠起、步步紧扣人心,因而极富饱满的艺术张力。
《野狐岭》中超越叙事的板块化和跳跃性,颇似电影艺术中的“蒙太奇”手法。在《野狐岭》共二十七会的内容中,第一会《幽魂自述》以集中亮相的方式,让九位有“代表性”的鬼魂各自叙述初次露面时的感觉和必要的交代,最后一会即第二十七会《活在传说里》则以鬼魂集体聚会“座谈”的形式结束了艰难而奇特的采访任务。而其他的“会”则是以一人和两人以上的多人方式进行。其中一人叙述的有十三会,木鱼妹一人就叙述了九会,分别是第三会《阿爸的木鱼歌》、第七会《械斗》、第八会《小城的拾荒婆》、第十会《刺客》、第十二会《打巡警》、第十三会《纷乱的鞭杆》、第十五会《木鱼妹说偷情》、第二十二会《木鱼妹说》和第二十六会《木鱼令》。马在波一人叙述了两会,分别是第十八会《胡家磨坊》和第二十五会《起场时节》。巴特尔和齐飞卿各叙述了一会,分别是第九会《巴特尔说》和第二十三会《狼祸》。阅读比较各“会”的内容就会发现,凡是一人叙述的“会”中,叙述人都讲述一个固定的空间范围里发生的故事始末。如第三会《阿爸的木鱼歌》中,木鱼妹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得从开头说起”,讲述了发生在岭南木鱼爸家里的故事。而第十二会《打巡警》和第十三会《纷乱的鞭杆》中,则以凉州为固定空间,讲述了“飞卿起义”的兴起过程直至最后被巡警镇压而四散逃亡的悲惨结局。第九会《巴特尔说》中,巴特尔讲述了在固定的野狐岭驼户驻地,为了防备“褐狮子”被害而开始跟踪陆富基,由之而发现了“哥老会”的许多秘密。这种呈现方式可以视为空间固定而时间流动的“时间蒙太奇”。凡是多人叙述的“会”中,叙述人都在讲述同一时间里场景不断变换的故事。如小说第四会《驼斗》中,在发生“驼斗”那个凝固的时间里,陆富基以“窝铺”为场景讲述了由于驼掌弄烂而蒙汉两家驼队不得不滞留在野狐岭,所以发生“黄煞神”和“褐狮子”两只公驼争斗的合理原因。马在波则以“帐篷”为场景,交代了野狐岭是远离寻常驼道的一个荒凉怪异的地方。齐飞卿的叙述中变换了两次场景,先是从“马家驼场”为场景叙述公驼争夺驼王的自然属性,又变换到“草场”叙述汉驼王“黄煞神”和蒙驼王“褐狮子”之间因争风吃醋而发生的战斗。“黄煞神”的叙述也从近处的“草场”变换到更远处的“草场”叙述了它咬伤和踢伤“褐狮子”的两次经历。在同一个凝滞的时间里因不同人物的叙述,就形成了不同空间变换的背景下人物的所见所闻乃至心理活动形成的独特“意识流”画面。作者巧妙地将这些画面拼合在一起,将引发野狐岭汉蒙两个驼队纠葛的“驼斗”事件描述得扣人心弦,历历如目。又如小说第十六会《追杀》和第二十会《肉体的拷问》等,作家都选择四个以上的人物来叙述在同一个凝滞的时间里,在不同空间快速变换的背景下发生的故事。这样的叙事方式可视为时间凝滞而空间迅速变换的“空间蒙太奇”。这种故事情节的蒙太奇效果,给读者留下深刻的艺术印象。作者使用“蒙太奇”画面效果,不仅是为了叙述故事,更多的还在于表达故事背景后面的某种情绪和感觉,比如忧虑、仇恨和愤怒等,这一切都较好地渲染了野狐岭中贯穿全书的完整的气息与气场氛围。叙述画面的“蒙太奇”效果,成为《野狐岭》中超越叙事方式最突出的艺术标志。
三
《野狐岭》的超越叙事并非简单的一般的复杂叙事,雪漠没有满足于仅仅追求叙事结构的繁杂,也不是单纯的追求叙事层次的繁复和叙事场景的宏大,而是追求一种超越叙事的深邃和广博,使读者在初始阅读体验中萌生一种迷蒙困惑的氛围,似乎又在一团迷蒙困惑中看懂了更多的东西。超越叙事中的“空白”“缝隙”就像很多省略号要表达的东西一样,有一种意会大于言传的神奇功效。对此,评论家陈晓明曾经指出,“《野狐岭》不是把日常经验简单描述,而是把西部大地的神话气息、文化底蕴重新激活,重新建构,传导了一种西部大地人和自然相处,人和动物相处、人和神相处,人和灵魂相处的神奇景观。”[6]。《野狐岭》采用超越叙事的方式,将历史与现实,人间与鬼界,史实与传说,歌谣与故事相结合,使小说具有了一种充满想象的丰蕴度和艺术力,别是岭南木鱼歌和凉州贤孝这种不同民俗方式的融合,将二者共有的忠君报国的孝义精神相互渗透,真实地再现了清末民初的那个动乱时代里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生命传承精神。
在超越叙事的大视角下,雪漠笔下的历史和现实都笼罩着一层理性和普适的人性意义。《野狐岭》讲述了“飞卿起义”“土客械斗”“蒙汉争斗”“回汉仇杀”等历史事件。“飞卿起义”无疑是贯穿全书的主要事件。雪漠笔下的齐飞卿、陆富基连同苏武庙中的胡旯旮在历史上均有其人,在《武威市志》的记载中,“飞卿起义”是辛亥革命背景下发生的一场农民暴动事件。但是,雪漠阐述历史的视角与方式与众不同,敢于直逼那些神秘幽深的生命真相,借助历史事件的描述传达自己对历史和现实的感悟与反思。马克思说过,“一切历史事实与人物都出现两次,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喜剧”。作者深谙马克思关于历史的解读意味,超脱了历史,将那个时代的特征消弭在普遍的社会发展的规律中,表现了更为深广的现代历史意识。《野狐岭》的重点不在表现历史过程本身,而是挖掘沉淀在历史过程中的地域性的封闭愚昧、自私落后的文化劣根性,揭示出历史事件中以“革命”的名义掩盖了的荒谬性和喜剧性的存在事实。如在《野狐岭》第十二会《打巡警》和第十三会《纷乱的鞭杆》中,作者描述了齐飞卿领导哥老会党徒发动农民暴动时给人民生活带来的负面灾难,比如烧房子、抢东西、砸店铺、毁岗楼等等。在第二十五会《起场时节》中揭示了哥老会成员“为达目的”而进行的胁迫和杀戮。在第二十六会《木鱼令》中,齐飞卿因“革命”而被杀时深刻而绝望地感到了凉州吏民的自私、怯懦、冷漠和麻木,发出了“凉州百姓,合该受穷”的喟叹。在第二十二会《木鱼妹说》中形象描述了哥老会党众的结拜仪式——
那些汉子摸着一只大公鸡,齐声在唱。声音很是整齐,想来他们已演练很久:“摸摸凤凰头,咱们兄弟都得封公侯;/摸摸凤凰腰,咱们兄弟骑马挂金刀;/摸摸凤凰尾,咱们兄弟都是得高位;/摸摸凤凰脚,咱们兄弟加官又进爵……”然后他们杀鸡,饮血酒,盟誓,从此以兄弟相称。[7]344
在这里,作者通过沉着从容的白描手法表现了“入会”的重要仪式过程。但阅读时感觉不到丝毫的庄重、庄严和神圣的气氛,反觉这样的“已演练很久”的结拜场景非常滑稽可笑,几至于忍俊不禁。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超越叙事并没有在无原则的“超越”中掩没了历史真相,相反,雪漠对历史事件的记述却是忠实于历史真相的一种真实的记述。历史记载中的哥老会就是一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相当粗糙且混乱的组织。虽然哥老会广泛参与辛亥革命,为迅速瓦解清王朝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其本身存在的弱点是致命的。哥老会固有的帮会陋习时时暴露出来,缺乏严密组织纪律,缺乏明确长远的政治目标。哥老会成员走漏消息、欺良霸善之事屡见不鲜。为之孙中山曾发出喟叹,“(哥老会)皆知识薄弱,团体散漫,凭借全无,只能望之为响应,不能用为原动力”[8]115。难能可贵的是,《野狐岭》以超越叙事的方式,形象地揭示了哥老会组织的荒诞性,从而揭示了齐飞卿、陆富基等人悲剧命运的时代性和必然性。对此,雪漠说,“故事的背景,我也放在了一个有无穷可能性的时代,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有戏剧性的时期,各种背景、各种面孔、各种个性的人物,都可以在这个舞台上表演,演出一幕幕让我们大眼张风的丑恶、滑稽或是精彩的故事”[9]416。而雪漠的高明之处就是找到了叙述历史事件的一种恰当的超越方式,将常见的历史小说中的“革命叙事”方式转化为“民间叙事”方式,在《野狐岭》中质疑历史事件的动机,深刻反思飞卿起义的悲剧性后果,并因之而肯定和推崇一种普适的社会规则,比如生活安定的必要性、传统文化的恒定性、人之常情的可靠性和平凡众生的合理性等。
(续)
——刊于《唐都学刊》2015年11月第31卷第6期
雪漠文化网,智慧更清凉!www.xuemo.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