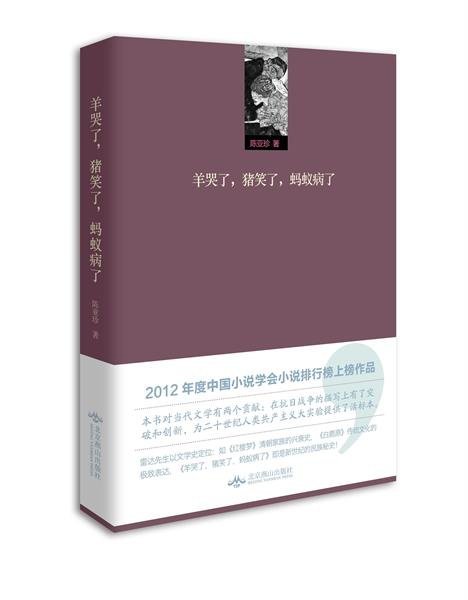
《羊哭了,猪笑了,蚂蚁病了》 陈亚珍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雪漠:灵魂的拷问和身份的追索
――解读《羊哭了,猪笑了,蚂蚁病了》
我在甘南草原体验生活,已经有两个多月了。我想感受另一种生活,再写出几部能安慰自己灵魂的好作品。
我这次西部之行,源于雷达老师对一部小说的推荐——它就是今天研讨的《羊哭了,猪笑了,蚂蚁病了》。我看到这部小说之后,我突然觉得,很多中国作家,都应当惭愧——包括一些获了大奖的人。他们根本不能和这个默默无闻的作家相比拟。我看完小说之后,便发短信感谢雷老师,感谢他推荐这样的作品。我对雷老师说,以后我也想写几部这样的作品。于是,我就重新回到了西部,在甘南草原体验生活。
看到《羊哭了,猪笑了,蚂蚁病了》以后,我被深深地震撼了。她的作品是灵魂的倾泻,生命的迸发,决不是技巧的功效。陈亚珍真的很了不起。我的儿子陈亦新看完之后说:“这样的作品如果被埋没,中国文学是没有希望的。”
当然,目前这部小说被中国小说排行榜评为上榜图书。感谢雷老师推荐了这本书,让我们很多作家,发现了自己和这本书的距离。我们的作家应该更好的去深入生活,让自己的灵魂更加博大,更加强健有力。
我跟陈亚珍的创作追求有相近之处。相较于文学作品,都喜欢看宗教、哲学类著作。过去我在武威,有一间闭关的小房子,保留了将近二十年。在这间房子里,我放了两张照片。一张是我的上师——活佛的照片;另外一张是雷达老师的照片。我一直很感激雷达老师发现了我的《大漠祭》,经过他的力推,才让更多的人发现了我。在这一点上,陈亚珍也一样。所以,雷达老师对文学的热情和赤诚我是深有感触的,他对任何一个他认为写出好作品的作者无论世俗地位高低,都是一视同仁的!这样的文学心灵是值得我崇尚的。我把他的照片放在书桌上,提醒自己一定要写出好作品来报答他的心灵。所以,宗教和文学两种力量,形成我生命的元素。雷老师代表文学,上师代表佛教,造就了我生命追求的两峰。当雷老师占上风时,《猎原》、《白虎关》、《西夏咒》便从我心灵中流泻出来。当上师占了上风,我就专注于“光明大手印”、《无死的金刚心》这些佛理佛心的书写。它们有时在我生命中纠结,有时互为统一。正如儿子所说,雪漠本是一个作家,却想当佛陀。其实宗教和文学不尽相同,但都需要精神超越,其终极意义是:善!于是我的小说有了另外一种张力。
阅读陈亚珍的作品亦然,我总能感到文学之外有一种张大的力量。《羊哭了,猪笑了,蚂蚁病了》以充沛的内功、强大的心灵力量、超凡的思辩、原始森林般的生活容量,写了一个被良知拷问的灵魂和一群被灵魂拷问的生命。
书的开篇,首先出现的是一个寻觅和追问的灵魂。依照作者所言:“活着的时候我想死,死去的时候我想活,于是我又勇敢的复活了”。“我”成了一个追问和寻觅的灵魂,重回人间,重回故土,重见家人,为了寻根问祖,为了爱的渴望。这既是灵魂本身的追问,同时又是灵魂---良知对活人的拷问。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说法,肉体本是灵魂的载体,肉体随时可以消失,但灵魂却不灭。我更愿意将灵魂当成是一种良知,因为凡有渴求良知者,总是会感受到灵魂的被迫受欺。而丧失良知者不在乎灵魂是否安然。也许,惠儿的灵魂复活或者说不死,正是她的良知使然,也正是因为有更多的人在招唤她,比如他的父亲,惠儿灵魂的出现是父亲的一个难题,他必须正视他不愿正视的种种。起初正如书中所见,父亲更多的是个背景,也是惠儿生命中的一个影子;再如她的二妹,正在崇高与低俗的十字路口,时而嘲弄,时而仇恨,时而悲天,时而捶胸,他们都需要“灵魂”。所以惠儿无疑是灵魂的救赎者,设若没有灵魂的拷问,惠儿爹们则无法安息,惠儿姐妹们则无法选择,书中的众多角色也不可能有升华的可能。因此,我们首先看到了一个四处奔走的灵魂,她首先以寻祖的形式,追问良知。
“祖”是什么?祖就是一个人的身份。书中还有一句话:一个人如果没有身份就像一个民族没有祖国一样。这句话给人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其意义让我意识到亡灵是寻找做为一个“人”的身份,什么是人的身份?作者说:人的全部尊严在于思想,人的全部身份在于爱与信念!如果人类失去了爱,就丧失了最后一点文化。是的,爱、良知、信念是人类的普世价值,可人类的良知已被腐蚀、被淹没、被侵袭,但良知使灵魂死而复生,去寻觅,去追问,去化解,甚至去引领,去洗礼,去救赎。由此,我断想灵魂不止是寻根问祖单一的含义,而是寻找真正的“人”的身份。
其次是对“规矩”的追问。
“规矩”如同层层蛛丝制约着世人。惠儿生活的梨花庄像所有的村庄一样,似乎都有一个魔幻式的、神化式的、唯美式的开始,点石成金般给了那块土地一个灵魂。一代又一代的人类在那块土地上繁衍生息,日夜耕作,守着古老的规矩,不超一步,不越一池。于是,这千古传下的“规矩”也开始被灵魂追问。有人说规矩是杀人不见血的刀,是绑架灵魂的魔鬼,也有人说规矩本是善和美的使者,失去规矩就是恶。
规矩是什么?
其实文化祖先制定“规矩”正是校正人的行为,然而它一但程式化、教条化,人性就在其中桎梏。书中的“规矩”让九妮刺瞎了自己的眼睛,独眼九妮又用“规矩”杀死了所有需要爱和应该被爱的女人们,最后又被破“规”纵“欲”的养女击毙在“贞洁”牌坊下;“规矩”让惠儿的母亲以“不贞”为名屈辱地活在梨花庄,被深爱的丈夫抛弃;规矩”又让许多烈士遗孀跳井、上吊死于非命,也让惠儿嫁了张世聪。后来,被玉米们以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理念,把这“规矩”彻底粉碎了……自此,梨花庄无一瓣梨花,凡有灵之物一概不复存在。
旧的“规矩”破了,新的“规矩”再次成立,它的呈现似乎潜在中更加惨烈。玉米们肆无忌惮,一会儿舞起革命的大旗,一会儿歌唱造反的小调,他们永远是时代的宠儿,是权钱的追随者,他们深通任何一个时代的“规矩”其妙处。因此人世间的最大工程是:消解规矩、再造规矩、利用规矩。这其中也包括张世聪们,一群可怜的小人物,当他们制造不了规矩时,便成了规矩的爪牙。凡是这样的“规矩”都是虚假的,是经不起时间推敲的,也经不起历史追问的。任何一个良知者,都会明白,这“规矩”实际上是人类生存过程中,残忍厮杀时的一种遮羞布。
在这部小说中,惠儿奶奶,是个目不识丁的思想者,她知道再大的“规矩”也大不过活命、大不过一个孩子的亲娘。如果规矩变成凶器反过来刺向人心时,这规矩就是元凶。惠儿奶奶沒有成为规矩的奴隶,她以内心的痛切、坚毅,有效地摒弃了“规矩”维护了一条命。这是这个人物的伟大之处。但更多的人在“规矩”面前,钝化了良知,随着人潮,拥上了那班不知去向何处的公共车。他们在车上拥挤着,厮杀着、吵闹着,望不到一点属于自己的风景。他们自动放弃做人的尊严。像书中所说,只有“狗”做到位了,才能支起来做所谓的“人”。
巨大的历史漩涡海啸般席卷了人的灵魂,剩下的,只是一堆堆干巴巴的肉体。他们木偶般的笑着、动着,念叨着那句老话:好死不如赖活着。
为何会有这历史的漩涡?这漩涡的主宰者是谁?谁能超越这漩涡,超越这集体无意识的宿命?
有人说这漩涡是国家、是民族,是地域,是人种或血脉。每当一个漩涡卷起千层浪时,民族、国家、种族无不在巨大的痛苦之中,梨花庄的人不就是这样吗?因为汞矿,土有毒,水有毒,食物有毒,人也有毒。废弃——难道是一个村庄的终极悲怆?。这正是艺术家们、文学家们时刻警觉的,用历史来提示现代,用经历来告知人类,用语言来展示因果,用疼痛来提醒时代和时代的“规矩”。如此,庸常者才有可能发现那个即将到来的灾难,至少听到了警钟的鸣响。
所以,才有了大量的思辨。这种“思辨”则是一个真实的灵魂不由自己的倾诉,那些话畅快淋漓,酣畅痛快,仿佛久病之人一场大汗后不治而愈。为此在那些“思辨”汇入了形象体系,让人感受到它不是在说教,而是良知的共振、摩擦和燃烧。在熊熊的烈火中,真金接受着最炽热的冶炼,灵魂需要洗礼,需要被人间称之为苦难的洗礼。
你到底有没有灵魂?非是无知时的自大之言,而是经历拷问后的生命轨迹。
灵魂的拷问是一种态度,我相信作者就是在这种态度下写作的,她用文学拷问着自己,历练着自己,升华着自己。但是在升华之处还有一个空间。字里行间中苦难的味道浓烈不散,虽然也能看到作者对爱的追求,却没能用爱化解所有的仇恨,让爱成为一种智慧。
书后评者说,平庸的作家书写的是个人的心灵,优秀的作家书写的是民族心灵,伟大的作家书写的是人类的心灵。这句话是有道理的。陈亚珍无疑是优秀的作家,她书写了一个民族的心灵,但又不仅仅如此。战争、饥饿、瘟疫、政治高压、文化禁锢、人心的黑暗,哪一个民族不承受这样的灾难和痛苦?所以这部书又是人类灵魂的书写。亡灵的找寻是茫然的,这也许就是人类的宿命。但作者最后的仁慈是:让亡灵与亲人团聚。最高的理想是:“让仇恨扯远,让爱延伸”,他们“终于唱起了一支属于自己的歌”,这歌声还要让所有的人都听见。所以,这部作品里的爱,是灵魂的绝唱,她宁静、安息……
也许我的解读称不上解读,因为我不想把自己和人物当成毫无关系的二元,小说中的那些人物何尝不是自己,而自己又何尝不是人物。文学成全着作者,同时也成全着读者。
——2013年8月18日“陈亚珍作品研讨会”发言
雪漠文化网12月荐书《羊哭了,猪笑了,蚂蚁病了》:
http://www.xuemo.cn/show.asp?id=150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