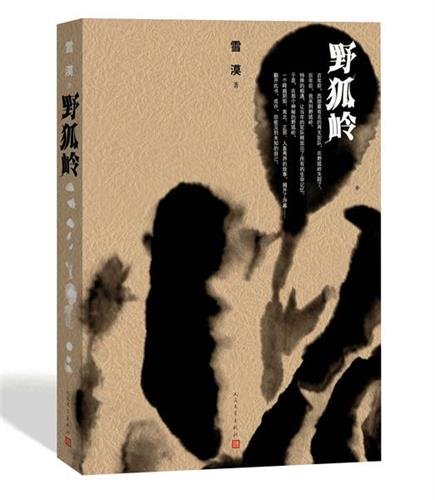
《野狐岭》 雪漠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7月出版
【出版人】《野狐岭》:雪漠的野心与文化方位感
文\宋炳辉(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教授、《中国比较文学》副主编)
雪漠把丝绸之路的文化历史,跟整个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勾连起来,然后借助他的故事和精神结构,让他的灵魂叙事能够突破中华文化的范畴。在这一点上,雪漠是有野心的。
一个有野心的作家在几个方面必定是很有底气的。一是他很会讲故事,他的故事能抓住读者,这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对于雪漠的《野狐岭》,如果我们倒过来解读,就会发现磨坊的故事是核心情节,如果将来马在波变成隐士的话,那肯定会成为一个核心的高峰。同时,一个有野心的作家也必定有一个强大的精神结构,在这方面,雪漠也有他的特点和优势。他对佛教,尤其是藏传佛教,有过长期的潜心研究,所以有一种独到的见解和积累,在他前面的作品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另外,一个有野心的作家,还必定有一种文化方位感。一直以为,雪漠的整个创作有一种文化上的方位感,不同的作品在他构筑的文学世界中,有着具体的文化方位。我的理解是:雪漠的根在丝绸之路一带。虽然我们对那里的地域色彩印象都非常深刻,而且在当代作家中,有地域写作意识的作家其实很多,他们都知道作品要写出一方水土的文化和传统,才有一定的价值,但是,雪漠有一个比其他作家更出彩的地方,就是他能把丝绸之路的文化历史,跟整个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勾连起来,然后借助他的故事和精神结构,让他的灵魂叙事能够突破中华文化的范畴,在这一点上,雪漠是有野心的。如果我们系统地读雪漠作品,就会感觉到他的努力和运筹。雪漠在《野狐岭》中的努力,就是借助于他在东莞的经历,把凉州文化和岭南文化进行想象性勾连,而且这个勾连在作品中是通过木鱼妹的线索来实现的。当然,要完成这样的目的,雪漠在人物和情节的构成上,就肯定要带进很多东西,而且要面对一个很大的难题,情节必定会复杂很多。看完《野狐岭》后我甚至想,如果雪漠把那核心的故事——也就是磨坊的故事单独拎出来的话,其实一个中篇的架构就足够叙述了。但是,假如把它变成一个中篇,只写磨坊的故事,那么它跟当代的很多作品放在一块的话,就不觉得它有多么出彩、多么令人惊奇了,它的意义也会降低很多。就是说,这样一个透视人性善恶的、具有超越性的故事,是需要确定一个自己特有的文化方位,并且需要大量的背景来支撑的,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宗教背景、精神超越的背景等等。然后,那个核心故事在不断呈现的过程中,才会体现出它背后的意义,也才能带给我们一个思考的空间,包括一种超越性的启示。
我想,这也是雪漠在叙事方式上面的努力,而不仅仅是“招魂”这样一种方式。招魂只是一种外在的方式,而且,让死人回顾往事的大陆作家其实很多,比如方方的《风景》就是其中之一。这种形式本身并不是非常复杂的。但雪漠借助于这样一种文化方位的设计,这样一种精神结构,把中原的核心政治和边缘文化,以及佛教文化——甚至在佛教文化的背景中,他也把藏传佛教进行了勾连,但藏传佛教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书中有很多修炼方式都属于藏传佛教——民间文化——把凉州的说唱艺术和东莞木鱼歌进行勾连,而且这两种民间说唱其实跟佛教传统本身也是连接在一起的——连接在一起。就是说,他把最世俗化的生活和最具超越性的佛教背景勾连在一起了。雪漠在《野狐岭》中的努力,是很令我们感到欣慰和高兴的。与《白虎关》相比,作为小说的《野狐岭》,或者说作为小说家的雪漠,在宗教精神和世俗生活的关系上处理得更成功了。因为——也许是我的个人倾向——我不太喜欢作为小说家的张承志在《心灵史》中对信仰和世俗的处理,我觉得,小说终究是一种以世俗生活为材料的语言叙述,如果你过于把世俗生活排除在叙述之外,哪怕精神立意再高,实际上也就降低了超越的力量,最后也就降低了小说的力量。
——(本文选自《出版人》杂志2014年12月17日第12期)
转载: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OTU5MDYyMw==&mid=201713635&idx=3&sn=af5ecb72f58231f7e0c09dc7ff2e6d99&3rd=MzA3MDU4NTYzMw==&scene=6#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