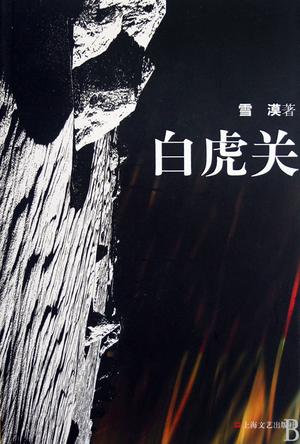
论《白虎关》的三重意蕴
《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4期
摘要:《白虎关》是西部作家雪漠的又一长篇现实主义力作,在这部作品中,作者展现了西部农村生活的变迁。显性的地域文化与隐性的哲理思考相结合,以诗一般的语言表达了思辨的哲学精神,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地域文学之限。
关键词:地域文化;隐性的哲理;人生与生命的追问
《白虎关》是西部作家雪漠继《猎原》与《大漠祭》之后的又一心血之作,老顺一家的故事也在本部小说中告一段落。读者阅读他的文字,需要依靠个人的阅读经验与想象去感受他的文学世界。顺“流”容易,逆“流”则难,在物质利益至上的今天,雪漠选择了一条冷僻的写作之路:用心去敬畏文学之神,在沉思现实的长久寂寞中,以韧性的方式,饱含深情地叙述了西部农民的生活,呈现西部底层生活中真实的东西,并对整个群体及人生进行反思。如果说文学是对命运的展示,那么《白虎关》所展示的不仅仅是老顺一家的遭遇,也是整个西部农村生活的辛酸。
《白虎关》基本上运用了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但作家的立足点和内容的整体象征意味超越了文本的时空,写的是西部却又不仅仅是西部。作者没有沉浸在对西部神秘的描写上,而是以一种挚爱的、忧郁的目光凝视着脚下的厚土并思考着这片土地上发生的悲欢离合。被生活的现实与难言的伤痛煎熬着,敏感的心不能安然,因此,一种深刻而悲凉的人生哲学便贯穿其中。文似看山不喜平,《白虎关》中交织着多种情感,阅读《白虎关》是一次情感的冲击,也是一次精神的炼狱。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它是一部具有丰富意蕴的现实主义杰作。 大体来看,作品可以分为以下几个层次:第一层是显性的地域文化层。在《白虎关》中,作者用了大量的文字描写西部农村的风土人情、地理环境、奇异的大漠风光,以及商品经济给西部农村与农民生活带来的表层变化。这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对乡村青年男女的恋情、偷情,婚嫁礼仪与生活习惯的描写。对相亲习俗的描写风趣、诙谐,“丫头一过去,就是掌柜的,左手抓住,右手捧银,前脚踢秤,后脚关库房门,有你们老两口享的福呢。”齐神婆生动、鲜活、夸张的语言,让相亲的主角猛子偷偷的笑,也让读者忍俊不禁,齐神婆职业媒人的形象跃然眼前。二是对民歌“花儿”的描写。“花儿”是西部文化的象征之一,也贯穿在这部小说的始终。沧桑的土地赋予了“花儿”生命力,富有生活气息的“花儿”凝聚了西部农民日常的喜怒哀乐,给贫穷的日子增添乐趣或是给绝望的心带来一点希望。苦难的生活让莹儿变得执着与坚强,一曲曲荡气回肠的“花儿”则让她有了“惨痛后的微笑”,“凉州女人在花儿中读懂彼此的心”。三是对大漠风光的描写,荒凉无边的黄沙中也有蓬勃的生命力。沙漠里有可怕的豺狗子,有晚来疾的漠风,有沙狐子、沙老鼠、沙娃娃、沙米,也有盐湖和抵御风沙的芨芨草,这些不屈的生命力让广袤的沙漠不再沉寂。四是对西部农村女性生活的描写。前三个方面的展现让人以愉快的心情领略了西部风光,然而这一生活表象的描写却让人悲从中来。艰苦的环境腐蚀了女儿性,青春在满目的黄沙中昙花般开过,晶莹的心过早地为生计而劳碌。没有爱情也没有尊重的婚姻摧毁了女性最优秀的东西,“兰兰又挨打了,白福抡着牛鞭,跟捶驴一样,捶了她一顿,红的紫的血道儿织了一身”,“更可怕的是,谁都觉得这是命”。这冷静的叙述里有着比贫穷更可怕的东西。五是商品经济给西部农村农民生活带来的变化,“白虎关的金窝子多了起来”,隆隆的机器声,飞扬的尘土,喧嚣的人群,曾经安静的乡村不再宁静,月儿也回不到记忆中的家乡了。作者对农民形象的描写没有符号化,在表现他们的表层行为时,深入到他们的精神深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他们勤劳、善良也不乏狡诈与愚昧,文明的程度往往与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作者为我们呈现了农村生活的真面目。他深情的关注农村生活,更以理智的思维,站在中西哲学文化的基础上审视生活背后的东西。这就是文本中的第二个层面,即隐性的哲理思考层。
隐性的哲理思考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浓郁的儒家思想及对儒家思想的扬弃;朴素的道家思想;发展变化的观点与辩证的思维。
小农经济是儒道思想产生的土壤,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发展并没有消除儒道思想对人们的影响。反而在时间的长河中渗透到不同阶层、不同地域的文化中,形成了一种潜在的心理因素,从而影响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行为方式。也许在不同的群体那里表现方式各不相同,但本质的东西是不会变化的,最多是大同小异而已。“克己复礼”的儒家思想有儒的安宁也有儒的残忍,“顺其自然”的道家思想能够暂时回避生活的痛苦但也消解了人们改变现实的可能性。儒道思想作为一种民族文化精神制约着作者,也制约着作者笔下的人们。
莹儿、兰兰、月儿是文中三个最有立体感的形象,一如她们的名字般美丽善良。然而,这样的三个女子却各有各的不幸。善良的莹儿在丈夫死后陷入了两难的处境,爱灵官而不能说,又无法反抗父母要求改嫁的命令,“克己复礼”的思想在莹儿心中根深蒂固。经历了生离死别的她只好在再婚之夜吞服鸦片而死,让人想起几千年前“自挂东南枝”的刘兰芝。以喜写悲悲更悲,再婚之夜就是生命的尽头,一个年轻的生命从此消散了。从古至今,“天下无过错父母”的思想扼杀了多少年轻人的爱情与生命?莹儿与兰兰是作者批判儒家文化的载体,所不同的是,兰兰最终走出了一条生路。她是儒家文化的牺牲品,也是儒家伦理的反叛者,她按父母之意认命了自己的婚姻,但当不能为夫家生个继承香火的儿子而遭打骂,女儿又死了时,她想到了离婚。“在牛鞭和拳头中度过一生,实在不甘心,她不想走母亲的老路”,为了摆脱自己难以解除的苦恼,她去金刚亥洞里修行为,以希求得心灵的安慰。然而,金刚亥洞里也不是一片净土。后来,莹儿的死给她上了人生的一课,在沙漠小道上徘徊的她,要去寻找自己的人生路了,幸福于她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如果说莹儿、兰兰的形象反映了作者对儒家文化批判的思想,那么月儿的形象则可以看作是对传统儒家思想某些方面的继承。月儿不愿在满目的黄沙中生活一辈子,她走出了这片贫瘠的土地去城市寻找更好的路,然而,她却被城市生活弄得头破血流。固然,月儿的不幸有城乡文化差异与商品经济的冲击之故,可是我们也应该更远的想一想:如果月儿能够坚守儒家“克己”的思想,她的命运会不会是另一种样子?兰兰的真、莹儿的善、月儿的美,洋溢在文本中,是真善美的象征。无数个她们在西部的大地上绽放光彩,也在继续她们的悲情人生。真的东西依然在艰难中继续,善与美却消失了。笔者认为,这可能是作者内心矛盾无法调和的结果,也可能是商品经济下真善美无法融合的反映。当经济的发展淡化了道德意识,人们无视传统文化规范时,传统文化的力量就会显现其积极的一面。
“顺其自然”的道家思想中和了儒家思想对人性的束缚,很多时候,“人生的积极意义并不全是在积极本身中显现,倒常是在虚幻中得到了其价值的体现”[1],道家思想的内在美就在于减少人的痛苦,也常常是失败者安慰自己的一剂良药。老顺的“末日就末日,死就死”的人生观是道家思想的典型体现,花球的“活人嘛,你想咋样?闭了眼,咬了牙,就是一辈子”,这种朴素的生存哲学减少了花球的欲望,暂时回避了现实生活的痛苦,可是也消解了年轻人本该有的进取之心。正确对待传统文化是当今人们应该思考的问题,作者看到了儒道文化的两面性,既未一味地赞扬也未一味地批判,让读者自己去体会。
在这本以写实为主的小说中,作者用诗一般的语言表达了思辨的哲学精神,农家女秀秀“有多红就有多黑”的观点道出了生活中很多事物的两面性。“青丝被鹤发取代,水红叫皱纹覆盖,细腻被风沙吹去,浪漫叫穷困吞噬”,这蕴含着时间的无情与人的无奈,风沙吹去心中的浪漫,生活现出绝情的一面。在历史的长河中,在现实的生活中,人如尘埃般渺小,生存是如此的艰难,生活充满了不安定因素。面对经济浪潮的冲击,城市文明对乡土文明的渗透,偏远土地上的年轻一代该如何面对?这不仅仅是西部农村年轻人的问题也是当今时代人人都要面对的问题:人生之路该怎样走?如何塞所说:生命是否有意义并不是我的责任,但是如何安排人生却是我的义务。这就是文本的第三重意蕴:对人生与生命的追问。
对人生的思考是一个永恒的问题,然而却永远没有标准答案。生命充满了太多的偶然与必然,想到最终的必然还有什么不能释然?人生真如孟八爷说的“人吗,就是活个心”,还是应该像沙漠中的骆驼那样“无论有风,无论有雨,它总是很悠闲”?猛子渴望智慧之手去抚慰他的灵魂,但又哪里去寻智慧之手呢?人生与生命的空白无处不在。绝望与希望折磨着芸芸众生,不论贵贱。文本的最后,作者借用了希腊“西西弗斯推石上山”的神话,从一方面来说,西西弗斯面临的是永无止境的失败,从另一方面来看,他每一天的生活都充满希望。生活最伟大的智慧,必须能在所有方面,在我们的失败、过错和由于我们的愚蠢而造成的罪恶里,痛苦地接受我们的有限性[2],因为“世界并不因你的慌张而迎合你”。人生的悲剧大都是性格的悲剧,生活的态度隐藏在人的性格中,炽热与冷静是面对生活的两种方式,炽热也许能融化生活之冰,但难免有曲终人散的落寞,冷静带来理智也会因此多了些烦恼。太认真或太执着是对还是错呢?欲望的实现带来满足也带来更大的空虚。从“心幸福,人就幸福”到“比死亡更可怕的是心死”再到“心是一派荒凉了。一切,成了灰色的影子,虚虚幻幻,若有若无”,绝望与无奈感挥之不去,留在作者的文字里也留在读者的心中。生产力的发展可以解决物质的贫乏,但无法解决人们精神的困惑。综合整个文本来看,以儒治世,以道修身,以佛养心,是作者理想的人生方式。雪漠把他的情感隐藏在客观的写实中,弥漫整个作品的是人生的孤独和悲凉感,“谁来指点迷津?谁来做我的上师?谁能给我以清晰?”三个急切的追问里读出鲁迅式的悲凉,也读出孤独的力量。“我”是个体,也是一个时代的群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观,都要面对不同的人生与同样的虚幻和悲哀,“西西弗斯”的精神也是当今众多人生活现实的写照。人生有限心无限,待到眼前烟云散,纵是有梦亦惘然,孤独彷徨与谁言?空留多情在人间。
作者在文本的这一意蕴里提出了一个普世性的命题,它打破了地域文学的界限,扩大了文本的时空,赋予了作品更强的生命力。作者在题记中说:“当一个时代随风而逝时,我抢回了几撮灵魂的碎屑”,作者抢回的仅仅是灵魂的碎屑吗?有深度的作品应该像一座山,带给读者“远近高低各不同”的感受,也让远近高低处的人各有风景看。在《白虎关》中,没有刻意追求技巧和方法的痕迹,但作品很有智慧、很好看,有思想启迪而无教化意味,有心灵的深度震撼而不仅仅是感动,是“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也是“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它将西部的小说创作提升到一定的高度,又为当下的文坛吹进了清新的气息。
参考文献:
[1]吴炫.穿越中国当代文学[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161.
[2]何光沪.蒂里希选集(下)[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951.
作者简介:
李贤(1983-),女,安徽六安人,硕士,蚌埠学院(安徽蚌埠233030)文教系助教,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曹永光(1961-),男,山东省安丘市大汶河开发区十里中学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