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现代理论无法解读西部文学
澎湃新闻记者 徐明徽
8月24日,上海思南文学之家吹进了一股强劲的西北风。来自西部大漠的甘肃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西部文学代表作家雪漠携首部自传体长篇散文《一个人的西部》和最新长篇小说《野狐岭》,与文学评论家陈思和、上海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资深编辑曹元勇一起,对谈“西部文学的自觉与自信”。
“西部文学”的提出已有三十年,但直到今天,似乎仍是一桩理论悬案。三位嘉宾从雪漠近期创作谈起,围绕西部文学展开了对谈。澎湃新闻记者专访了雪漠。
提到西部,曹元勇认为可以从四个方面去认识。“首先是地理上的西部,包括西藏、新疆、甘肃等;再者是文化的西部,西部文化非常复杂,宁夏、甘肃、内蒙古、西藏这些地方的信仰思想都不一样,有佛教文化、道教文化、伊斯兰文化、维吾尔文化、汉族文化。到了西部你会惊叹于眼前的世界,也会感叹自己缺乏享受那样多元文化的能力,因为你不了解。雪漠在《一个人的西部》中提到‘凉州贤孝’,一种当地说唱形式的地方戏,我们就从来没听说过”。
“第三是精神上的西部,西部每个地方可能都有不同信念,甚至一些神秘的东西,这在中原地区其实也有,但我们较少书写,西部作家的作品中都能感受到更多。我看《一个人的西部》,雪漠父亲身上那种‘老天给什么,老子都能承受住’的这样非常朴素的信念也很触动人心”。
“还有就是文学的西部,从西部立场出发的文学。中国现在有影响力的一批大作家,其实还是与‘寻根’有关。1980年代改革开放,因为经济原因,我们在追着美国、西欧、日韩走,文学上也是,很多作家写作也在追随,包括各种流派,包括魔幻现实主义。今天回头再看,会发现这样是有局限性的,反而是走‘自觉’道路的成功了,包括莫言、张承志、雪漠这样的,从一开始就没有跟着所谓西方最流行的现代派走。用西方的现代、后现代文化的一套理论来看待他们的时候,是无法理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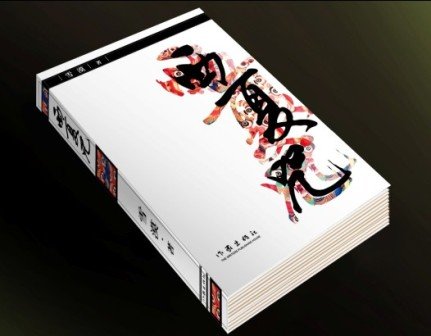
雪漠另一部长篇小说《西夏咒》出版时,曾有评论认为这是中国西部的《百年孤独》。曹元勇并不认同这样的说法:“其实这就是西部土地上生长出的先锋样式,包括《野狐岭》。我们在自己的体系中找不到标准,就只能用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来诠释了”。
西部文学中强烈的精神性,可能是与东部文学最明显的差异性之一。“西部文学的精神是与那个地方的天、地融为一体的东西,这个你在北上广编不出来。我们今天可以一起讲究喝茶、讲究咖啡、讲究美食,但西北人不会这么做,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方式。在贫穷的状态下,人需要靠精神维持,因而他们精神上的东西就会非常强。雪漠跟张承志是中国当代西部文学作家当中最有精神性的”,陈思和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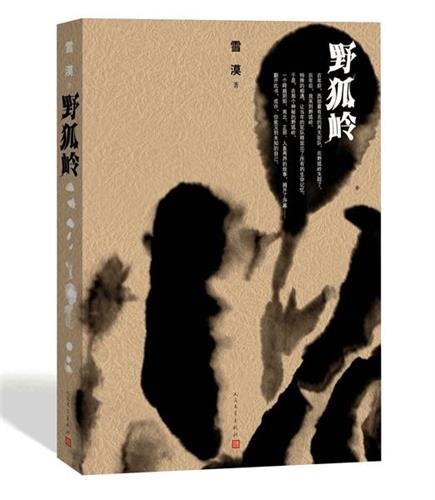
在《野狐岭》中,人物之一马在波与一个革命者在沙漠中争执,两人追求不一样发生了争执,革命者说“别去找了,找到是空,不找也是空”,马在波反问“既然都是空,那你革命做什么,今天反清朝是这样,反明朝也是这样,为什么还要革命”。陈思和回忆小说中的这一情节给他带来的触动:“两人斗嘴,突然间把人生许多执着破除了。现在我们倒是可以为了一点事情争天夺地,吵架了无非就是要多讲最后一句话。人生有许多执着,这种执着可以鼓励我们去奋斗,但不要被它束缚住了。雪漠的作品中有很多这样的一层一层的东西,慢慢体会非常有意思。”
西部文学在当代文学中仍处于被遮蔽的状态,现代都市文化可以容纳下西部文学吗?陈思和认为未来的“文学大家”应该出于西部,不能用东部文化去改造西部文学。“东部城市、都市文化正在走向碎片化,西部因为生活方式不同,它呈现的是一个完整的思维,一个人从生到死的呈现,这种哲学在中国非常重要。我觉得以后的‘文学大家’应该是出在西部。我们现在看小说文本,觉得故事要有头有尾,要有高潮。但是西部的文学好像常常没有这样做,为什么?西部太大,好比你从早到晚在沙漠中走,走了一天一夜还在沙漠,这就会产生另一种文学,不是靠故事支撑。我们对西部文学叙事背后的精神力量都讲不清楚,顶多就讲一句‘他们富有诗意’。好比张承志的《心灵史》,这到底是小说还是史诗?我们首先应该去解放自己,生长出一种新的审美系统,就能解读它们了。”
曹元勇也认为,文学发展至今有其多种多样的形态。西北有雪漠、西南有阿来,新疆也有李娟这样的文字。文学有自身的生长的规律,尤其面对经济全球化,文学本身具备一种反叛和抵抗的自然的天性。
“我们首先应该去解放自己,生长出一种新的审美系统。我们的阅读审美受西方文化影响,但我们接触的西方也很局限,读者也不了解南非文学、阿拉伯文学,都是德国法国的西方、美国、英国的西方。但其实还有东欧、有巴尔干半岛,他们也有无数大师和思想家,文明是多级的。”陈思和强调,“如果世界上只有一个青藏高原、只有一本《百年孤独》,也是很可怕的。”
“西部文学需要北上广这样大城市平台的关注,但不是被改造。从西北吹来的这阵硬朗雄壮之气,对中国文坛是有好处的。我认为现在西部文学还远远没有得到重视,没有得到应该属于它的荣耀。”陈思和说。

◎澎湃新闻:《一个人的西部》是你的自传,如何想到在这个年龄就开始写下回忆录?
●雪漠:这本书从文学上来看,是一个文学青年的成长史,但又不止是这样。写《一个人的西部》的机缘是不期而遇之的。我不喜欢总是回忆过去,也不喜欢外界的干扰,算是有一点拒绝外面的世界和声音,所以闭关独居20多年,训练自己化除杂念,深入内心极致就有智慧而出。
但因为儿子结婚遵照风俗要回老家请客,我必须得回忆过去,该请谁,不该请谁。回忆中仿佛整个事件都被打开,在那个赤贫的年代下,30多年间世事变幻,朋友们各有不同命运,巨大的沧桑感扑面而来。如果把这个过程、这么多种命运记录下来,可能会给读者带来启发。我写作得非常快,30年感悟的冲动非常强烈,很多文字就这样流出,不由自主。寻找一种活着的意义,这是我写作的意义。
◎澎湃新闻:《野狐岭》讲述了百年前西部最有名的两支驼队在野狐岭神秘失踪,故事中的“我”通过召集幽魂,从各个不同角色,呈现了真相的各个不同侧面。这与你之前的小说又有很大不同。
●雪漠:《野狐岭》不是那种人们熟悉的小说,而是另一种探险。其中的人物和故事,像扣在弦上的无数支箭,可以有不同走势和轨迹,甚至不同目的地。因为这个故事是由很多幽魂叙述的,我有意留下了一些支离破碎的片段,淡化了小说的主题,因为一旦有了明显的主题,你的想象力就会受制于它。只要读者愿意,可以考证和演绎它。
《野狐岭》的主要内容,如凉州英豪齐飞卿的故事,我酝酿了很多年。在三十多年前,我刚工作时,就想写这个故事。写《野狐岭》前,除了我调往齐飞卿的家乡任小学老师外,我还采访了书中提到的马家驼队的子孙,采访了很多那时还健在的驼把式,了解驼道和驼场的一切。
这本书中还有关于木鱼歌、凉州贤孝、关于驼队、驼把式等许许多多消失或正在消失的农业文明的一些东西,这是和我以前的小说“写出一个真实的中国,顶个一个即将消失的时代”一脉相承的。

◎澎湃新闻:你的几部长篇小说中,容纳了诸多西部土地上的传说、风俗、历史故事,你是如何获得这些素材并融入作品中的?
●雪漠:这需要作家对书写的土地有深入的了解。第一,了解这片土地上的所有相关资料,包括历史、地方志、笔记记载等。第二要寻找到这个地方讲故事的人,可能是一个,也可能是很多个,他们可以让这块土地上的很多东西鲜活起来。许多东西不是文字记载的,而是一代代人口口相传而来,是一种群体记忆,这是非常有价值的。很多作家可能就是因为没有找到,所以作品内容缺乏活力和连接。在写《野狐岭》之前的十来年,我一直在积累相关的故事,寻找这些人。写《猎原》之前,我跑遍凉州,多次前往草原和大漠,采访了上百位猎人和牧民。第三就是去当地生活,我会有意识地在一个地方住很长时间,去感受土地的脉搏。这些你都做到、经历过后,你的灵感自然会喷涌而出,不需要刻意编故事,而是所有的故事向你涌来。你去看许多作家作品,是能感觉到哪些作品是喷涌出来的,哪些作品是挤牙膏一样挤出来的。
◎澎湃新闻:你的小说争议很大,《西夏咒》、《无死的金刚心》出版时,喜欢的读者认为作品中斧头劈出的粗粝让文本充满力量,但是叫骂声也有。你怎么看待这种争议?
●雪漠:不要紧,哪怕这世上所有的人都在乎和赞美你,等这一茬人死后,你仍是下一茬陌生人,批评声也一样。最重要的是,你能不能留下让下一茬人也记住的东西。再者,我认为读者有批评也很好,他们在批评你的同时,可能他们自己会注意不要犯上他们所批评的缺点,这很好。之前很多不喜欢我作品的批评家,还和我成为了朋友,哈哈,当然他们还是继续批评我。
◎澎湃新闻:《无死的金刚心》是一部很特别的作品,写了被誉为“雪域玄奘藏”的藏传佛教香巴噶举派祖师琼波浪觉的一生经历。评论家认为这部小说犯了很多小说不能犯的忌,比如充溢于字里行间的思想。
●雪漠:对传统小说规则来说,写思想是犯忌的,都说思想会腐朽,生活之树却可以常青。但在我眼中,那些“忌”,正是我作品的魂。如果不写这些,还不如扔了笔去晒太阳。我要写的就是这种死不了的魂,无论啥规则,要是做不到这一点,我便要打碎它。不要希望我拿腔拿调地写一部四平八稳、循规蹈矩的小说,世上到处都有这种东西,要是想看它们,走进任何一家书店,随便抽一本小说就是。我不愿意浪费自己的生命去遵循别人的标准,我有自己的标准。
◎澎湃新闻:你的一些小说甚至有些不像小说,对你本人和作品的定位外界也各说纷纭,有说你是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象征主义,也有说是魔幻主义的,你怎么看?
●雪漠:我觉得我什么主义都有,和我自己表达的内容有关系。我感受到的是一个博大的世界,表达出来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世界丰富了,所以写出来的东西也丰富,也就出现了很多所谓的主义,如果一定要说主义,我应该是理想主义,我的作品都有理想主义的色彩,有乌托邦梦想,总希望未来比现在更美好,也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让世界变得更好。
雪漠文化网,智慧更清凉!www.xuemo.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