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假如你不能彻头彻尾地改变你的生活,至少你可以改变你的环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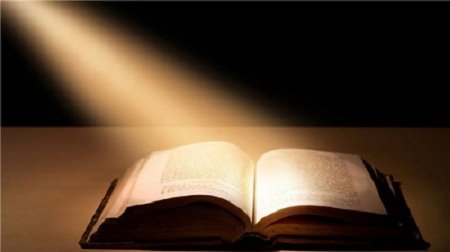
诺奖得主索尔·贝娄为何逃离?
诺曼·马内阿 著 邵文实 译
◎马内阿:我们正在讨论意识形态与艺术之间的联系,信仰与艺术良知之间的联系。我很想说,对于一个像你这样的作家,重要的事是艺术调节歧义性的方式。你坚持把歧义性放进来的方式。
●贝娄:谈论它、理解它会很困难。我不得不想一想这个问题。
◎马内阿:是的,因为你在小说中所知道的事不一定是一个问题的答案。
●贝娄:是啊,我有答案,然后我也有问题,我的意思是:我从之前的某时起,已不再寻找定局,寻找最终的解决之道。我似乎相信那些我从来不知道我相信的东西,这些是无论我喜欢与否都至关重要的东西。所以它不再是一个我对之进行推理的问题,而是我与之共生的问题。你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你不再努力使一种立场尽善尽美,而是正在容忍你不知何故就是无法摆脱的秘密偏好或秘密的解决之道。你将永远无法摆脱。你现在知道了那一点。
例如,我不再与自己辩论有关对上帝的信仰。它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所有这些年来,我真正的感觉是什么,而所有这些年来,我一直信仰上帝;事情就是如此。你会拿它怎么办?所以,它其实不是个有关将自己从约束中解放出来的智力问题,它首先是个有关试图决定这是否是种束缚然后接受你所相信的东西的问题,因为那就是你至今能做的一切。
◎马内阿:是的,我想这正是我们面对死亡这个极其不可抗拒而又无法解决的话题时的状况。卡内蒂(Canetti)过去常说,在他看来,死亡是人每天都得面对的敌人——真正的敌人,他一直对它怀恨在心。我知道,你思考过很多有关来世的问题。也许不是作为艺术家,但我知道,你一直在解决这个问题,即死亡的意义。
●贝娄:是啊,它迫使你要严密关注它,不是吗?我现在更倾向于跟着我真实的感觉走,而不是跟着我的思想走。人生短暂,时至今日,我觉得我不能靠着理论问题到处招摇撞骗。
◎马内阿:假如我们接下来回到写作、回到你的想象是什么上……
●贝娄:我没有对作家的特定想象。我要告诉你我一直以来是什么样子,从我睁眼看这个世界起,我便对它对于秩序思想的控制有了印象,那种秩序思想其实不会对所有人起作用。对于这其中的任何一种情况而言,更为根本的都是一种很难与任何人交流的独一无二的观点。当我还是个孩子时,它足够简单:这个人有副深沉的嗓音,一个尖尖的鼻子,他歪戴着帽子,牙齿稀疏,等等。你将它们全都放在一块儿,那就是这个人,他是这一个和那一个要点的整体结合,这些要点要么是他的嗓音,要么是别的任何东西。
这种直觉的知识是孩子气的,但它并未随着孩子而消失不见,它会持续下去,正如你所知道的那样。在某种重要的意义上,这是真的,而假如它不是真的,人们就不会对你正在写的东西有任何的关注。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对于所有人而言,它都不可避免地是真的。这也就是这种现象学、你个人的现象学使你成为一个艺术家的秘密原因。你对它无能为力,而思考它并不会有多大的帮助,因为它是对起源的思考——好吧,那不是我的工作。我的工作是做我自己。在做自己的过程中,我正在成为这样一个简单而重要的现象学家。
至少,这是我的方式——我现在正在结清账目,在我离去之前——这是我解决这一特殊问题的方式。这是成为一位艺术家的意义所在。首先,你看到了你以前从未看到过的东西;你睁开眼睛,那里就有个世界,这世界是个非常奇怪的地方,对于它,你有自己的版本,而非任何别人的版本,而你会忠于你的版本以及你看到的东西。我认为,从个人意义而言,那是我成为作家的根源所在。你完全知道我的意思是什么。
◎马内阿:是的,我希望我知道。我知道,神秘依旧存在。有那么多的著作和冒险——我也指精神冒险。不过,当我们读你的著作时,我们有种这样的感觉:神秘、奇迹依旧存在。
●贝娄:我相信是这样。我不打算太多地谈论它,因为它是大家都不大想孤立来谈的话题之一。
◎马内阿:作为作家,你被呼吁采取一种道德的立场,一种开放、公开的立场,然后再返回到你的写作之中,这是十分困难的,不是吗?这好几次发生在我身上,结果,我无法回归真正的小说,因为我深陷在立场选择之中。我非常不喜欢这样,从公众人物转向总是要回归歧义性的作家……
●贝娄:这个嘛,这无疑是对的,即你不得不过着双重生活,就此而言,也许是种四重的生活。我对此心知肚明,因为我每天都在经历它,正如你一样。我认为,在我生命中的某个特定的点上,我变得非常固执。我知道什么对继续当一位作家而言是不可或缺的,不会让任何事来干扰它,这与其说是为了我自己的缘故,不如说是因为我觉得应该那样玩游戏的缘故,于是对于此,我变得非常固执和任性,在我有其他选择时,偏偏将它们抛在一边。
◎马内阿:是的,但是你也会时不时地采取一种刺头的、并非总那么令人自在的立场。
●贝娄:没错。
◎马内阿:而你要应对由此带来的后果。你是怎么应对它们的?
●贝娄:尽力而为吧。你知道,我一直处于一种防御性的立场之上,捍卫真正重要的事,当人们把枪口对准我时,我会做出让步。我之所以能够时不时地做出让步,是因为这样做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
◎马内阿:但当你做出让步时,势必会造成损失,所以大家都宁可不做让步。让步是你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我明白,你后来从芝加哥搬到波士顿,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这样一种后果。你不得不离开自己热爱的城市,在这个城市中,你本是重要的文化财富,而在某一个时刻,你觉得必须离开。它不像我离开罗马尼亚那样艰难,但你依旧会觉得,你是被迫的。你怎么应对它?
●贝娄:让我们依照我提供的理性化状态行事。当人们问我,为什么你要离开芝加哥时,我说,因为如今只要我沿街而行,我就必须思考我的死亡,所以到了该离开的时候了。我在这里有个女朋友,或是到那里去参加个聚会,或是到那里参加一次会议,等等。大多数我知之深爱之切的人都离世了,而我不想占领一块墓地。那就是你开始有的感觉。还有另外一个角度,也就是说,我已变成了市里面的一个文化大亨。我其实不想扮演那个角色。我认为,这其中有某种非常恶劣的东西在。我不想被我看不上眼的人膜拜,我就是不想玩他们的游戏,因为在任何程度上,我太了解他们了。于是我想,让我们列一个新的人物表。我前往波士顿,我们得再试一次。好吧,一些发生在芝加哥的事情也在波士顿发生了,所以你复制了环境,但不管怎样,时至今日,你觉得轻松了一点儿。我说的轻松是比喻意义上的轻松。你丢掉了你的一些道貌岸然之举。
◎马内阿:所以,你所做的这个决定不是出于你在芝加哥最后几年中所遭遇到的敌意?也许我错了。
●贝娄:这个嘛,是的,是这样……数十年来,一而再再而三地循环往复。最后你厌倦了,于是,假如你不能彻头彻尾地改变你的生活,至少你可以改变你的环境。
◎马内阿:大体上看,波士顿是否对你自己有益?
●贝娄:是的,我很喜欢波士顿。它让我想起了我六十年前常常过的那种生活。难以形容。
◎马内阿:难道它不是也更欧化一些吗?
●贝娄:我想是的,但芝加哥也很欧化,以一种大相径庭的方式。它是农民的欧洲,芝加哥有很多的农民。
◎马内阿:你不是其中之一。
●贝娄:不。犹太人不擅长当农民。
雪漠文化网,智慧更清凉!www.xuemo.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