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文学更多的是一种净化,净化自己的灵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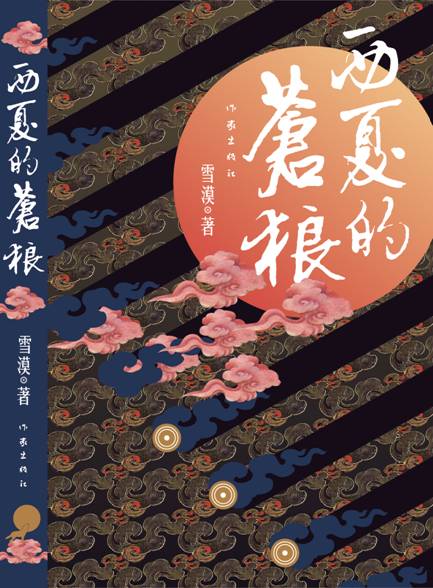
谈超越和永恒
(代后记)
-1-
表面看来,《西夏的苍狼》的写作缘于跟东莞文学院的签约。
的确,这是它出生的一个重要契机。没有这次签约,我不可能远离家乡数千里,客居在广东的山区小镇樟木头——后来,对这儿风景的痴迷,变成了我的一种执著,竟有点“乐不思陇”了。
我的生活,也因为这次签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曾对东莞文联林岳主席说:跟东莞签约改变了我后半生的生活。确实,要不是这次签约,我还可能静静地待在西部的“关房”里,时而执笔,时而打坐。我决不会想到,在数千里外的南方,会有一处我喜欢的地方,会有一个“爱我的”和“我爱的”群体。原以为会老死在凉州的,不想我这棵老树,却忽然移往他乡,绽出新枝了。
生命因善缘而改变。所以,我总是提倡与人为善。许多时候,我们小小的一个善行,改变的,却可能是别人的生活甚至命运。
我跟东莞文学院签约的决定,主要缘于雷达老师的推荐,也因了妻子的一句话——
一年前的一天,妻说:只希望我们平平静静地过下去。这当然是个美好的祝愿。我听来,却成了另一种含义:我们就这样等死吧。于是,我就想,该换一种活法了。
正是为了“换一种活法”,我才走出家门,来到南方。没想到,那块土地竟然欣喜地接受了我。在广州亚运会前夕,我竟然成了亚运火炬手,事儿虽不大,却象征了这块土地对我的接纳。
在一些朋友的帮助下,诸多因缘,一起齐备,我便客居于此了。很快,我有了一种鱼儿跃入大海的感觉。也许,那些加入“中国作家第一村”的朋友,跟我有着相似的感受吧。
我发现了另一个无与伦比的文化宝库。
记得,初到东莞时,有人告诉我:“这儿是文化沙漠。”后来,我才明白,真正的“文化沙漠”,不是东莞,而是那些没有发现能力的心。我在东莞发现的,仍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文化宝库。这儿除了木鱼歌这种可以与凉州贤孝相媲美的文化之外,几乎每个乡镇都有其“绝活”。它们同样根植于中国文化的肥沃土壤中,却又与时俱进,结出了时代和地域的硕果。那些明显异于西部的民俗风情,更激活了我休眠的许多诗意。
东莞跟我的家乡凉州一样,同样是一块有着浓厚底蕴的文化沃土。
-2-
对《西夏的苍狼》的主题,我思考了很久。对永恒的追问,一直伴随着我的生命成长过程。书中黑歌手的所有寻觅,其实也发生在我的生命中。
我一直在寻找永恒,却又明白,这世上没有永恒。我明知世上万象如风中远逝的黄尘,却又想定格存在。我洞悉这一悖论,却总是乐此不疲地追问,故自号“大痴”。
一天,广州的杨菲菲——她为我提供了本书中的一些客家生活——问我,您为啥叫大痴?
我告诉她:因为,我想在无常中创造永恒,我想在虚无中建立存在,我想在虚幻中实现不朽。我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不是大痴,又是啥?
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大手印文化熏陶,我有着看破红尘后的超然,却又提倡积极入世。我们虽然改变不了世界的终极结果,但却能改变我们当下的态度。看不破的“积极”,是愚痴,它多为贪欲驱使,如蒙了眼拉磨的驴子。“看破”后的消极,是人生大敌,佛陀称之为“焦芽败种”。有了出世眼光,有了“看破”的智慧,还要有入世的积极,才是大丈夫的行为。我老说:“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老祖宗推崇的菩萨,便是“看破”真相后,却依然“精进”地想改变世界的人。他们明知那所有的改变,也不可能永恒,却仍用乐此不疲的行为,在虚幻无常的世界中,营造一份相对的不朽。萤火虫虽只是短暂的存在,却是暗夜中最美的风景。
在深圳文博会上,我发现了一幅俄罗斯油画:黑暗笼罩着旷野,四顾无人,却有一个亮灯的窗口。它的光明虽然有限,却唱着暗夜里最美的歌。那歌的名字,定然叫“希望”。
我研究和实践大手印文化的目的,不是为了让我有巨大的“能量”,去改变世界。不是。我的所有目的,仅仅是想让我的心属于我自己。我不是想改变世界,而是无论这世界如何改变,都改变不了我真心的自主。对这一追求,《金刚经》如是形容:“不着于相,如如不动。”
换句话说,我想做的,便是想实现终极的超越,做到心灵的真正自由。
对这种终极超越的向往,渗入了《西夏的苍狼》。
-3-
东方哲学的智慧精髓便是超越文化——“超越”何尝不是人类文化的精髓呢?——不过,西方人所说的超越,是有条件的超越。东方哲学提倡的超越,则是无条件的终极的超越。
2009年,我曾在上海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上海大学、上海图书馆等处作了巡回演讲,其主题便是超越。同年11月,我跟铁凝、王宏甲等作家一同出访法国,参加“中法文化论坛”。我在法兰西学院作过一次演讲,主题也是超越。
法兰西学院创立于1635年,是法国独具一格的最高荣誉学术机构,下设五个学院。其中文学院设有四十个院士,终身制,只有在某成员去世后留下空缺时,才通过全体成员的投票选出新成员。被选为院士则意味着从此进入法国文化历史的殿堂,成为“不朽者”,其名字会刻在学院墙壁上,令后代永志不忘。——瞧,法国人想追求的,跟《西夏的苍狼》中的黑歌手一样,也是“不朽”或“永恒”。
那次“中法文化论坛”的形式是,由中国和法国选择最有代表性的作家和学者就某一题目,展开演讲并进行对话。我演讲的题目是《文学与灵性》,跟我就同一题目进行演讲和对话的是法兰西院士弗罗伦斯·德雷,她生于1941年,其父让·德雷也是法兰西院士。弗罗伦斯·德雷是法国著名的作家、演员、翻译家和剧作家。二十岁时,她在电影《圣女贞德的审叛》中曾扮演贞德,其文学作品多次获奖,久负盛名。
在演讲中,我重点介绍了大手印文化的超越智慧对文学的灵性滋养。因为当代人的灵魂已经陷入了热恼和焦虑之中,物欲的膨胀及人心的浮躁,给这个世界带来许多不安定因素。一方面,许多人陷于热恼和焦虑,不能自拔。他们非常需要心灵的滋养;另一方面,那些有益的文化滋养却早已尘封,无人问津了。在心灵滋养的供应和需求之间,出现了明显的断裂。
在中国作协张涛先生和翻译的建议下,我没有读备好的稿子,而作了即兴发言。演讲很成功,现场气氛非常热烈。我于是有了很多汉学家朋友。
从法国回来后,法国汉学家柳烟(音译)来信称:“我非常喜欢您的小说,也很喜欢您写的那些又偏僻又经常比人类伟大的风景,使我心里感到十分平静。如在道家思想中,如在一幅山水画中,人占的位置很渺小,如一滴水那么微小,才不去迫害他自己和他人的环境。所以,我很爱看您写的大自然的美妙和神奇,它们都富有诗意。您的甘肃老家离巴黎都市的吵闹很远,离我们也很远,但幸好,通过文学的存在,可以缩短距离,也可以让我们感觉到什么边界都没有了。”
在我们身边,其实有许多能够普世化的、能为世界认可的好东西。只是我们自己闭了眼睛,没有去发现罢了。
-4-
在法国,我的演讲题目是《文学与灵性》。后面的文字中,也渗入了这方面的内容。
灵性就是超越后的“自由”。自由超越了任何人类的概念、限制以及诸多的标准。超越是大手印文化的主要特质。
本书中的黑歌手想实现的,其实也是超越,他演唱的《娑萨朗》诗史,也是灵性的产物。
超越的追求缘于孤独。而真正的孤独,缘于灵魂的明白和无奈。
我也曾陷入孤独。我想建立永恒和不朽,但这个世界上却没有永恒。我们找不到永恒,我们没有任何办法留住眼前的一切,我们无法建立岁月毁不掉的东西。这样,我的追求和世界的本质之间就构成了巨大的反差,这就是我的孤独。我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许多作家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许多伟大的哲学家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所以,他们孤独,他们痛苦。他们觉得这个世界飞快地向我们不知道的地方消失而去,我们没有办法留住它,没有办法留住哪怕一丁点我们愿意留住的存在。正是这样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造成了我以前的孤独。所以,我很长时间没有办法写作,因为我找不到写作的意义。虽然我觉得这个世界可能会让我的作品永恒,但我知道这个世界都不知道能存在到什么时候。因为人类制造了那么多的可以毁灭这个地球无数次的核武器和原子弹;因为这个地球上的许许多多的人在疯狂地掠夺地球的资源,破坏着我们的家园。前些天,一个朋友告诉我,威尼斯的水平面上升了,那个美丽的城市也许在不久之后就会成为水下城市。这个世界飞快地消失到我们不知道的所在,而我们却想建立永恒。
这是许多智者不能不面对的一个命运悖论。
这也是人类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所以,我们是孤独的。真正的孤独不是挣不到很多的钱,不是得不到利益,不是得不到名声,也不是电视、网络对作家和纸媒体的挤压,不是这个。这种心外的东西造就不了孤独。孤独是发自内心的东西,跟外部世界关系不大。当一个作家非常在乎世界对你的看法时,说明他已经堕落了。他想追求美貌的女孩子,得不到时,他可能痛苦;他想拥有很多的金钱,想成为比尔·盖茨,而不能如愿的时候,他也可能失落。像他们的这种失落情绪不是孤独。孤独是一种境界,是一种很高的境界。耶稣想爱人类,他想博爱,但这个世界却容不下他,要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是孤独的。他会说,神呀,原谅他们吧,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就是孤独;在菩提树下觉悟的释迦牟尼,看到世上许许多多的人被一种虚幻的、正在消失的假象所迷惑,心中充满了贪婪、仇恨和愚昧。他觉得不能马上让这些人明白真理解除痛苦时,他是孤独的。当中国的孔子想向整个世界宣扬他的“仁爱”、却又不得不像丧家狗那样流窜的时候,他是孤独的。
真正的孤独是一种境界。
真正的超越就是从你非常在乎的外部世界中跳出来,超越这个世界。这才谈得到自由。若将世界喻为一个池塘,超越就是池塘里的莲花。从世界池塘里长出你自己的莲花,这才叫超越。当你已成为一朵莲花后,开始俯视池塘时,你发现里面有很多莲子,它们都可能成为莲花。但是,因为某种原因它们不得不陷在淤泥中不能发芽。这时,这朵莲花可能会孤独。它希望所有的莲子都能从淤泥中超越出来。当它不能实现这一愿望时,孤独随之产生。孤独就是这样一种东西。
超越则超越了一切概念。所有的名词,所有文学中的主义,都不是超越。超越是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不能限制自己心灵的自由。同时,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又都成了创作主体的心灵营养。世界可以让那颗心灵长大,可以让它丰富,可以让它博爱,可以让它包容一切。当整个世界不再成为枷锁,反而为我们提供了无数的营养和无数的可能性时,才能谈得到超越。
我也像书中的黑歌手那样,一直在寻找超越。我发现,大手印文化认为的超越自由和西方人所说的超越自由不太一样。上次我出访法国时,发现好多人在罢工。他们把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寄托在政策、法律等外部因素的保障中。他们要求的这种权利,是作为自己得到幸福和自由的一个条件。但大手印文化不是这样,大手印永远把目光转向自己的内心。它认为,超越在于心灵。当我们消除了贪婪、愚昧、仇恨的时候,当我们心灵的本有光明焕发出来的时候,当我们消解了小我真正做到了大爱和无我的时候,就可能得到自由。
黑歌手和紫晓追求的,便是这种自由。
-5-
德国哲学家马丁·布伯写过一部书,叫《我和你》。他认为,人类实现不朽有两种可能:“其一,是用至大无外的永恒宇宙吞没个人人生,让个体通过把自身的有限性,投入到宇宙的无限过程来获得自我超越,实现不朽;其二是用至大无外的‘我’来吞没宇宙及其他存在者,把居于无垠时间流程中的宇宙当做‘我’之自我完成的内容,由此铸就‘我’之永恒。”
对此,也可以理解为,第一种是消解自我。当博大的宇宙和大自然消解了自己的贪婪、愚昧、仇恨的时候,自由可能产生;另外一种就是当自己的心灵能包容整个宇宙和自然界的时候,自己的心像宇宙一样博大、丰富,像大自然一样宽容、无所不包的时候,也可能实现自由。
中国的智者们追求的自由是后一种。他们面对的,永远是自己的心灵。他们以战胜自己的欲望来赢得世界,而不是靠掠夺和侵略来征服世界。他们不会把自己认为的某种真理强加给世界,去实现某种所谓的自由。
大手印哲学中,永远是以塑造自己的灵魂为主。这个“灵魂”的“灵”字就是我们谈到的“灵性”,文学真正追求的正是这个东西。灵性和灵魂跟物质的关系不大,当人类基本的生存条件满足之后,幸福、自由、快乐都取决于心灵的明白与否。在我看来,那些罢工的法国人的生活已经很好了。他们肚子里有很好的食物,身上有很好的衣服,还有这么美的环境,很奇怪,却有很多人感到痛苦。
而本书中的黑歌手,只要能唱出心中的歌,他就会很快乐地活着。
中国西部是歌声的海洋,每一首歌都像大海的浪花一样,谁也不知道歌的曲目究竟有多少。西部许多地方,都有黑歌手这样的智者。正是有了他们,西部文化才绽出异常绚丽的色彩,喷涌着陈思和先生常常谈到的那种大地般的活力。
西部老百姓吃着小米粥、馒头、玉米这类东西,但他们觉得很快乐。为什么?因为,西部文化认为,大自然给了我们很多东西,能够让我们生存,我们当然很快乐。这时候,除了享受快乐和明白之外,我们不应该去掠夺别的东西。当我们用这一杯水能维持生命的时候,决不去掠夺别人的大海;当我们有一个苹果的时候,我们就把香蕉和其他水果让给别人去吃、留给子孙去吃。我们觉得没有必要把世界掠夺过来,放在自己的家中。
所以,西部人向往的自由,是消除自己内心的贪婪、愚昧和仇恨。他永远不去管这个世界怎么样,他活得照样很快乐。
中国文学中最本质、最充满灵性的,也是这一点。《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有时候吃不饱肚子,他爱喝酒,但常常没有酒喝。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他的心灵却得到了自由,写出了不朽的《红楼梦》,里面充满了灵性的智慧。《西游记》讲的取经故事,也代表着中国人对灵性的求索之旅,它是一次灵魂的旅途、生命的旅途。一个人从动物性的人,生下之后,充满着欲望、愚昧、仇恨。他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超越,一步步向西天走去。西天在传统文化的概念中,代表着圣地,象征着一种比人类更伟大的存在。在取经的过程中,主人公遇到了许许多多的妖魔鬼怪。当然,那所有的妖魔,都是我们内心的贪婪和愚痴所化。
我们每一个人在实现超越的过程中,必然要面对自己内心的欲望。当一个人真正降伏了欲望时,才能实现终极的超越。在中国古代哲学和大手印文化中,都充满了这种超越的智慧,我们把这种超越称为“得道”。这个“道”,是大自然的规律,是一种能与这个世界和谐相处的智慧。当一个人拥有这种智慧时,他就实现了超越。老祖宗于是说:“朝闻道,夕死可矣。”
在大手印文化中,更多地强调一种活着的理由。我们为什么活着?一个作家要追问为什么要写作?这就是活着的理由。中国几千年间的那些哲人,都在追问这个东西。老子、孔子、诗人屈原都在追问。当屈原找不到活着的理由时,他就放弃生命不活了。因为,他觉得存在的理由消失之后,存在是没有意义的。
在中国西部,有一种有灵性的狐狸,它老是拜月亮。当月亮出来的时候,它就作揖磕头,产生敬畏和向往,希望自己能像月亮那样放出光明。西部人把这种动物叫狐仙,这“仙”字,包括了超越、灵性和智慧等。而同时,我们又将不明白活的理由的人,称为“混世虫”,即浑浑噩噩过日子的虫子。
本书中的紫晓离开常昊的原因,也许就是不想做“混世虫”吧。
也许,正因为有了这样一种精神追求,人类才能活得更快乐、更明白、更自由。文学跟宗教、哲学、其他文化的目的一样,其终极目的就是给人类带来自由和快乐。离开了这个目的,文学就没有意义。所以,我常说,好的文学,必须做到两点:第一,世上有它比没它好;第二,人类读它比不读好。做到这两点的时候就是好文学,做不到这两点的时候就不是好文学。
好多人说:雪漠,文学拯救不了世界。我说,是的,文学有时连作家也拯救不了。比如司马迁,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暴君的屠刀总能随心所欲地伸向那些优秀的作家。但是,文学的无力是暂时的。因为,岁月或时光很快会让那些暴君的生命消失,但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这类作家的作品却永远定格在人类文明的时空中。
更多时候,文学能拯救的,只是作家和跟他有缘的读者。不过,当每个人都能从文学中拯救自己时,就等于拯救了世界。所以,我始终认为,无论读者也罢,作家也罢,能拯救自己的,永远是他自己。他是在拯救自己的过程中实现了超越。不过,当世人都能拯救自己时,也就拯救了世界。
-6-
我常说的自由和超越,跟西方人所说的自由和超越不一样。西方人常说的自由,更多地由制度、物质、宪法等因素来保证。我所说的自由,是无条件的自由。什么是无条件的自由?就是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种光明,它不一定依靠外部世界和外部条件来实现超越,而是明白的内心本身就能实现超越。这个世界虽然很复杂,但许多对我们的限制和束缚并不是来自外部世界,而是来自我们的内心。因为在我们的内心中,充满了各种概念,我们称之为“分别心”。人类的所有痛苦、烦恼都缘于概念和分别心对心灵的束缚。
大手印哲学认为,当人类通过清洗自己内心的污垢,通过清洗自己内心的贪婪、愚昧、仇恨,扫除了诸多垃圾之后,人类本有的、像佛陀和耶稣那样伟大的心灵的光辉就会焕发出来。当我们的心焕发出这种光明后,就可能实现超越。
换一句话说,西方人的自由更多地像月亮一样,它借助一种外界的力量,包括法律、物质或其他的一种制度性的保障来实现自由。我追求的自由像太阳,它本身要能发光,它要去照亮这个世界,而不是让世界照亮它。
当我们的心灵足够强大时,就能和这个世界对话。那时,我们的心也是一个非常博大的世界。它可以和这个世界对话、沟通、交流,但世界却别想侵略它。所以,我追求的超越,是要丰富自己的内心,清除心中的垃圾,让它像太阳那样发光,去照亮这个世界。就是说,世界无论有没有光,都不要紧,我自己的心会发光。
那么,文学如何实现这种超越呢?文学更多的是一种净化,净化自己的灵魂。一个作家,当他真正地拥有主体性的时候,就是当他的心灵博大、足以吸收这个世界的诸多营养,却不受这个世界的许多诱惑的时候,自由才可能产生。
这种自由是什么表现呢?
第一,他有一颗巨大的悲悯之心,却没有烦恼。他觉得这个世界给他的东西够多了,他不会贪婪地寻求更多的东西,不会掠夺更多的东西。大自然给他这杯水就够了,他感觉大自然太美了,他有一种感恩的心,他绝不会去掠夺更多的水。因为有了这种世界观,他远离了贪婪,自然也远离了烦恼。当我们拥有一颗巨大的博爱、悲悯之心,就自然没有贪婪和烦恼了。
第二,我们追求的自由是快乐的,从内心向外散发着大快乐,却没有欲望。一个满足的、自由的心灵可以观察到欲望,但欲望却干扰不了他。
真正自由的心灵就像镜子一样,能照出世上的一切,但外界却别想干扰它。它非常宁静。无论我们的来和去,镜子都是那样宁静。
我追求的智慧就像这面镜子一样。房子中有无数的人来来往往,镜子是明明了了的。但它不会看到美女就哈哈大笑,也不会看到醉鬼就非常讨厌。它本身也是一个世界。我追求的,就是能拥有明镜般的智慧,去照出整个世界,但世界却别想影响它。
就是这样。
黑歌手在寻觅娑萨朗的过程中,最后得到的,便是这种快乐和悲悯。
-7-
在“中法文化论坛”的那次对话中,法兰西学院院士德雷问我:你认为能有多少作家实现你所说的这种超越?
我告诉她,东方文化首先认为,一个作家首先是一个“人”。什么是人呢?人就是具有人的主体性。中国西部百姓对人的最高评价就是他是个“人”,再高的评价就是他是个“好人”。骂他的时候就说他“不是人”。
我所说的这个超越,就是真正的“人”应该追求的智慧。人不应该是外部世界的奴隶。只有这样,他才会成为我认为的完美的“人”。
一个作家,首先应该是一个完美的“人”。你要有一颗独立的心灵,有一种不受这个世界诱惑的智慧,有着非常强大的主体性。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你才有可能成为一个作家,才可能成为好作家。这应该是一个作家的底线。如果没有这种智慧,他不可能成为好作家,他只会制造文字垃圾,他只是一个写字的人,而不是一个作家。
一个作家,首先是要有独立的人格、拥有完美的心灵、拥有智慧、拥有博大的胸怀。在这个基础上,他才可能成为作家。如果没有这个基础,他不可能成为好作家。
所以说,我们认为的许多作家,其实不一定是作家,甚至不一定是“人”。
因为,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就是,一些没有智慧的人,却老是推销自己非常狭隘的“智慧”。比如,他甚至可能利用暴力和屠杀,将这种非常狭隘的“哲学”、“智慧”推销给世界,根本不去管这个世界是不是真的需要。如果一个作家被这样的暴力文化同化之后,就会去讴歌暴力。人类历史上充满了这样的东西,我们的世界历史中,几乎所有被我们讴歌的英雄,都是杀人最多的屠夫。
所以,直到今天,人类中的许多人并没有发现自己的局限,相反地他们仍在讴歌屠杀。你想,这个屠夫杀完人就死了,这种讴歌的文化却依托文字流传了下去,继续毒害下一代人类。于是,人类充满着暴力。这一代人死了,罪恶就会依托这种非常肮脏的文明,传给下一代人。所以,地球上的战争越来越多,民族间的仇杀也越来越多。
因此,一个作家如果没有达到“人”的标准去写作,这是罪恶。他会依托自己所谓的才华,把那种暴力,把那种仇恨传播开来,让整个世界都恶化。
-8-
在广东,最令我惊喜的,是这儿有许多我爱的或是爱我的朋友。他们大多是某一行业中的精英。在这儿,我甚至对百姓眼中的“官”也有着很好的印象。
真是这样。在广东,最令我高兴的,是这儿竟然汇聚了如此多的人才,竟然有着许多热爱我作品的读者。有不少读者从我的作品中得到了滋养,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某次,我刚住进东莞文学院,就拥来了数十位“粉丝”。东莞文联林岳主席每次谈及,总是感叹不已。
这一切,同样成了我的写作理由。
在东莞樟木头镇的一个山清水秀的所在,我完成了《西夏的苍狼》。跟我所有的小说一样,书中的部分构思和内容,十多年前就已有了雏形。那时,我便想写西部人到南方后的生活。不过,后来我才发现,《西夏的苍狼》并没写出西部人在东莞的生活,它其实成了一个寓言,它有着更广泛的外延和更值得追问的深度。它虽有毛病,却有其独有的光芒。许多时候,没有毛病的作品,便没有优势。因为,凭啥获益者,便因啥受到限制。有时的流行因素,恰恰可能是文学之大敌。
更也许,《西夏的苍狼》中那些世人眼中的毛病,恰好正是我的追求。我说过,我总是在打碎一些东西,其中也包括我的小说理念。我常常警惕的,就是时下流行的文学对我的污染。
也许,正像雷达老师在兰大演讲时说的那样:在目前的文学背景下,雪漠是个异数。
但我的想法却是,要是我写得和大家一样,我就不写了。我最珍贵的生命,最该写的,是一些无可替代的作品。所以,即使有无数不喜欢我的理由,那些最挑剔的评论家也会承认:雪漠的小说,是无可替代的。我写出的,是只有我能写出的作品。任何人的作品,都高不过他自己的心灵。
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是,我在刚开始写小说时,就有了一个包罗万象的构思。那时,我将它起名为《老顺一家》,我想通过对一家农民命运的描写,写活一个时代和世界。我想告诉世界我所有的生命感悟。那个小说虽然没有面世——其实它已经整形后变成了别的小说。——我后来的所有长篇小说,都是它的成长。它就像一个树根,长出了《大漠祭》、《猎原》、《白虎关》,也长出了《西夏咒》、《西夏的苍狼》和后面待写的《木鱼歌》。对前者,人称“大漠三部曲”。对后者,我称“灵魂三部曲”。
这,便是为什么我的许多小说总是开始于十多年前的原因。
那时,我并不懂小说创作的诸多技巧,我只想写出一个我感悟到的世界。而我在明白之后感悟到的,总是一个巨大的混沌。它是一种巨大的存在,我无法清晰地表达出来,总觉得我能说出的,并不是我想表达的那个东西,真的是“不可说,不可说,一说就错”。真正能读懂《西夏咒》的朋友,也许就会明白我在说啥。
所以,我最初想写的那种能包罗我之所悟的全息作品,注定是不可能成功的。幸运的是,后来,它虽然没有长成巨人,却承载了我生命和智慧的全息。后来,它的不同元素、不同章节,都像一粒粒种子那样,发芽,抽枝,开花,结果,成长为一部部新的长篇了。
我于是想,一个作家的作品,也许真像一些人说的,是一种生命的定数。我目前发表的几乎所有长篇,都源于我为文之初的那些“种子”。那时,我不过二十出头。我用了近三十年时间,才让那些种子发芽、抽枝、长成了大树,创造了一片很大的绿阴。
也许,这片绿阴,在日后的若干年里,还会带来许多清凉呢。
-9-
《西夏的苍狼》实践了我的另一种文学追求,体现了我对世界的另一种解读和感悟。我说出了许多该说但一直没有说过的话。
更重要的是,它是我写作处于黄金阶段的作品。写它时,我仍然涌动着无穷的生命激情,书中的主人公,也成为我的另一个生命体,承载了我的很多向往。
更也许,它会告诉世界,雪漠的作品为什么会有那样一种巨大的转折。从《大漠祭》、《猎原》、《白虎关》到《西夏咒》、《西夏的苍狼》,我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不管朋友们喜不喜欢,它总是我生命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在《西夏的苍狼》中,你会看到那种转变的由来和动力所在。
最后,该谈谈我感激的人了。这也是我的惯例。我总是忘不了那些帮我的朋友。没有他们的善心,便可能没有我的成功。所以,在过去出版的小说中,我总能提供一长串的感谢名单。这次,有点例外了。我重点谈一个人。
《西夏咒》出版之后,妻看了之后,说,你在书中写了许多应当感激的人,但最该感激的,却没有提到。她说我应该感激陈亦新,因为书中的诸多修改和构思,都是他提供的。这是实情。我不善于编故事,命运便给我送来了一个善于编故事的儿子。由于我自小就严格训练他的想象力,他的构思才能是我望尘莫及的。在这一点上,正应了“善有善报”之说,我在儿子身上的所有生命投入,都得到了超值的回报。他是我的第一读者和最后定稿者。
陈亦新还是我生命中的“恩格斯”,他源源不断地向我送来那些“英镑”。他一直在打理着一个私人文学院。由于他的努力,我才不再像过去那样为生计奔波了,也有了一些帮助别人的所谓“善举”。在《西夏的苍狼》中,我引用了他和陈建新的几段文字。某年春天,我们一同去藏地朝圣。那次经历,我直接嫁接到了主人公紫晓的身上。
还有许多帮过我的朋友,人数很多,不胜枚举,一并致谢了。
在此,向所有我提到的或是没有提到的帮过我的朋友表达我的谢意。
愿你们明白、快乐、清凉、平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