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百年孤独》成为中国文学从伤痕叙事转型转型的教科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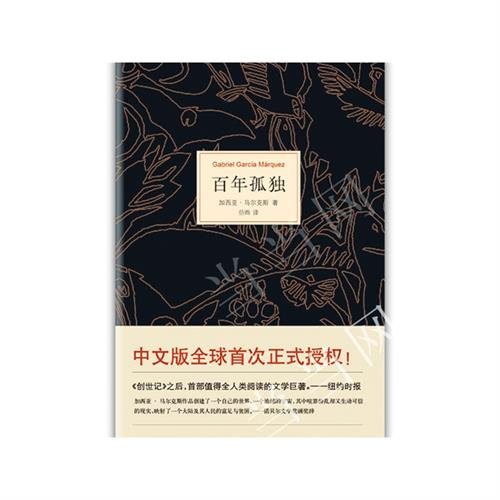
朱大可:马尔克斯同志的乌托邦
中国作家的仿写运动
尽管马尔克斯汉译本面临浓重的版权阴影,但经历了二十多年的自由译介之后,马尔克斯事实上已经完成了对中国读者的影响,高中语文课和部分大学中文系,均已将《百年孤独》列为教材。三联书城最近发布的“20年来对中国影响最大的100本书”名单中,《百年孤独》赫然在列。此外;《博览群书》杂志选编的《读书的艺术》,向读者推荐“近20年来对中国社会有重要影响的20本书”,也列入了《百年孤独》。这些迹象都向我们验证了马尔克斯在中国公众心目中的意义。
但仅有这些表面的热烈场面是远远不够的。马尔克斯的灵魂,已经渗透到中国作家的语法里,并与卡夫卡、博尔赫斯和米兰·昆德拉一起,对当代文学产生深远影响。在某种意义上,中国作家是喝着盗版马尔克斯的精液长大的。我们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作家清单,他们包括莫言、贾平凹、马原、余华、苏童、格非、阿来等等,几乎囊括了所有创作活跃的前线作家。
《百年孤独》成为中国文学从伤痕叙事转型转型的教科书。一种“马尔克斯语法”在作家之间流行,犹如一场疯狂的西班牙型感冒。
“许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良诺上校仍会想起他的祖父带他去见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这个《百年孤独》的开卷句式,出现在许多作家的笔下,从马原的《虚构》、莫言的《红高粱》、韩少功的《雷祸》、洪峰的《和平年代》、刘恒的《虚证》、叶兆言的《枣树的故事》,到苏童的《1934年的逃亡》、余华的《难逃劫数》和格非的《褐色鸟群》,等等。
这是时空的双重移置,即从当下作家的书写场景移置到奥雷良诺上校的场景(空间),以及从行刑场景移置到“遥远的下午”(时间),由此造成了一种鲜明的他者化效应。他者为主语的书写,制造了作者和叙事对象的疏隔,由此跟此前的以“我”为主语的伤痕文学和朦胧诗划清界限。这是中国文学整体性转型的时刻。马尔克斯的“他者叙事”,帮助中国人跟幼稚抒情的状态决裂,蹒跚学步地走向后现代的前沿。与此同时,他的“拉丁美洲魔幻”,他的传说、神话、童话、巫术、魔法、谜语、幻觉和梦魇的拼贴,都令那些被“现实主义”禁锢的中国作家感到战栗。
然而,中国的前线小说家始终面临“抄袭”的指责。早在八十年代,就已出现过大量批评声音,称先锋小说对马尔克斯和博尔赫斯有过度模仿之嫌。而在2007年初,网友黄守愚与老英子,又在天涯等论坛联合发布题为《余华〈兄弟〉涉嫌剽窃》的帖子,将矛头直指余华的新版小说《兄弟》,认为他的《难逃劫数》与《许三观卖血记》,就是模仿和剽窃了马尔克斯的《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子》和《百年孤独》。甚至《兄弟》的开头,也仍然笼罩着“马尔克斯语法”的浓重阴影——
“我们刘镇的超级巨富……李光头坐在他远近闻名的镀金马桶上,闭上眼睛开始想象自己在太空轨道上的漂泊生涯,四周的冷清深不可测,李光头俯瞰壮丽的地球如何徐徐地展开,不由心酸落泪,这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在地球上已经是举目无亲了”。
我不想在此谈论中国作家模仿运动的得失。但“马尔克斯语法”对中国文学的渗透,却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长期以来,马尔克斯扮演了中国作家的话语导师,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超过了包括博尔赫斯在内的所有外国作家。其中莫言的“高密魔幻小说”,强烈彰显着马尔克斯的风格印记。但只有少数人才愿意承认“马尔克斯语法”与自身书写的亲密关系。对于许多中国作家而言,马尔克斯不仅是无法逾越的障碍,而且是不可告人的秘密。
老人的乌托邦
马尔克斯与秘鲁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长期以来都将对方视为仇敌。1976年的某天,在墨西哥的一家破旧影院里,两个南美汉子曾大打出手。但这坚冰最近似乎有望消融。70岁的略萨已经同意为纪念版的《百年孤独》提供序言,而即将80岁的马尔克斯也欣然接受了这一戏剧性安排。
但这种表面的和解,不能遮蔽两人间的政治分歧。巴尔加斯·略萨是著名的右派,曾经作为右翼派别候选人参选过秘鲁总统,而加西亚·马尔克斯则是坚定的左派分子,并且是古巴独裁者卡斯特罗的支持者和密友。这种长期的政治友谊,对一个自称“百年孤独”的作家构成了尖锐的讽刺。显然,这只是一种有限的孤独,它在古巴境内得到了超越。
只要探查一下马尔克斯的简历我们就会发现,他担任过古巴拉丁通讯社的记者。又在去苏联旅行后写下不少激情洋溢的游记;他还公开发表过大量政治宣言,声援卡斯特罗的“雪茄社会主义”运动。
《百年孤独》出版后,立即被誉为本世纪最伟大的小说之一,赢得多种国际性文学大奖,成为几十种语言的畅销书。瑞典文学院也破天荒地放弃右翼立场,盛赞马尔克斯在政治上坚定地站在穷人和弱者一边,反抗压迫与经济剥削。在诺贝尔受奖词里,马尔克斯坚信,一个类似共产主义的乌托邦就要实现。他宣称,那是“一个新的、真正的理想王国,在那里没有人能决定他人的生活或死亡的方式,爱情将变为现实,幸福将成为可能;在那里,那些注定要忍受百年孤独的民族,将最终也是永远得到再次在世界上生存的机会”。
马尔克斯同志和卡斯特罗同志关系很亲密
但当时就有人断言,这个奖项无异于给本已声名过高的马尔克斯的创作生命下达了“死亡判决书”。1985年,马尔克斯发表了他获奖后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霍乱时期的爱情》,此后的10年间又出版了《迷宫中的将军》、《爱情和其他魔鬼》和《绑架轶事》等,但都反响平淡。在身患淋巴癌之后,他便基本丧失了书写的能力。直至2004年,马尔克斯才推出一部只有114页的小说《回忆我忧伤的妓女》,描述一位九旬老人的心灵愿望,暗示老年人的衰老其实就是心灵的衰老。这似乎就是他最后的自白。在精神大幅度衰退之后,他在试图寻找跟世人道别的方式。
在一个被左翼势力环抱的空间,作者的书写生命,似乎受到了强烈的诅咒。马尔克斯的有限创造力,跟中国作家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他无疑是杰出的作家,但他的文学生命力却只有10多年之久。这是马尔克斯的“阿喀琉斯脚踵”。他呼吸在脆弱的乌托邦里,最后就连自己都无法维系这种梦想。《回忆我忧伤的妓女》向我们揭示一个重大秘密,那就是他的心灵迅速衰老,正是缘于内在信念的瓦解。马尔克斯一直在向世界说谎。他的灵魂背叛了他的言辞,而他则靠可恶的美国“资产阶级”医学,维系着日益衰竭的肉身。但早在1990年代,这位空心的老人就已悄然死去。
雪漠文化网,智慧更清凉!www.xuemo.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