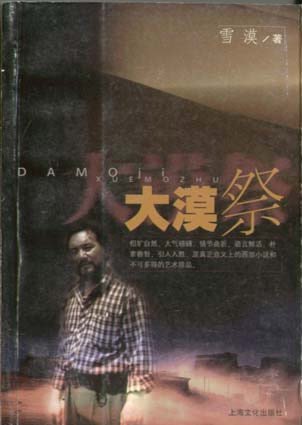
8年前,雪漠在上海出版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大漠祭》,以充满浓厚西部风情和生命气息的语言文字,抒写了一个叫老顺的农民在一年间的日常生活,在一家人生之艰辛,病之痛苦,贫之无奈中表现了原生态的西部农民的生存现实和劳动者的精神现实。更为难得的是,《大漠祭》并没有成为一部展示苦难之作,而是一部表现变革前夜,西部人的生存和精神品性的优秀作品,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因此,它甫一面世即引起了文坛的热烈关注。接着,《大漠祭》的续篇《猎原》和《白虎关》又相继在上海出版,作者宣布:老顺一家的故事告一段落。
比起《大漠祭》的原生态写法,《猎原》明显地吸收了一些现代小说技巧,如结构上将村庄生活与沙漠生活两条线索交替展示,如象征与意像手法的运用,以神麝象征一种古老的草原精神,以羊眼变狼眼,羊吃羊、羊吃牛的意象,表现生态失衡后人们心理的扭曲等等。
在《白虎关》中,被作者推到叙事前台的是3个年轻女性:老顺的大儿媳莹儿、女儿兰兰、二儿媳月儿和二儿子猛子。在《猎原》中,现代化、工业化对于老顺和他的家族来说,还是外边的事情,在《白虎关》中,因金砂矿的发现,却成为发生在自己村庄土地上的现实。一些有权力、有资金的人圈地挖井淘金,发了大财,而无权无钱的如猛子这样的家庭,却加深着贫富悬殊的挫折感和羞耻感,以及仇富情结。近在咫尺的白虎关,因为更多的淘金者的拥入而成为有酒店、洗浴中心、发廊的街市,而如猛子一样的青年只有或卖身金矿当雇工,或沦入偷盗犯罪等等。如果说在《大漠祭》中老顺一家的贫穷是前现代化时大漠农民的生存写真的话,那么《猎原》表现的则是现代化所造成的生存尴尬。

读完《白虎关》,应该承认他实现了自己从一个“小视点”写出了一个大时代的意图。他总是将自己的关注瞄准着社会的缺陷、弊病和弱者的不幸和痛苦。雪漠说:“世上已有了那么多的时尚叙述,也不缺我一个。就让我遵从心灵,流淌出质朴和真诚吧。”
开始动手写《大漠祭》时,雪漠只有25岁,到《白虎关》定稿、出版时,雪漠已经45岁了,中间相隔了整整20年,雪漠将自己生命的黄金岁月,几乎全部给了祖国西部这个农民和他的一家,这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是少见的。如果说在《大漠祭》中他是以质朴、逼真的生活流式的原生态叙述,并以西部沙漠原始奇异的生产生活方式和西部农民独特的品性而产生了巨大的文学征服力的话,那么《猎原》则以孟八爷和猛子侦捕盗猎者线人的行走者身份,见证了草原的凋敝,草原人在严重的生态危机下,生存的绝望和惨烈。在沙漠和草原深处所发生的牧人为了争水争草的以命相拼和盗猎者的铤而走险,以及老顺等村民和国际盗猎集团的斗争等情节,显然有了些文学的合理想象。而在《白虎关》中我们则看到了他对西部农民,特别是女性精神苦难和心灵寄托的热切关注,有了更为自觉的生命和灵魂的悲剧感和超越意识。过去的贫穷和今日的希望走出贫穷,仍然是莹儿、兰兰和月儿悲剧的最终根源,但她们的心灵、精神类型却是完全不同的。在莹儿是对灵官执著的爱和等待,在兰兰是对愚昧落后的家庭暴力的恐惧和拒绝,在月儿则是在城市寻找幸福失败,并得了恶疮之后对美好的家庭爱情生活和保持自己洁净美丽之身的追求和向往。然而,在通过不同途径认识到自己作为一个人和女人的价值与尊严后,她们却难敌亲情的相逼、世俗的偏见,或吞毒自杀,或落入荒诞和虚妄,或难逃病魔的狰狞。在她们身上,雪漠寄托了自己对草原儿女无比的热爱和赞美,对她们的不幸又表现了无限的同情和怜悯。与其他沙漠人行为的鲁莽和语言的粗率相比,一写到她们,他的语言和叙述就充盈了清新美丽的诗意,痛苦和忧伤,沉思和心灵独语,沙漠风光和白天黑夜的西部自然,都如诗如画,让读者体会到一种难得的西部风情美、儿女美、心灵美、情感思绪美。《白虎关》写到莹儿、兰兰、月儿的一些章节,都让人想到曹雪芹对林黛玉、晴雯、尤三姐等人饱含深情的描写。不过雪漠更多的是通过心理分析,感受和抒发着他们对生活的热爱,对自己尊严价值的维护,对现实的质疑与追问,对生与死的思考。
——《甘肃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