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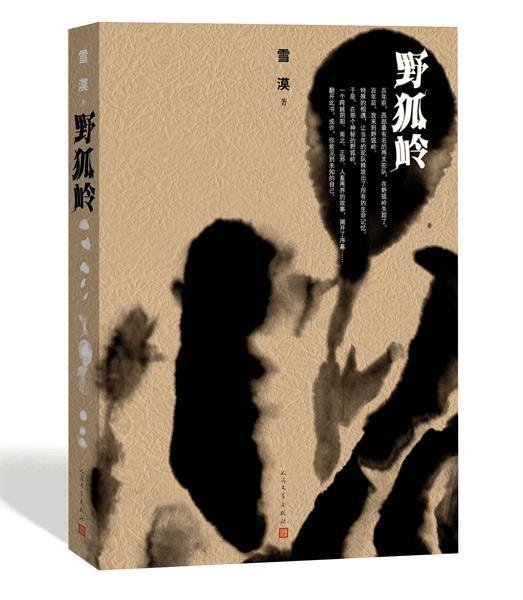
论《野狐岭》中的命运书写
李楠
摘要:雪漠作为一位重要的西部小说作家,从“大漠三部曲”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浓厚的生活气息,在“灵魂三部曲”中我们可以感受到炽热的生命与灵魂的跃动。在《野狐岭》中,雪漠依旧秉持着一颗真诚与热切的心,通过对大漠、对骆驼和骆驼客的深入了解,以招魂的形式向我们展示了独特的西部图景和深刻的灵魂追问。本文将从生命之路的寻觅、反抗与选择、信仰与自我救赎三个部分进行论述,探索“野狐岭”中关于灵魂、关于信仰、关于命运的一幕幕触目惊心的故事。
前言
“两百年前,有两只驼队,在野狐岭失踪了。”[1](P1)两只西部最有名的驼队,心怀改天换日的壮志,漫步于千里驼道,最后却如迷雾般烟消云散。小说起始就被一股神秘的气息笼罩着,一面是最强壮的驼,一面是久经沙场的骆驼客,还有一群神枪手保镖,如此庞大的队伍何以会消失呢?这个疑问久久萦绕在“我”的心中,为了探寻野狐岭发生的神秘故事,解开历史的谜团,也为了见到未知的自己,“我”开启了野狐岭之旅。在“我”的二十七次采访中,全部是由阴魂第一人称讲述,无形间增添了讲述过程的真实感,拉近了叙述者与读者的距离,面对身陷囹圄的木鱼妹、黄煞神与褐狮子激烈的打斗以及祁禄、蔡武对陆富基惨绝人寰的迫害,读者也不禁为当事人担惊受怕。他们表现的是对灵魂的寻觅,在反抗命运中又不断接纳命运,最终实现自我救赎的生命过程。
一、生命之路的寻觅
寻觅作为一种人生姿态,就是生命的存在形式。每个人来到人世间,都会有点什么念想,而这也正是促使他们踏上寻觅之路的症结所在。亦如加入“野狐岭”这段征途的人们,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念想。
(一)现世的追寻
作为采访者的“我”,野狐岭的神秘故事贯穿了他的整个童年幻想,由此便向他的上师苦学时轮历法,终于修成宿命通,从儿时的好奇尚异、拨开历史迷雾到渴求寻找自己的前世、见到未知的自己,满载着这样的疑问,因为担心阳气太盛影响招魂的效果,“我”只带了白、黄两峰骆驼和一只狗便进入了野狐岭。在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下,不仅要抵抗夜晚的极寒天气,还要与沙漠中的猛兽巧妙周旋,眼看着带来的水所剩无几,又找不到新的水源,黄驼的抵触情绪也日益加深,自己深陷进退两难的生存困境中该做何选择呢?仔细阅读就会发现,“我”对此次采访有着非常坚定的信念,面对恶狼的尾随、水源枯竭,仍旧在坚持采访。受访者们带来的水可以说是解了燃眉之急,但是之后从木鱼爸口中得知,阴间之水会导致“我”永远走不出去,可是“我”却说:我可以不喝那水,但是不能不见他们。[1](P381)由此可见,“我”的态度之坚决,目标之明确,作为在沙漠中孤独的存在,经历各种焦虑和苦难,能够看到真实的历史世界成为彼时最大的心愿。
在追寻自我方面,“我”把野狐岭当做一段重要的生命经历,通过连续的采访“我”逐渐了解野狐岭一行人的性格和经历,从未显露过真容的杀手满怀着恨铁不成钢的意气,他那傲慢的语气令“我”反感;而齐飞卿和和沙眉虎的英姿飒爽可以给“我”带来莫名奇妙的兴奋,然而他们的崇尚暴力却是“我”嗤之以鼻的,就在这样矛盾的自我寻找中,“我”也慢慢意识到生命的一切无时无刻不在变化,一切都是无常,所以生命更应该着眼于未来,去把握那些握在手中的力量。当然“我”也发现了那些令我讨厌的特质,例如祁禄和蔡武背叛汉驼队,残忍迫害陆富基的丑恶做派让人鄙夷不已。在最后一会采访结束时中,“我”就表达了这样一种意愿:自己的前世可以是除了豁子、祁禄、蔡武中的任何一个,“我”可以容忍自己是动物,但绝不可以接受在前世里做过小人。[1](P413)由此我们可以了解到,“我”寻找历史的过程,也是一个认知自我的过程,在这段旅程中,不断的灵魂叩问拍打着“我”的心,也让自己更加趋近那个真实的灵魂,正如作者雪漠所说:“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像照亮我的生命那样,也照亮你的灵魂和命运。”[2](P5)
当然,一路兼程的“我”除了收获了圆满的采访,也领略了大漠真情,一是同行的狗为了帮“我”找到起火的褡裢而冻死在沙漠,二是木鱼爸的深切关怀也为大漠孤行的“我”带来阵阵暖意。
(二)灵魂的求索
野狐岭中的魂灵们是孤独的,太多的尘世牵绊让他们寄居在野狐岭这个精神家园,“我”的到来,将他们尘封的记忆再次唤醒,追忆起那随风而逝的往日时光,好像被重新赋予了生命,因此他们欢迎“我”这么一个倾听者,甚至热情地为“我”拿来阴间之水,想留下“我”,希望“我”能留下来陪他们度过那漫长的夜晚。
进入野狐岭的每个人甚至动物都有属于自己的目标,贯穿其中的主干便是两只驼队运送金银茶叶到遥远的罗刹换取军火,完成驼队的总任务。作者采用直观的笔触,刻画出了在生命的追寻道路上各种各样的面目形态,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的思想的睿智与人道的关怀。马在波作为驼队中的重要人物,从他最开始的讲述中,便可以得知他是一个热爱禅修诵经的富家少爷,他踏上野狐岭之行并不是去罗刹换回武器,而是因为他预感到驼队这次的出行会遇到难以躲避的灾祸,那凉州传说中的木鱼令可以化解所有的冤结,改变所有的结局,根据凉州歌谣“胡家磨坊下取钥匙”所提示的内容,马在波就是要寻找胡家磨坊,找到木鱼令,从而改变整个驼队的命运。很显然马在波在这里扮演的是一个救世者的身份,而他为什么会知道此次行程必遭凶险呢?这就不得不说到他的宗教身份,从开始的诵经打坐到后来的整理木鱼歌,可以看出他是一位不被功利所沾染,不为凡尘所牵绊,是一位真正参透生死,领悟生命真谛的智者形象。
他不但注重自我的修行,也乐于渡人摆脱苦难,驼把式张大嘴就是受到马在波的点化,被那诵经的优美旋律所感染,发现自己并不是真正的苦命人,从此便从悲观厌世的张无乐变成了逍遥自在的张要乐。也正是因为马在波执著的寻找,领会了那木鱼令的真正意义,守住了灵魂之路的寻觅,最后终于走上了自我拯救的生存之路。
二、抗争与选择
人对于自己的生存环境,一般会做出两种选择:反抗和接纳,你是和周围的一切作斗争,还是被动接受命运的安排碌碌无为,做出什么样的选择,也就决定了你拥有怎样的人生。野狐岭的人们做出了自己的选择,而此刻回望那段遥远的岁月,他们似乎在抱怨与抗争中找到了两者的平衡点。
(一)在困境中挣扎
作者在同一个环境下为我们展示了人生百态,面对命运的安排,一切似乎早已注定,小说中借马在波之口这样说道:“野狐岭中的人们就像是那磨盘上扭腰的蚂蚁,不论你扭得多用力,也改变不了磨盘的转动。”[1](P384)
小说伊始,便是一个“革命”的故事,哥老会密谋策划继而威胁驴二爷和马在波,最终踏上了野狐岭之行,哥老会成员壮志凌云,却不知从起场那一刻起,他们已经走向了命运为他们铺就的末日之路。飞卿与众多哥老会成员不满清廷的统治,谋划鸡毛令事件,这是他的挣扎,可是那一哄而上又一哄而散的意义在哪里呢?凉州贤孝《鞭杆记》给出了答案:干着好了好处由大家,干出害神了我们就担承下。[1](P206)在刘胡子马队的的激烈打压下,兵败如山倒,飞卿、陆富基等人只能趁机出逃,而“这次的暴动也只是无数次看似笑话的暴动中的一次”。[1](P206)由此可见作者对革命的反思颇有鲁迅的遗风,鲁迅曾这样论述过中国革命者与启蒙者的关系:“《药》描写群众的愚昧和革命者的悲哀,更直捷地说,革命者为愚昧的群众牺牲了,愚昧的群众并不知道这牺牲为的是谁,却还要因了愚昧的见解,以为这牺牲可以享用。”[5](P9)这里鲁迅先生便对革命党人严重脱离社会大众做出了深刻的反思。小说中还借木鱼妹之口道出了所谓的历史真相:“历史是什么,历史是胜利者写的一种属于他们的说法,真实情况怎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说法。” [1] (P193)那么飞卿等人流血甚至丢掉性命的革命斗争到底意义何在呢?或许那一切只是心的倒影,或许我们追求的自由并无什么显而易见的意义可言,正像鲁迅所认为的那样:“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有污秽和血。对于革命抱着浪漫蒂克的幻想的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进行,便容易失望。”[ 8](P1006)然而飞卿性格里本就有悲观的因子在,这也便是导致他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因此,不论革命前景怎样,不自行放弃,不失去那战斗的意志和拼搏的能力,便是那“不克厥敌,战则不止”的生动写照。
(二)在矛盾中选择
雪漠在《一个人的的西部》中说,“一个人的价值就是他的行为”,[2](P306)所以每个人都是自己行为的承担者。米兰•昆德拉也说过:“在这一重复性的世界中,人人相似;通过行动,人与他人区分开来,成为个体。”[3](P30)每个人在一生中要做出无数的选择,而当我们身处岔路口的时候,因为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也便有了不同的命运之旅。
在第十一会中作者借杀手之口,介绍了马在波和齐飞卿两人因选择不同而各行其是的故事,两位都是有着独立、淡定、从容等优秀特质的人,且两个人都有修行的习惯,并在修行的过程中看破了红尘。可以说他们二人是从同一起点出发,但最终却有着完全不一样的人生。马在波看破世俗之后,似乎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就一心想着出家,不想去做哪些没有意义的事情,在被驴二爷拒绝后,也没有浑浑噩噩,而是依旧想着做点自己该做的事,他将寻找视为自己的宿命,所以在进入野狐岭之后,便一直寻找那能化解一切冤仇的木鱼令,试图改变厄运。那为什么马在波能够如此与众不同呢?从他喜打坐诵经可以看出马在波深受佛教影响,而佛教就是提倡造命,引渡众生脱离苦海的,所以那难以言说的末日情绪在他眼里,不是杀手眼中的磨盘,也不是大烟客眼中的木鱼,而是一只船,一只救度人心的船,而所有爱听经的人都将得到救度。而飞卿则截然相反,在看破红尘之后,还想做事,想去改变那命定的东西。同样作为哥老会成员之一的大烟客对于革命也有着自己的的看法,他这么说道:“把造反呀叛乱呀换成了‘革命’,但我知道,无论啥都一样,都是想从别人那里抢财富,都是相当老爷,但你们当上老爷后,只会比以前的老爷更坏。”[1](P329)在他看来,人活一辈子总要做些什么,但也只是做而已,是职业道德的驱使。飞卿的选择也可以说是性格使然,就像在马在波和豁子看来,飞卿太出色太优秀太富有,但又不免太偏激,所以他的死是必然的一种结局。
木鱼妹作为驼队中唯一的女性形象,可谓是一个矛盾着的复杂体,命运之棒对她似乎太过于残忍,作为一个柔弱的南方姑娘,却承受了太多难言的苦难,一面为了复仇历经千辛万苦从岭南赶到凉州,阴差阳错地卷入哥老会的暴动,另一面又不可自拔地爱上了仇人驴二爷的儿子,一直在仇恨和爱情之间痛苦地摇摆,但幸运的是经过十多年木鱼歌的熏染,她没有被仇恨遮蔽善良的心智,与马在波共同战胜疯驼,最终在爱人的支撑下走出野狐岭,那爱的力量不仅消解了仇恨,而且走向了灵魂的救赎与超越。
三、信仰与命运
在《野狐岭》中我们会发现,由于不同的心灵和文化,会导致不同的命运。正像雪漠在《雪漠造命歌》中写道:“福祸原无门,世人唯自招。心变命亦变,吉凶由心造。心善无厄运,福祸自了了。恶贯满盈者,菩萨也难保。”[2](P172)
(一)孤独的信仰之路
为什么现代人普遍没有属于自己的信仰?雪漠在一个访谈中这样回答:“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死亡,明天也不一定像你想象的那样,肯定会来临。”对于自己的信仰和文化,雪漠曾这样说道:“真正的信仰是无条件的,它仅仅是对某种精神的敬畏和向往,信仰甚至不是谋求福报的手段,信仰本身就是目的。”[4](P497)
真正坚定的信仰者,即使陷入了生存的困境,也还会有一种希望在,因为他们相信真理,即使道路充满艰难险阻,但还是愿意一直走下去。大烟客就是一位真正的信仰者,在末日的沙尘暴吹起的时候,即使是走过很多次的驼道,可那狂风和移动的沙墙也是他第一次遇到,在劳累与绝望一起袭来时,他没有怀疑那古老的歌谣,没有追问到了胡家磨坊又能怎样,他只是无条件地坚信着:“老先人既然说胡家磨坊有钥匙,那就定然有钥匙。”[1](P377)即使到最后大烟客也没有进入到胡家磨坊,但是在那坚持不懈的寻找中,才走出了末日的沙暴。但是在信仰之路上并非都是一帆风顺的,那些没有保持足够的清醒和向往的人,便被那恐怖的假象所欺骗,就像那在流动的沙墙中倒下的驼户们,他们把持不住自己的心,放弃了努力,只能被流沙掩埋,永远的迷失在野狐岭中。的确,“人一旦迷醉于自身的软弱,便会一味软弱下去,会在众人的目光中倒在街头,倒在比地面更低的地方”,[3](P40)这就是一种叫作“眩晕”的东西,它会给那些不够坚定地灵魂施压,让他们沉醉于自身的软弱之中。所以有信仰很重要,而懂得在孤独中默默地坚守则更为珍贵。
(二)无奈的自我救赎
“人从巧计常安排,天自从容做主张。” [1](P329)野狐岭中的人们一路辛苦跋涉,他们头顶的上方的命运磨盘从未停止转动,难以言说的末日情绪也从未消散,叩问命运之后,一切仍旧是茫然。小说中巧借人物之口,发出了一次又一次无奈而又茫然的质问。驼户生来就有着穿重鞋的宿命;杀手打破自己种种美好的设想后也只能感叹,命运就是这样,人生就是这样;堂堂“左相大爷”胡旮旯也不禁感叹人生无常;作为“沙漠之舟”的骆驼也只能驼了东西行走,走就是它的宿命;汉驼队长齐飞卿后来加入同盟会也没能摆脱砍头的结局;即使是可以化解仇杀的木鱼令也没能终止汉驼和蒙驼之间的纠纷。难道面对苦难的命运和变幻莫测的人生,我们只能坐以待毙吗?马在波给出的回答是:“一个人的心念会改变一切,你有哪种情绪,便会招来哪种结果,许多人就是用一种良好的心态改变了命运。” [1](P108)又或者是:“人活的意思,就是活那个过程。亦如很多时候,道理解决不了问题。” [1](P399)史铁生也给出了他的答案:“生命的意义就在于你能创造这过程的美好与精彩,生命的价值就在于你能镇静而又激动地欣赏这过程的美丽与悲壮。但是,除非你看到目的的虚无你才能进入这审美的境地,除非你看到目的的绝望你才能找到这审美的救助。”[6](P21)也正是因为这种茫然之中不懈的寻找和坚持,才使那种看似无奈的自我救赎产生出一种对待苦难命运的乐观心态,命运也终于向他们递出了上帝之手。
我们也许永远都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会先来,而生命中那些无法改变的局面,是每个人都避免不了的缺憾,如果一切已成定局,那么我们能做的便是坦然地接受,这样或许可以消解一些悲伤和无奈,让自己的灵魂得到救赎。
四、结语
小说结尾处马在波和木鱼妹在走出野狐岭之后,又重新返回潜心修行,躲过了世俗的风风雨雨,他们找到了超越命运的自我救赎之路,实现了灵魂的升华。有时候我们会想到,当你我身处野狐岭这场考验中时,我们是否有足够的智慧和力量应对这场挑战,我们会作何选择?又会有怎样的人生轨迹呢?希望我们都能做勇敢的追梦者,经过时光的历练从而拥有一个鲜活的灵魂。
雪漠在创作自述中谈到:“灵魂三部曲”是写给有灵魂追求的人的,他们定格在一个独特的精神世界,同时其又是非常广博的,因为每个人都有灵魂的痛楚,每个人都有灵魂的追问,每个人都有属于他们自己的寻觅之旅。”[2](P358)也正以为如此,雪漠的作品一直被誉为是“灵魂深处的真诚流淌”,滚烫的语言文字炙烤着一个又一个迷失的心灵,并希望照亮他们的灵魂和命运,完成各自的人生。对于西部文化的养育和熏陶,雪漠也谈到:“西部的生活虽然贫瘠,但给予我的,也够我这辈子用了。”[2](P127)由此可见,雪漠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真正担负起了“开发大西北的精神世界和文化堆积,传达大国的雄风壮美,为大西北造影立传”的重任。[7](P6-7)
参考文献:
[1]雪漠:《野狐岭》,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
[2]雪漠:《一个人的西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
[3]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
[4]雪漠:《白虎关》,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
[5]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
[6]史铁生:《灵魂的事》,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
[7]萧云儒:《中国西部文学论》,青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8]鲁迅:《鲁迅小说杂文散文全集》(中),广西民族出版社,1995年。
[9]钟怡雯:《论“西部文学”命名的文学史意义》,《当代文坛》,2019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