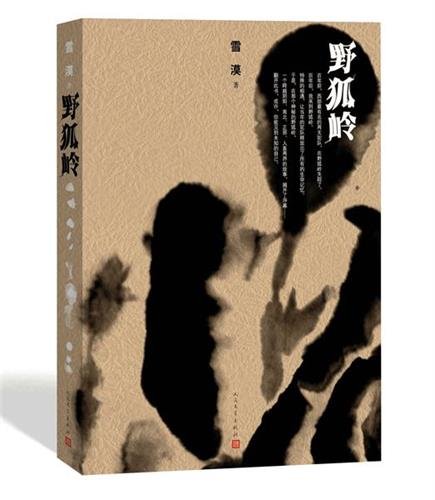
《野狐岭》的叙事艺术
文\彭金山
读了雪漠的《野狐岭》,感到他的创作又有了新的变化。《野狐岭》给我最强烈的印象,是小说的叙事艺术。这部小说同雪漠以往的小说不同,整个故事是在通灵的环境里,由故事采集人招亡灵出来,闻声不见形地听他们讲述当年事。也可以说《野狐岭》是一部历史小说,然而它却打破了一般历史小说的叙事规则,不是由作家在一个统一的视点平台(统一的叙述人称)上,遵照一定的时间逻辑来展开故事,通过由走进书中的不同角色、亦即不同的当事人自叙,展开一个辽阔的叙事空间。故事断断续续,在叙事轴上悬念丛生,或远或近,或明或暗,又都指向一个历史事件——发生在清朝末年的凉州暴动。这个并非《野狐岭》直接切入的故事,也是读者的诘问点、关注点;就像一块巨大的磁铁,读者犹如铁屑,一进人“野狐岭”的故事,就感到了强大的吸引力、粘附力。而“我”则是故事叙事时空的总统领,事是百年前的事,人是亡故之人,采用招灵术招引到荒漠野岭,让他们自己道出各人的事儿,从而增强了真实感和可信度。《野狐岭》的中心事件是蒙汉两只驼队在野狐岭的遭遇,在一片神秘氛围中,连动物也有了灵魂,以另一视角观照、描述那一历史事件,加入了叙事的众声喧哗。野狐岭的故事打破了阴阳界限,古今藩篱,驼人之别,幻真之分。这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力求使那一段历史立体真实地显现出来。《野狐岭》以这样一支凉州童谣作为全书“引子”的开端:“野狐岭下木鱼谷,金银九缸八涝池,胡家磨坊下找钥匙。”显然,雪漠首先找到了《野狐岭》叙事的“钥匙”。对于那个颇具神秘色彩的历史事件,作者找到了最佳叙事的“接口”,于是,往事如水,淙淙流出,徐徐道来,虽多头交叉,却纷繁而有序。这就是《野狐岭》的叙事艺术,在结构上别创新途,独树一格。此则《生死疲劳》有之,但是不像《野狐岭》这样迷乱人眼。
《野狐岭》一开始就是众声喧哗,云遮雾罩,神龙见首不见尾,及半部小说掀过,云雾渐淡,开始显山露水,始见主人公面目,即木鱼妹、马在波。是作品的主人公,也是整个叙事结构的枢纽,枝枝蔓蔓的情节或直接或间接均由此而生,围绕主人公之间的爱恨情仇,故事一波三折,走向那一个出人意料的结局。在大爱大善的木鱼歌的感召下,杀手变成了情人,世代冤仇在人生的至境中化解——作者的历史观、伦理观,乃至生命哲学层面的存在观,至此揭底。
当事人的自述,旁观者的插入,叙事人的讲述,作者的潜在干预,构成《野狐岭》的复调言说。如此别致的结构艺术,是与作者的人生经历、生命体验、文化构成和精神境界密切相关的,出于自然,发自本心。雪漠久研佛理,明了死生,对那个几代凉州人口口相传的故事,自有其比较透彻的觉解。借古事以启迪今人,这也许是《野狐岭》的创作初衷。
从头贯穿到尾的“木鱼令”这一线索,构成故事最大的悬念。那么,什么才是“木鱼令”的真面目?雪漠说:“我总是在别人的病里,疼痛我自己。”(雪漠《杂说<野狐岭>》)和与爱——这也许就是“木鱼令”!野狐岭,人类的夺命谷。幸亏冥冥之中还有一个“胡家磨坊”在。那把童谣中的钥匙,其实就在人的心里。
至《野狐岭》面世,雪漠的小说创作经过现实感很强的大漠系列和几近于神话的灵魂叩问系列两个向度的探索,终于结于一处。对于作者来说,是一种回归,一种螺旋上升后的回归。这种将历史、现实和灵魂叩问合为一炉的熔炼与重铸,体现了作家自我突破的自觉意识。这便是《野狐岭》的意义。《野狐岭》是雪漠创作道路上的又一个标志性成果,一次对自身的超越。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野狐岭》就是一部无可挑剔之作,也不意味着它的价值已经超过了《大漠祭》。《野狐岭》的写作别致在叙事,但疏漏也在叙事,特别是关于岭南生活的那部分叙事,以及木鱼妹的两次跟随驼队之行的情节设计中,都还颇有一些可商榷的地方。
然而,《野狐岭》却标识了作者努力的一种方向,一种开阔,一种远行的可能性。
《甘肃日报》2015年4月30日
http://epaper.gansudaily.com.cn/gsrb/html/2015-04/30/content_25078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