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可我把“自强不息”这四个字不知读了多少遍,并珍藏在心里,变成了箴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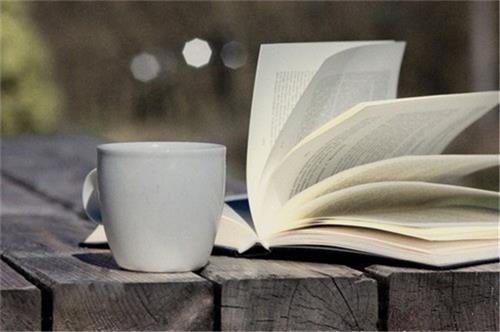
童庆炳谈治学之道:积累·体验·对话
编者按: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资深教授、著名文艺理论家童庆炳先生,因病于2015年6月14日去世,享年79岁。童先生生前是《文史知识》的作者和读者,历年来为《文史知识》撰稿30余篇。今重读先生旧文,以寄哀思!
积累·体验·对话当时的文章对童先生的介绍是这样的:
童庆炳,福建连城人,1936年生。1958年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现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文艺学博士生导师,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理事、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理论著作主要有《文学活动的美学阐释》、《艺术创作与审美心理》、《中国古代心理诗学与美学》、《文体与文体创造》、《艺术与人类心理》(主编)、《现代心理美学》(主编)、《中国古代诗学的心理透视》(合作),文学创作已出版的有长篇小说《生活之帆》和《淡紫色的霞光》。
编者要我谈点治学经验,心里惴惴不安。因为自己的学问连自己都不满意,怎么敢介绍治学经验呢!只是自己是个教师,平时免不了给学生谈到自己学习、教书和研究中的一些甘苦,学生们也还听得进去,这次就把其中的几个要点写出来,供有志于治学的青年作参考。
积累
我家很穷,我在上中等师范时,最高的志愿是当一名小学教师,每月给家里寄些钱,让家里每天都有米下锅。但我很幸运,却在师范毕业时被允许报考大学,并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大学毕业后,我留校任教,进的是文艺理论教研室。如果我一直平稳地呆在室里,那我想是搞不出名堂来的,因为幼稚的我一定会被那些文学理论的名词概念弄得晕头转向。我可能是被人认为业务没有发展前途,而被派到学校的社会科学处当一名职员。白天我坐班,晚上我开始研读《红楼梦》,在隔壁同事们的搓麻将声中,我天天晚上与贾宝玉、林黛玉们在一起,在经过了二年的努力之后,我完成了我的第一篇论文《高鹗续红楼梦的功过》,并且又碰上了曹雪芹二百周年祭,我的论文经过了五位教授的审查后,在学报发表出来。可能由于有这篇论文,中文系重新接纳了我。现在回想起来,这就是我治学的起点了,或者说开始了治学的“积累”的过程。
“厚积薄发”是治学名言。但是,我的青年时期是一个政治运动连绵不断的时期,并不是你想读书就能安下心来读书的。然而,“幸运”之星第二次照耀我。当我的同事纷纷下乡搞“四清”的时候,我被派到越南国立河内师范大学外语系任教。由于那次派去的五人中没有一个是搞古典的,而河内师大又必须要一位教中国古典文学的教师。这困难的任务终于落到我的头上。河内师大中文专业学生的水平相当好,他们是三、四年级的学生,其中又有不少华侨子弟,因此对中国老师的要求也比较高。我同时教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和写作三门课,此外还要给系里的青年教师讲授古汉语课程,有时一周要上24节课。困难的还在于所有的教材也要自己编写。这样我就开始了一个长达二年的“边干边学”的教学和研究生活。这段生活是难忘的。我发现我大学期间学习质量是很低的。一切都要从头开始。在那里,我还发现一个教师和一个专门的研究者的区别。某些研究者对于材料的使用,只需有整体的理解就够了,有时不必去抠每一个字的读音和意义。但对教师来说,对你要讲的东西,只有整体的大致的理解是不够的,因为往往是你自己不甚明了的地方,也正是学生不明了的地方。这样,在备课时,你就必须把每一个字的音和义都弄得十分清楚,然后才能走上讲台。在越南的两年,我编写了一部20万字的《简明中国文学发展史》、50万字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注》,并由学校油印出来。我记得,我那时的认真是少有的。例如我不满意郭沫若的《离骚》翻译,就自己逐字逐句重译,直到满意为止。这两年的教学生活,对我来说是又一次“积累”。我的古典文学的基础主要是在这段时间打下的。
从越南回国后不久,“文革”开始,当大家忙于打“派战”之际,“幸运”之星第三次照耀我这个“逍遥派”。我又被派到地拉那大学历史语言系任教。我给学生讲现代汉语、屈原、李白、杜甫、鲁迅和“样板戏”。工作并不重,有的是时间,可就是没有书可读。地拉那,连汽车声都难得听到的、寂静的、气候宜人的地拉那,真是读书的好地方。哪儿去找书呢?当时中国驻阿使馆的文化参赞似乎是从我的脸上看出了我的苦恼。他告诉我,大使馆内有一个中文图书馆,只是你要“借”书得有勇气。原来图书馆被使馆内的“红卫兵”贴了封条,若真想读书可以想办法去“偷”。我那时真是太寂寞了。我利用使馆人员午休时间,一次又一次“潜”入使馆去“偷”书。后来发现地拉那图书馆也有不少中国书,因没人识中文,堆在那里,没有整理上架。我便讨了帮他们整理书的工作,条件是准许我随意借书。在地拉那工作的三年,我不但系统地读了《史记》等古代典籍,而且还读了中外的诗歌、小说,特别是《鲁迅全集》我读了两遍,积累颇多,收获非浅。
我的专业是文艺学,可我教的课,读的书,却古今中外无所不包。从古到今,从语言到文学,从史到论,我都摸了摸,这使我积累的知识比较广,为后来的学术研究作了较好的准备。学术研究工作要懂得限制自己,不能什么都抓,但为学术研究所涉猎的面则愈宽愈好。知识的积累愈多,内存就愈深厚,视野就愈开阔,研究中知识就可能实现自由组合,最终也就能有所发现。就像植树挖坑,你想挖得深,开挖的面就得宽。治学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在长期的学术生涯中,难免不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但只要有一种爱情般的苦恋,宗教般的虔诚,困难是可以克服的。
体验
书本知识往往是死的,怎样把死的知识变成活的呢?这就要从生活中去体验,把书本与生活接通,,死的也就变成活的了。特别是搞文学的人,若不能从生活中去体验,文学的那种具体的、感性的、微妙的、难于言传的生命力也就很难把握住。我经常对学生说:“对于研究文学的人来说,经历是一种重要的财富,经历中的生活体验更是一种重要财富。因为过去时代的作品,是作家对当时的生活体验的结晶,我们必须有相同、相通、相似的生活体验,才能深刻地理解古人和前辈作家的作品。在深刻理解作品的基础上,进一步的研究才有可能。”杜甫在《水槛遣心》中有“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的句子,这十个字无一字虚设,体物之微之准,十分难得。我出身有山有水的农村,是乡下人,对鱼和燕子的活动仔细地观察过,所以对杜甫的这两句诗别有会心。大雨,鱼儿感觉有东西可能危害自己,所以伏而不出,细雨,鱼儿觉得似有食物从天而降,所以纷纷浮出水面觅食,那小嘴一张一合,景观煞是好看;大风,燕子的小翅膀不胜风力,是无心在空中戏耍的,只有在微风中,燕子才会展开翅膀,在风中倾斜着抖动。杜甫的《船下夔州郭宿雨湿不得上岸别王十二判官》中有“风起春灯乱,江鸣夜雨悬”的句子,表面看起来似不通,灯怎么会乱,雨又如何能悬着呢,实际上是把诗人因夜雨不能上岸会久别的朋友的心情,写得淋漓尽致。“灯乱”、“雨悬”都是从一个焦急的人的眼中看出。我自己因也有相似的体验,所以也就能体会杜甫的描写。作家创作要调动自己的全部体验,研究作家作品也要调动自己的全部体验,当自己的体验与作品中所表现的体验息息相通时,我们就走进了作品所描写的境界,我们对作品的理解就不会停留在字面上,刻骨铭心之感就油然而生。
我在研究工作中重视体验,与我的好几位老师的教导有关。黄药眠先生、钟敬文先生、穆木天先生、启功先生等,都既是学者,又是作家、艺术家。众所周知,黄先生除了搞美学、文艺学研究外,他还写诗歌、散文、小说和报告文学。钟先生是著名的民间文学家、民俗家,同时写散文和诗歌,他的散文在“五四”新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启先生是著名的古典文学研究家、古汉语专家和文物鉴定家,同时又是著名的画家、书法艺术家,他的诗也写得很有情趣。作为学者,他们十分重视理性、抽象、概括,作为作家、艺术家,他们又十分重视感性、具象、体验。对于他们来说,这两者不但不会互相妨碍,而是相得益彰。有一次,黄先生对我说:“你为什么不搞点创作?搞文艺学的人成天跟名词概念打交道,弄得不好,脑子就僵化了。应该学会观察和体验生活,搞点创作,创作成败无所谓,重要的是通过创作,你有了实际的体会,那时你就会知道哪些概念是有用的,一定要跟学生讲清楚,哪些概念是虚假的,应把它从教学和研究中清除出去。”有了这些老师的榜样,在黄先生的督促下,从1979年起,我开始写长篇小说,并于1980年出版了《生活之帆》,1987年出版了《淡紫色的霞光》。虽然作品不太成功,但反响比我的任何理论文章都大。后来又陆续发表了一些散文。果然,自搞了些创作之后,才有下了文学这个海的感觉。对前人的作品,对中外的理论,都能从创作这个新的角度去理解,对问题也就有新的发现。
我深深地体会到,治学之路是与自己的生活密切相关的。从概念到概念,从材料到材料,从书本到书本,拼拼凑凑,是不可能作出真学问来的。因此,治学就要全身心地投入,当书本知识跟生活体验打通之后,学问才能跃入一个新的境界。

1955-1958年童庆炳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图为童庆炳大一期间在数学楼前留影
对话
我的另一点看法是,认为研究就是对话。如果你研究的对象是古典,那么你就是跟古典对话。如果你的研究对象是外国,那么你就是跟外国对话。
在长期的生活实践和知识积累中,每一个人的头脑都不是一张白纸,而形成了一定的预成图式。这个预成图式具有活力,它必然要以积极的态度去整合新的对象,这就构成了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的对话关系。平日的积累与体验最终都要内化为预成图式而在研究中起作用,在对话中发挥影响。
我把研究看成是对话,牵涉到一个历史观的问题。旧的历史观把社会历史的发展看成是静态的,通过客观的研究是可以复原的。在这种历史观的制约下,把作者的生平、作品的历史背景看成是独立的客观的可以复原的对象是合理的,因此选择作者或作品的社会历史背景进行单维的研究就比较可行。马克思的历史观则是发展的历史观,他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但他又说:“当人们好像只是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马克思这段著名的话,表达了双重的意见,一方面,历史是既定的存在,永远不会过去,先辈的传统永远纠缠着活人,因此,任何一个新创造的新事物都要放到历史天平上加以衡量;另一方面,今人又不会恭顺历史,他们以自己长期形成的预成图式去理解、改造历史,甚至“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因此,今人所理解的历史,已不是历史的原貌,而只是人们心中眼中的历史。如果把马克思的观点运用于文学研究,那么一方面要把作家作品放置到特定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另一方面则要重视研究主体对作品的独到的解说。当代西方的新历史主义学派有一句重要的话:“文本是历史的,历史是文本的。”他们的观点继承马克思的历史观又有所发挥。所谓“文本是历史的”,是讲任何文本都是历史的产物,具有历史的品格,因此,任何文本都必须放到原有的历史中去考量,才能揭示文本的本质;所谓“历史是文本的”,是说任何历史(包括历史活动、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作品等)对我们今人来说,都是不确定的文本,我们总是以今天的观念去理解历史“文本”,改造和构设历史文本,不断地构设出新的历史来,而不可能把历史文本复原。之所以会如此,关键的原因是作为认识主体的人和人所运用的语言工具。人是具体历史的产物,他的一切特征都是特定历史时刻的社会因素所刻下的印痕,人永远不可能超越历史;语言也是如此。按结构主义的意见,语言是所指和能指的结合,语言的单一指称性就极不可靠。这样,当具有历史性的人运用指向性不甚明确的语言去阅读历史文本时,会发生什么情况呢?肯定地说,他眼前所展现的历史,决不是历史的本真状况,只能是他自己按其观念所构设的历史而已。我是主张用这一新视角去分析和探究历史文本的,那么这种分析和探究就变成一种对话,一种交流,一方面是作品作为历史的文本,发出了信息,另一方面,研究者也有自己固有的观点,也向文本投射了信息,这就形成了文本与研究者的双向对话,过去和现在的双向对话。在这种情况下,文本的原本的意义、永恒的真理已不可寻,能够办到的主要是作为主体的研究者运用语言对作品意义的重新解说和构设。这样,随着研究者的现时的观点不同,对文本的意义的构设也就不一样。由于不同时代的研究者的观念不同,对同一部文本的意义的构设不同,这部文本的意义就不断增加,成为一个意义链。我的一系列著作,如《中国古代心理诗学与美学》、《中国古代诗学的心理透视》等,都是对话,今与古的对话,中与外的对话。如果能从这种对话中生发出新的意义来的话,这在我看来就是学术研究了。
我想再说一遍的是,治学总要有前辈的激励和指导。启功老师曾给我写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题辞,在他可能只是对后辈的一般的激励话,可我把“自强不息”这四个字不知读了多少遍,并珍藏在心里,变成了箴言。黄药眠老师总告诫我们:不能总是重复孔子怎么说,庄子怎么说,重要的是你自己怎么说,你对这个问题有何新的意见。黄先生的治学要“出新”的思想,在我写作的时候,也常常像警铃般在耳边响起。在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九十一岁高龄的钟敬文先生在我陷入困境时对我的教育。大概就是几年前的一天,我去看钟老,钟老见我情绪不佳,就语重心长对我说:为人治学要讲六个字:勤奋,正直,淡泊。勤奋,只有勤奋才能把学问积累起来;正直,就是对大是大非要清楚,不说违心之论;淡泊,就是不要去考虑名利得失。这六个字,紧密联系,缺一不可。当我走出他家的时候,我的情绪好多了。我想到,自己已是五十多岁的人,应该是“知天命”了,可还是要前辈老师的教导。给过我帮助的不但有校内的老师,还有校外的老师,如王元化教授、徐中玉教授、蒋孔阳教授都给过我教诲与激励。
(本文节选自《文史知识》1994年第2期)
雪漠文化网,智慧更清凉!www.xuemo.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