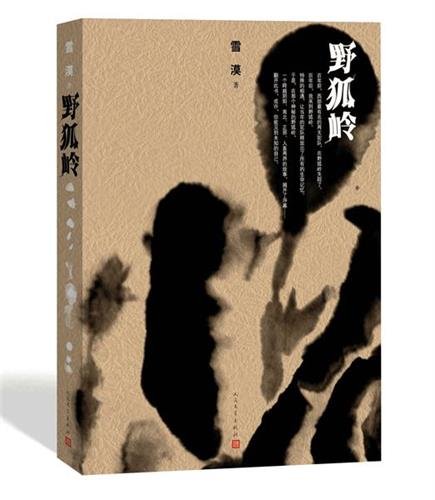
张柠:俗世生活与神圣生活的嫁接
——2014年10月19日雪漠《野狐岭》中国作家协会研讨发言
因为是南方人,我对大漠文化不是太了解,读着关于大漠的文字,感受不是太深。但是好奇是有的,比如对骆驼那些非常细致的描写,包括撒尿、咀嚼,包括求配偶的方式,对我来说都是陌生的经验。从阅读的新鲜感受来说,是可取的,但是从文学感受、审美感受的角度来说,我认为大漠文化对我来说是陌生的。但是,这部小说读下来,我感觉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文本,不是说很简单地直接就能够把它抓住。究其原因,肯定是作者在叙事方式上进行了很多的探索,有点像 80 年代中后期、90 年代初期的小说,对我们的阅读构成一个巨大的挑战。
《野狐岭》读下来还是有很多值得讨论的地方,其中感受比较深的就是木鱼歌、木鱼妹这条线索。木鱼歌这样一种民间说唱的形式,是岭南特有的广东南音这种形式,但是这个南音跟潮汕的咸水歌不一样。潮汕的咸水歌是从疍民船上直接生发出来的,而这个木鱼歌的源头在北方,是从北方传到岭南去的,其中宝卷就是佛教故事说唱传到岭南,然后在此基础上岭南人再创作形成南音、木鱼歌这种形式。小说里提到的《花笺记》也是木鱼歌非常重要的一个唱本。我觉得雪漠做了很多案头工作,包括歌德对《花笺记》的赞赏。我们国家也对歌德怎么样去接受《花笺记》做过研究。歌德还通过阅读《花笺记》写了一组诗,这组诗由冯至先生翻译成中文,影响比较大,被命名为《第八才子书》。岭南木鱼歌或南音,又跟传过去的西部的宝卷有关,所以它是世俗生活和神圣生活的一个直接嫁接。南音本来就是介于念经和歌唱之间的一种说唱形式,它敲着木鱼,所以就称为木鱼歌。
雪漠这样一个创作动机,实质上他是把神圣生活的念经和俗世生活的歌唱嫁接在一起,同时也有把北方文化和南方文化嫁接在一起的一个冲动。我想到陆九渊的一句话: “东海西海,心同理同。”还有钱钟书说的: “南学北学,道术未裂。”我把它改成了“汉学蒙学,道术未裂”。所以,这个嫁接过程实质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人的性情、人情。这种人的性和情是在木鱼妹、马在波和大嘴哥故事中凸显出来的。因此,不管是北方文化,还是南方文化; 无论是汉族文化,还是蒙族文化; 无论是驼斗,还是土客械斗,里面体现出的最核心的,就是人的情感,就是人性的问题。这一点是我非常感兴趣的。我们总觉得北方文化是一种形态,南方文化又是另外一种形态,好像它们之间差别非常大,但实质上在这个作品里边雪漠打通了。无论是俗的生活,还是圣的生活; 无论是南方生活,还是北方生活,最终在人情、在欲望层面打通了。从整体构思上来说,这个想法是非常好的。
在阅读过程中,我抓住了一点,无论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都应该触动你的东西,那就是人性和人情,就是木鱼妹和马在波等人之间的关系,这条线索是非常清楚的。说实在,阅读时,我一旦看到大篇幅谈骆驼的时候,大篇幅谈情节设计,如暗杀、暴动的时候,我读得非常快,而一旦出现木鱼妹、马在波和大嘴哥之间的故事的时候,我会非常细致地读,我会用我的心去感受它,这是我一个直观的感觉。
在整个故事中,欲望展开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仇恨消失的过程。这里边还提到很多马在波修行的方式,它不是简单的爱情故事或情欲故事,他是以密宗“双修”的方式进行的一种修炼。“双修”实质上也是一个打通的过程,就是世俗生活和神圣生活之间的打通。“双修”表面看来身体是那个东西,但灵魂不是那个东西,所以,灵魂性是雪漠小说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所有世俗生活里边的事物,无论是情欲故事,还是爱情故事、仇杀故事、暴力故事,虽然他的身体是那样一个动作,但是灵魂不是那个东西。他一直有一种灵魂叙事在统摄着
身体的动作,这是小说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也是吸引我的地方。
另外,它的叙事方式,刚才有很多专家提到了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我觉得也可以不用那种表达,实际上就是一个分身术,作者本身的分身术。当灵魂跟叙事对象附着在一起的时候,它是这个叙事视角,如马在波; 当灵魂跟叙事对象附着在另外的时候,如木鱼妹,就是我们传统文化里面的分身术的叙事方式。不过,对于成熟的作家来说,对于大作家而言,特别是长篇叙事作品里边,我想等待的就是,他所有的精神力量全部融入他的整体叙事里面,他是“言事之道,直陈为正”。无论是圣事,还是俗事; 无论是情欲,还是仇杀,他是要超越灵魂叙事,还是肉身叙事,都包含在最浓缩的一点。我觉得雪漠先生叙事的能力,以及对文化的一种消化能力,应该具备了“直陈其事”的能力。我期待雪漠的下一部作品有更大的气势,直陈为正,我觉得那时候雪漠就是大作家!
——刊于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第28卷(总153期)
雪漠文化网,智慧更清凉!www.xuemo.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