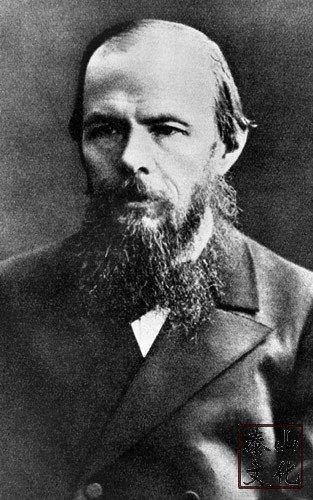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命运,比他的小说要精彩千百倍。癫痫症控制他的一生,发病时全身抽搐,口吐白沫,常摔得头破血流;监禁和流放是他的主要经历,在西伯利亚监狱或国外气味污浊的出租房里,他忙着扛砖头,或四处写信哀求施舍;放荡是他的生活方式,比如,他沉迷于污秽糜乱的性生活,还曾为了赌博,偷过妻子衣柜里的衣服。
后世的人津津乐道于他作品里的宗教情怀,但他的一生却是离经叛道的。无论是道德还是律法,都没能约束他的生活。正如他自己所言:“我毕生都是跨越限度的。”
起初,因为抨击苦难的书稿和激烈的私下言谈,他被误以为是策划阴谋的革命分子,并被宣判死刑。他人生的极端体验就是在这之后到来的:当时,他穿着敛尸服,眼睛被黑布蒙住,捆在刑场的柱子上听完对自己的死刑宣判,并等待随后进行的枪决。到最后一刻,射击被阻止了,沙皇赦免了他,改判流放。
现在,人们已经知道,他是革命传统里最厌恶的那种人,他反对革命。甚至,他连温和的改革也不喜欢。从这个角度来说,将他划在顽固死硬的守旧者群体里,是恰如其分的。即便他曾在沙皇的监狱里熬过4年,每天和盗窃犯与杀人犯同吃同住,搬运砖头,他也不认为有必要改变这个社会 。
这听起来很难以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是那个时代困难命运的最深刻体会者之一。政治压制和平民生活的困顿同时袭击他。他却既痛苦,又甘之如饴。对他来说,生活的苦难反而是一种美。传记作家们则煞有介事地分析:正是从这种对苦难的享受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升华和展现了他宗教的情怀,他通过拥抱苦难而战胜了它,并成为圣徒一样的人物。
19世纪中叶,俄国正不知道往何处去。人们不知道该走向西方还是走向东方,是走向欧洲还是走向亚洲。曾经被东正教信仰统治的社会,一下被共产主义者的无神论笼罩,保守了很久的国家进入了狂热猛烈的状态。这个时候,标准和价值观此起彼伏,互相消长,叫人无所适从。
陀思妥耶夫斯基本身的地位和名声,可以当成这种消长的晴雨表。他出道后获得极高评价,接着被当政者压制和监禁;出狱后,他描写流放者的苦难,连沙皇读完都掉眼泪,他又成为社会的宠儿,办杂志,写政论,结果后来杂志被封,事业破产,不得不流落国外;他长久被人忘记,天天向地位低下的人们奴颜卑膝以求生存,却又在死前被人记起;他在纪念普希金的集会上演说,宣布俄国应和解,短短的讲话让人们如痴如醉。
事实上,没有什么派别是他真正喜欢的。他反感保皇派、改良派、革命派,和所有可能成为时代风潮的事物都不相容。他的小说里,不同的人物有截然不同的价值判断,而他本人也由此被不断贴上各种标签。但人们最终却很难判断,哪一种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的内心判断。到最后,让人们记住他的,反而是那些脱离了时代印记的,更永恒的精神价值。
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反感”与其是一种理性判断,倒不如说是他用来对抗苦难生活的武器。他为躲避债务和政治风险,多年流浪在欧洲大陆的各个国家,人们发现,当他住在法国,就讨厌法国人,住在德国,又讨厌德国人。而他内心希望的,只不过是离开这些人,回到他的家乡去。他从不和国外的作家来往,没有人认识他。他每天自己独自蹒跚走过同样的街道,也许是回到那个肮脏的住处,也许是焦渴地去银行查询一小笔汇款是否寄到。
他的死亡成为他伟大声誉的开始。1881年春天,人们从最偏僻的小镇赶来送别他的灵柩,挤满那间工人居住的小屋,用身子紧紧贴住他的棺材,并因为难过和过度拥挤而不断倒在地上。
据说,无论是亲王、牧师、军官还是学生、工人、乞丐,都对此悲伤不已。不过,陀思妥耶夫斯基临死并没有摆脱那个喜欢给他贴上标签的时代。警察局长将此视为一场事件而试图阻止他,几名异议分子则打算,把囚犯戴的链锁挂在他的棺材上。
转载:http://zqb.cyol.com/html/2011-01/19/nw.D110000zgqnb_20110119_3-10.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