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狂草的特征,就是以天地为法度,以性灵为动力,云驰鹤翔,山呼海鸣。王蒙在80岁的世界,又一次完成了语词的舞蹈和青春的飞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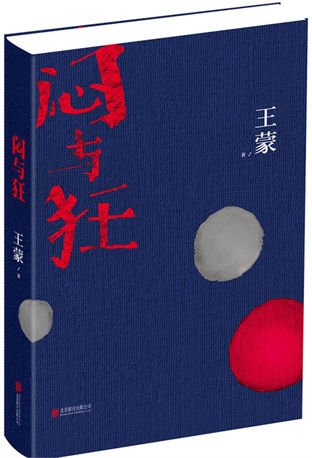
王蒙长篇小说《闷与狂》:不老叙事人的青春逆袭
一直关注这个智者的言说、书写和行为,和他同时代的共和国的作家们在远去、逝去、老去,王蒙依然在言说,在行走,在书写,他仿佛用他自己旺盛的生命在印证他年轻时写作的一部小说题目——青春万岁。青春对这位老人来说自然不仅仅是生理意义上的,而是精神上的,写作上的。
七旬之后,写作的欲望比之以前更为旺盛,而数量更是惊人,几乎是以前的总和,这是奇迹。当然,人们以为他在小说领域渐行渐远的时候,最多偶尔在中短篇小说亮亮身手,比如前两年发表在《中国作家》上的《悬疑的荒芜》和《人民文学》上的《山中有历日》,依然那么矫健,依然那么敏锐而深刻。这还不是最特别的,当我读到王蒙的新长篇小说《闷与狂》(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年8月出版)时,更是感到意外和惊喜。八旬老人写作新长篇小说已是奇迹,因为很多老人的长篇都是旧时代未完稿的整理和续编,而王蒙的这部长篇小说是全新的创作,除了个别章节外,全是近年写就。
更为奇特的是,《闷与狂》的写法太年轻了,太青春了,像疯狂的文字精灵在舞蹈,像张旭的书法在咆哮。而对一个80岁的高龄少年(铁凝语)来说,这时候的文字,往往言简意赅,往往微言大义,而王蒙,青春万岁的王蒙对岁月进行了逆袭,对自己的小说也进行了逆袭,他颠覆的不仅是时间的无情和年龄的冷酷,而是再次证明了李安的那句名言:“这世界上惟一经得住岁月摧残的就是才华”。
读《闷与狂》的第一感觉,就是作家已处于一种追逐的状态,他在追逐历史,历史也在追逐他,他在追逐现实,现实也在追逐他。“我常常陷入一种胡思乱想或者准梦境:我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追逐一个影子。两个影子拼命地追赶我。或者是他们锲而不舍地追逐我,以为我是阴影。”这两个影子一个是历史,一个是现实,历史是现实的影子,而影子又是昨天的现实。在《闷与狂》中,历史和现实纠结着,像两个影子,也像太极图里的两条鱼,互相拥抱又互相离异,朝着同一个方向,又向着不同的方向。历史与现实的无穷纠结,在王蒙小说里尴尬而又潇洒地首尾交接,剪不断理还乱。
王蒙曾经试图整理过这样的纠结,但发现旧的纠结尚未了结,新的纠结又源源不断地涌来,这源于王蒙自己没有停下自己的脚步,他在伴随着时代的前行而前行,而不是大部分老人脱离时代隔岸观火般的旁观,但历史的记忆又时时把他拉回到曾经的岁月。比如,宠物的出现是当下生活富裕之后才会拥有的现象,而王蒙则联想到自己的苦难岁月的宠物,让人心酸,又让人叫绝,“我的宠物是贫穷,弥漫的、温柔的、切肤的与轻飘飘暖烘烘的贫穷。更正确地说,我从小就与贫穷互为宠爱。我的童年与贫穷心心相印。贫穷与童年的我同病相怜。爱就是被爱,宠就是被宠。我钟爱于贫穷的瘦弱。贫穷瘦弱怜惜于它培育出来的发育不良的、火焰燃烧的、心明如镜的我。”在谈到苦难的时候,王蒙又写道:“唯一的苦就是无所苦。无所苦的生活没了分量,周身轻飘飘,脚底下发软,胳臂也变成了面条,大脑平滑失去了折子。思考、期待、忘记与记忆都没有对象。无忧、无碍、无愿、无憾,如仙、如鬼、如魂、如灵,如水泡,如一股气儿,如早就驾鹤西去的云。没有重心,没有平衡,没有注意,永远不能聚焦。”苦与无所苦,谁更苦?历史和现实,谁更荒诞?这些都是王蒙作品里反复出现的无解之题。
王蒙的小说里有一个永恒的主题,就是对青春的描写、讴歌、咏叹,在他关于《红楼梦》的研究文字里,他透过情痴的主题看到的林黛玉永远13岁的少女模样,一任岁月的磨洗。这可能与他的少年布尔什维克的经历有关,他的小说里始终洋溢着、回荡着青春的主旋律。王蒙的青春主题或许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上世纪50年代的创作,那是正面的、写实的、无可遮拦的。与今天“80后”的青春小说不一样的是,王蒙的青春没有校园,他一开始的青春就是在社会的底色中呈现出来的,甚至《青春万岁》这样直接描写中学生的校园题材也是社会化的,因为当时的社会一体化,不停的运动让学校迅速卷入到社会的洪流之中。那个时代的青春是与共和国的青春同步的,每个人的青春都是共和国大合唱的一个音符。在《闷与狂》中,王蒙又一次写到:“青春点起了历史的烈火,青春天然地具有圣战的倾向。青春的五谷丰登是诗,爱它的人如醉如痴欲仙欲死感动莫名鼻涕眼泪灵感天才上天入地,对它不来电的人则认定它是纯粹的窝囊废物点心白吃饭浪费糟蹋装腔作势莫名其妙成事不足坏事有余。”但王蒙还是感受到青春的易逝和永恒,《青春万岁》的序诗之后被反复流传,说明他有一颗感伤的心。
大概王蒙自己也没有想到,抒写青春的结果是青春流放,成就了他青春写作的第二阶段。王蒙1957年被打成右派,青春沉沦了。1978年以后,王蒙和一群重放的鲜花再现在文坛时已是中年,他们在回顾历史的沧桑时,自然充满了对青春年华的顾盼和留恋。《布礼》《蝴蝶》都是反思历史也是反思青春的领衔之作,“是青春点燃了革命,是革命烧透了青春。是革命才华了教育了也纠正着青春,是青春升腾着忽悠着修饰着美丽着也歪扭着革命。青春拥有了革命,革命拥有了青春,于是革命有了强大的未来,有了动人的审美品质。有了多么感动的罗曼蒂克。于是有了躁动,有了狂想,有了威风,也有了那么多幼稚乃至胡作非为大呼小叫。”“呜呼,也有夸饰的、神经兮兮的、像青蛙一样地吹胀自己的肚皮的、泪眼迷蒙的,酸不溜秋的小资的或者浑横不讲道理却认为自己是所谓革命的、因愚蠢而自我拔高的该死的青春吗?”和其他作家不一样的的是,王蒙没有对青春岁月的遭际进行简单的控诉或揭露,他在拨开历史迷雾的同时更多的是对青春的礼赞和回望。在《季节》三部曲中,王蒙对自己的青春壮年进行了具象的近乎纪实的线性描写,对历史的沉思的同时展现了人性的沧桑。
第三阶段是超越青春,青春是美好的,青春是无可替代的,但青春又是不能挽留和定格的。青春不再是一个具象,或者是反思的材料,在《闷与狂》里,这些线性的、纪实性的生活化为一个个片段,化为一个个不相关联的意象,跳跃着、闪烁着,但这些意象本身又是作家的记忆甚至是实录。人生化为碎片,碎片本身也是历史。在这些碎片里,王蒙可以抒情言志,可以哲思禅悟,可以飞翔舞蹈,青春是一片浮云,也是沃土,它在叙事的缝隙,也在人生的缝隙,它在记忆的缝隙,也在遗忘的缝隙。从青春的记录到青春的反思到青春的羽化,王蒙完成了一个青春的回旋曲。
大约在30年前,王蒙的一些带有实验性的小说《春之声》《风筝飘带》等曾被人诟病为“三无小说”,即“无主题”、“无情节”、“无人物”。按照传统的小说概念,这些小说的主题呈辐射性,情节碎片化,人物也非全头全尾,有悖于现实主义的规范。王蒙当时没有去和论者争论是非,他写了《在伊犁》系列小说,可以说全头全尾了,他通过这些全头全尾的小说,证明了自己的写实能力和传统功力。虽然《在伊犁》至今仍获得人们的称赞,但王蒙内心其实更喜欢舞蹈一样的文字,更希望飞翔一样的叙述。
过了30年,过了见山是山、见山不是山、又过了见山还是山的三段论之后,王蒙再一次重拾“三无伎俩”,仿佛蓄积依旧的瀑布“飞流直下三千尺”,顺势而下,倾情歌唱。《闷与狂》是一部真正的“三无小说”,甚至是一部反小说,王蒙穿越纷繁的历史和曲折的现实的羁绊,完成了对人生的鸟瞰和俯冲,将青春与衰老的人生的极致优美地放肆地呈现出来。
或许有些读者不能充分理解王蒙的写法,小说的主人公其实就是那个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我”,这是一种后现代的“元小说”叙述,这就是打破小说的隔离效果,作者是王蒙,同时是王蒙的审视者、评论者。叙述者是作者,也是读者、编辑与论者。在小说里,王蒙描写王蒙,王蒙审视王蒙,王蒙解嘲王蒙,“小说退到了帷幕后边,故事隐藏进了黑影,逻辑谦逊地低下了头,悬念因为不好意思而躲闪瑟缩,连伟大的无所不能的生活表象也暂时熄了灯,它们保持住高度的沉默。作者不想全然告诉你,然而你终于会知道,你终于会喜爱。故事就像最喜爱的仪式,在阅兵广场群众集会上放飞和平的鸽子,你放飞多少就欣赏多少,你送走多少就收获多少,你隐藏多少就诱引多少,你期盼多少就牵挂多少,你挥舞多少就出现多少快乐的旗帜。”这种自我解读的小说,是放飞心灵,也是放飞文字,是心灵的自由舞蹈,也是小说的狂草境界。狂草的特征,就是以天地为法度,以性灵为动力,云驰鹤翔,山呼海鸣。王蒙在80岁的世界,又一次完成了语词的舞蹈和青春的飞翔。
雪漠文化网,智慧更清凉!www.xuemo.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