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我只知道,母亲做了一辈子教员,小学教员,中学教员,以敬业而著称,把一生献给了教育事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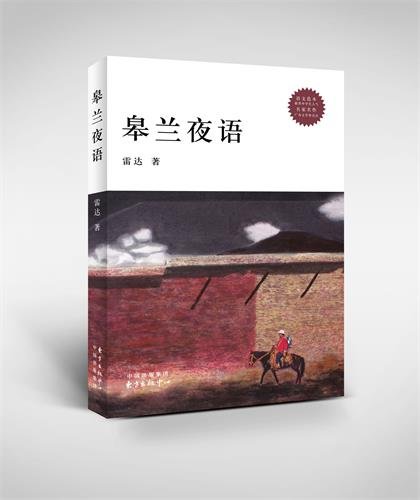
《皋兰夜语》 雷达著 东方出版中心 2014年7月
多年以前
文\雷达
1943年农历2月17,我生于甘肃天水。此前,我父亲因肺病加重,咯血,于1942年夏天与母亲一道,带着刚四岁的姐姐,从兰州回到了老家——天水新阳镇王家庄养病。邓宝珊将军作为同乡,朋友,对我父亲向来器重,曾荐举过,此时也只能说,子烈,你还是好好养病去吧。那个时候肺病是没法治的。据说父亲的肺结核是从他在北京大学的一位同窗好友那里染上的。
父亲是极热爱故乡的人,相信凤凰山下的渭河滩,古老的沿河城,那里的雾岚,柔风,还有浆水面,是世上最好的药方。他相信他的病会好的。就在这一年,他一边养病,一边还与几个朋友创办了天水第一所农校——新阳农校,自任校长。第二年即1943年2月,怀着我的母亲快临产了。母亲不惯乡间的土法接生,住到六十里外天水县一姓邢的女友家中,在那里的一家医院,我出生了。
据说父亲当时很兴奋。那一天,父亲走过一座寺院,听到里面隐约响起唱经声。就在他抬起头的时候,一个和尚迎面走来,向他微笑。他认识这位和尚,是当地的高僧。高僧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他对父亲说了几句话,微笑着走了。那僧人走后,父亲决定为我取名“达僧”。我这一辈子都弄不明白,父亲出于何种心情,何种感慨,甚至何种隐痛,要为我起“达僧”这样的名字,莫非他希望我最终成为一个僧人?在乡里,我的家族到了我这一辈是按“学”字辈起名,男孩的名都得落到“学”字上。母亲舍不得丢掉父亲起过的那个“达”字,于是我的学名便叫成了雷达学,也有通达所学之意。
父亲死时我三岁,对他知之甚少,尽是些碎片化的传闻。但我居然能忆起他清癯的模样。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他生于何年,只知他病殁于1946年。他名叫雷轰,字子烈,别名抱冰,曾毕业于北京大学下属的农学院,学的是农业经济。他虽出自西北一隅,却是当时北大《木铎》杂志的主要编者,文革时我曾查阅过;他还是当年北大学生赴南京请愿的核心人物之一。事急,藏在玄武湖畔的草丛中,险些被国民党宪兵的剌刀剌中。我的伯父从老家带了一小袋银元,辗转了半个月才寻到父亲。据说父亲因为于右任的关系,在南京中央研究院工作过一段时间,后仍凭借陕甘同乡关系,回甘肃后被委任为甘肃省审计室的负责人,相当于现在的统计局。92岁的乡人王纯业在其《顽石斋文存》中记述道,在老家,我父亲曾成功地制止过一场因灌溉引发的宗族间的大规模械斗;说他为人刚烈,敢对乡霸下逐客令;说他接到任某县县长的调令,自嘲说现在贪贿横行,阿谀成风,像我这坏脾气哪能干得了,遂力辞之。最后,他还是到兰州农校任教导主任。干教育好像才是他的正业。他的脾气不好似乎是比较出名的。他一直幻想并努力改造中国乡土社会,新阳农校仅是他这种努力的一个开端。霍松林先生是我的同乡长辈,79年文代会我作为工作人员,到车站接到了他,在车上,我自报了我父亲的名字,霍先生以极惊讶的目光看着我说,你父亲可是我们大家尊敬的兄长,可惜天不假年,早早地离开了人世。在此,我一点也不想美化父亲,也不知他属何党何派,该作何评价,只想客观地看他。在我心中,他大概是旧中国一个传统的、倔强却又不幸的知识分子吧。
父亲雷子烈和母亲张瑞英与当时兰州的许多民主进步人士都有交往,他们在兰州举行了婚礼。著名爱国将军邓宝珊是证婚人。父母结婚时,做了一批天水雕漆家具,上面均刻着证婚人邓宝珊的名字及其他人的,我经常以辨认上面的名字为乐。我其实是父母的第四个孩子,也是最小的孩子。第一个是男孩,去世早;第二个名叫丽珠,后改名雷映霞,就是我现在的姐姐;第三个也是女孩,也夭折了。事实上,父亲在与母亲结合之前,他在新阳镇老家有一位奉父母之命而娶的旧式妻子,也有孩子。那时,中国还是一夫多妻制社会,类似于雷子烈这样的人士大概都经历过相同的婚姻。
1944年夏天,父亲的病越来越重。于是父母带着我和姐姐从天水回到了兰州加紧治病。父亲的脸上总泛着深深的桃红色,彻夜咳嗽不止。母亲一边在学校任教,一边照顾丈夫和一对小儿女。王纯业先生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大约在1946年春,邓宝珊在榆林,却委托“晋陕绥区总司令部兰州留守处”王新令、岳跻山等人,专程来看望父亲。当时父亲卧床,床头摆着好多书,他们转达了邓的问候,并劝父亲不要太用功,养病为上。据说父亲对邓的知遇之情,无语泪流。这年秋,自觉不久于人世的父亲留言,希望他的灵柩一定要从兰州移回故土埋葬。他还希望我和姐姐都能上大学,希望我姐姐长大后嫁给天水人,我长大后娶天水女子为妻。可惜,以后的生活命运谁也无法左右,在我和姐姐的婚姻里,都没有天水人成为对象。
我的童年记忆是从失去父亲开始的。那是一个傍晚,我玩够了回来,见很多人拥挤在兰州农校第三院我家那间屋子的里外,我从人堆里钻出来,看见母亲哭着在床上翻滚,旁边的人不停地劝慰着,但没用,周围的人全都木然的观看着,叹息着。这情景让三岁的我极为恐惧,几十年后在梦景中还频频闪现,成为我童年的第一个清晰而痛苦的记忆。
母亲是位优秀的意志顽强的女人,多才多艺、忠贞善良。父亲的去世对她的打击太大了。在旧社会,失去父亲的孩子也常被视为“孤儿”,不是没有道理的。在那个父权和男权社会,丧偶的年轻的知识女性,面对宗法,舆论,习惯势力的包围,无所凭依,要带着儿女活下去,何其艰难!何况是极封闭的西部。母亲虽遭遇坎坷,却一直对人心存仁爱。当时的兰州不到二十万人,母亲自己过着拮据的日子,但路遇乞丐必会施舍。母亲好学,精通音乐,她在抗战时期曾与丈夫一起去过重庆,在华西大学音乐组进修过一段时间,后一直做音乐教员,每天吃完晚饭就弹风琴。她也喜欢京剧。母亲还写得一手好毛笔字,能背诵许多古典诗词,可以说,这样一位女性达到了新旧更替时代文化上对女性塑造的理想。
然而,命运之神对这样一位女性并不宠眷,她一生守寡,其中的艰难辛酸是常人无法想象的。全家靠母亲一人菲薄薪水维持生活,日子艰窘。小时候的我穿的衣服大都是姐姐的旧衣服改造的,母亲为了让我多穿些时间,总把衣服改得很长,有一种要永远穿下去的感觉。所以我平生很烦长衣服。我没有鞋穿,就穿雨鞋。那时兰州雨水多,有时还下暴雨,我的浅腰雨鞋下雨时穿,天晴时也穿,到了秋天还穿,闷得脚上长出了灰指甲,终生去不掉。母亲给正在长身体的我和姐姐也会改善一次生活,无非是吃炸得焦焦的无鳞的青海湟鱼,让我们一点一点尝出味来。还有兰州冬夜的热冬果,那悠长的吆喝声至今响在耳畔。这只有隔很长时间才能吃到一点。
每当母亲一手拉着我,一手拉着姐姐到兰州农校后面的旷野地里,面对黄昏时苍茫的皋兰山时,我就害怕极了,我预感到母亲又要哭了。果然不一会儿母亲大放悲声。对她,也许是生活重压下的一种渲泄吧。那是我童年最恐惧的时刻,父亲离开的那个傍晚的恐惧也在这时一并袭来,我不由浑身颤抖。母亲的巨大痛苦不是那个年龄的我所能理解的。
兰州农校后面的田野,叫红山根,一向是枪决犯人的地方,每当警车快开过来时,我和小伙伴便在春天刚耕过的松软的土地上奔跑,双腿却像陷在泥泞似的拔不出来,待追上去时,执行者的枪管已冒着蓝烟,被打死的犯人,栽在坑边,血往坑里涌流着。解放前后,我目睹过无数次这样的血腥场面。
在我童年的梦中,或在朦胧的玄想中,还常会出现一个场面:我陷身在满目荒凉的千山万壑中,夕阳西下,风过处,满山的草木悲鸣,我紧贴岩壁,脚下是仅容一只脚踏稳的窝窝印,稍一不慎,将会掉入万丈深涧。
其实,这不是幻象,是真实的回忆。父亲死后,母亲雇了一部道基卡车,在老家来的几个壮汉帮助下,把灵柩装上车,运往天水。母亲,姐姐,还有小小的我,都迎风站在卡车上。一路过定西,过华家岭,过通渭,直到秦安。秦安南面有座无名高山,翻过去,可直接下到我的家乡新阳镇,陡峭至极,常有人悬崖丧命。我依稀看见,抬着棺材的人们手扶岩壁,一步一挪,母亲紧紧拉着我,屏声敛息。三岁多一点儿的我,居然把这一幕永久刻在脑海里了。是的,母亲做到了答应父亲的“移灵”,这所做并非多么意义重大的事,只是为了死者的遗愿,可我总觉得这不仅仅为了爱,而是一种承诺和担当。当年,我的还不到三十九岁的年轻的母亲啊,你这城里娇贵的女性,却在这亘古荒凉的深山里,不畏艰辛,不惧生死,不畏风霜,是什么在支撑着你啊!每想及此,不由我泪珠奔出。
1948年秋,五岁半的我被母亲送入兰州师范附属小学,开始了我的启蒙之路。这个年龄上小学,不论在今天还是在当时都是很少见的,可见母亲对我所抱的厚望。由于在班上我一直是年龄最小的,加之生活在一个不完整的家庭中,不时会受到教工子弟中强横者的伤害,这一时期,我的大部分时光是在孤独中度过的。那时兰州的冬天冷极了,黄河上结了很厚的冰,风像刀子一样。我每年都冻了手脚,鞋底冻得不能弯曲。手上、耳朵上满是冻疮。母亲就给我抹上油在火上烤,那种既很难捱又很舒坦的感觉深印在记忆中。我的脚后跟冻得裂开了条条大口子,晚上烧热水给我烫脚,我疼得大叫,满眼含泪。
进入小学第二年的初秋,八月,我亲眼目睹了解放战争中极著名的兰州战役。四十余年后,我在散文《皋兰夜语》中,感受复杂地回忆了当时情形:“蓦然间,一九四九年八月的皋兰山重现在眼前,我又看见马步芳的骑兵沿山上临时公路昼夜转移。从山下仰望,可以清楚看见山腰间黄尘滚滚,万马攒动,每隔五分钟光景,必有一匹马同骑兵一起被挤翻下来,那只能是当场摔死。那时,不及六岁的我,就专门坐在操场上仰望,痴痴地清点着摔死者的人数。”我的此种亲眼看生死无常的经历,可能极少有人体验;有过这样的经历的人,在其成年后,对生命意义和命运的理解肯定与他人有所不同吧。
儿时的独特经历使我较同龄人更加敏感,更加反叛。在我上小学四年级时,附小来了一位飞扬跋扈,志得意满的年轻校长W,他常粗暴地训斥甚至殴打学生,而孩子们都不敢反抗。有一天,他又训斥我最要好的小伙伴,我站在旁边忍不住用叛逆的仇恨的眼光看定了他,四目对射良久。他走过我身边时硬是盘问到了我的名字。我已有不祥预感。过了几天,突然召开全校师生大会,而这大会的主题,竟然是斗争我!我时年不到十岁,这不到十岁的孩子只能选择拔腿而逃。校方早算计到了,布置几个强壮学生手挽手堵在校门口。可我灵活,一弯腰就蹿了出去,一口气跑回了家。斗争会没有开成,校长恼怒之极。此后学校不让我上学,罪名是“用仇恨的眼光看我们尊敬的校长”。母亲不得不去学校,哭着给这个校长赔情道歉,一周以后,我才得以继续上学。刚回到座位上,校长的狗腿子,麻脸教师V就来了,他用手掌狂擂着我的课桌,桌上的铅笔盒都蹦了起来,他用最恶毒的兰州土话反复侮辱我。我的境遇可想而知。这件事情发生后,一些老师迅速与我划清界限,一个个冷眼相向。幸而班主任周治歧老师,接纳了我,安慰我。不承想,署假过后,那个专横的校长W,因刑事犯罪被抓了起来。我的处境随之好转了。
母亲因对父亲的爱,对摆脱艰难生活的渴求,把过高的期望寄予了我,对我的学业很重视,也很严厉。我考得不好,或者有顽皮捣蛋举动,她会严厉批评,甚至体罚,然后,她自己会伤心痛哭。这样母子对峙场面我经历了许多。
我清楚地记得,有人不止一次地来,劝母亲改嫁,但都被母亲断然拒绝了。母亲说:“我在子烈死前答应他,供两个孩子直到大学毕业。”母亲确实做到了这一点。这在现在可能会简单地看作愚昧和封建。但我想,一个单身母亲,一个年轻女性,在复杂的环境中生存,为了维护自己的纯洁,为了怙恃年幼的孩子不受委屈,为了清白而自尊地活着,她宁愿选择独身。这无可厚非。然而,这其实是需要何等坚强的决心,何等刻骨的爱和何等超人的自制能力啊。
母亲的话题是说不完的,这里我不过是拉开了回忆母亲的序幕。因为篇幅关系,我只能用一封突来的书信,收束这篇文章。
某日,我接到天水文史专家王耀先生来信,言他正在编撰《陇上巾帼撷英》一书,想请我写一篇怀念母亲的文章。他说,“你的母亲是一位刺绣高手,某某家中就曾有老人家的刺绣作品悬挂,希望你的文章能以尊母大人的刺绣为主题来写”。我与王先生素不相识,他忽出此言,使我心头一颤,我吃惊于他何以对母亲了解得如此清楚。他说得对,母亲青年时代确实以刺绣之精美闻名于陇上,旧社会兰州的《民国日报》还专门发过消息,称为“一绝”。这旧剪报文革前我还见过,贴在一个大本子里。从我懂事起,我家的墙上就挂着一个镜框,内嵌一幅刺绣,在一个“心”字形的图案中央,单绣了一个大大的“爱”字,曾挂了很多年。它应是母亲刺绣的代表作了吧。至于它何时消失了,或落入何人之手,就记不清了。文革前夕我分配到北京工作,只留母亲在兰州,文革一来她受尽了磨难,那幅刺绣就此失落在文革风暴中了。我还听说,母亲的另一幅刺绣,被老家——天水新阳镇王家庄的某人拿去了,家里人去讨要,人家不给,还要钱,闹得很不愉快。这是文革后期的事。
这些沉重的往事我实在不愿回想。不过,王耀先生的来信使我动心了,我要在此披露一个连我自己也不甚清楚的史实,那就是:我的母亲张玉书,居然是甘肃省第一个女法官。
我只知道,母亲做了一辈子教员,小学教员,中学教员,以敬业而著称,把一生献给了教育事业;我只知道,我三岁父亲去世,母亲一直守寡,忍辱负重地把我和姐姐拉养成人,把一生献给了我们,别的,就不知道什么了。也曾偶听人说,母亲年轻时受过刺激,心术不正的人欺负孤儿寡母,还暗示坏孩子叫难听的外号,曾使我心如刀绞,欲跟他们拼命。母亲究竟受过何种刺激,在我心中是一个疑问。
母亲去世后,忽一日,宝鸡的陕西第二商贸学校沈克慈先生转来了沈滋兰先生写我母亲的一篇文章的底稿,叫《甘肃省第一个女法官——张瑞瑛》。此文写于1992年元月,距我母亲去世仅二个月。我这才得知母亲一生中的一个重要经历,同时也是甘肃历史上值得记一笔的往事。据这份底稿末尾说明,沈滋兰同期还写有《甘肃省第一个妇女组织——妇女部》《甘肃省第一个妇女问题期刊——<妇女之声>》《甘肃省第一个女邮务练习生——张菊英》等文章,此文是其中之一。它们是否发表过,发表在哪里,我不知道。作者沈滋兰,女,甘肃著名妇女活动家,与我母亲是结拜姊妹,我叫她沈姨娘。她解放前曾任国大代表,解放后历任兰州女中,兰州七中校长,并多次当选全国妇联委员。
下面全文转抄沈滋兰先生的回忆文章《甘肃省第一个女法官——张瑞瑛》:
张瑞瑛(字玉叔),甘肃兰州市人,幼年丧父,家道由富裕迅速没落,寡母在困境中抚养四个儿女,致使她形成多愁善感的性格。她在甘肃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附属小学,附设初级中学班和师范科毕业,1928年留任附小教员。她擅长音乐,会弹风琴,吹洞箫,练得一笔出色的墨笔字。
1931年她被甘肃省高等法院录为书记官,在此之前甘肃没有任何女性从事司法工作。身为甘肃省第一个女法官的张瑞瑛,得意,兴奋,穿着国民党军服,背扎军官皮带,头戴军帽,颇显神气。对分配给她的工作钻研学习,也能应付裕如。对这一新鲜事物,周围的人们以极大的兴趣关注着。正是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十口所言。她是二十一、二岁的未婚女青年,完全没有应付复杂多样的社会的经验和能力,不友好,不正常的气氛越来越严重地弥漫到她的身边,她感到孤独,压抑,手足无措,感到悲愤,终于在极不愉快的情况下,离开了工作了约一年时间的甘肃高等法院。
张瑞瑛离开法院,重新回到小学教师的队伍里,投入地驾轻就熟地做教学工作,安居乐业。后来转到中等学校里教音乐课和其它工作。解放后,张瑞瑛在兰州十四中学曾荣获优秀教师的称号,曾长期任该校教育工会主席。1974年自十四中退休。退休后的张瑞瑛身体健康,情绪高涨,频频往来居住于儿子雷达学(笔者的原名)工作的北京和女儿雷映霞工作的陕西武功西北农业大学之间,愉快地享受晚年美好充实的生活。1988年她身体渐衰,病渐多。1991年12月16日病殁于女儿家,终年84岁。
沈滋兰 1992年元月
在文中,沈滋兰先生始终称我母亲的原名,并对母亲的情况通过我姐姐知之甚详,可见她们结拜姐妹(母亲大,沈小)的感情之深笃。在谈到母亲受刺激一节,点到为止,并不深谈。这篇文章底稿,姐姐交我后,我一直妥善保存着,却也不想发表。也许是中国人求平安,为贤者隐的心态吧。现在,王耀先生既然如此热心,我就将沈先生原稿和有关情况抄出,或许可以补上甘肃妇运历史上的一个小小缺环。
我一直非常奇怪,为什么经历了这么多年的风雨,母亲却只字未提这一段经历?组织上当然是知道的,可她何以坚决不说。是她有意掩盖,还是不愿自己的儿女知道这些。可这又有什么呢?在今天看来,都是些很自然的事。当然,在那些年代,这可能是严重的罪状,还可能引来大祸。我推想,母亲一定认为,她的儿女知道得越少越安全。
雷达散文代表作《皋兰夜语》此处有售: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0.0.0.0.EW0SNr&id=41000485038&qq-pf-to=pcqq.c2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