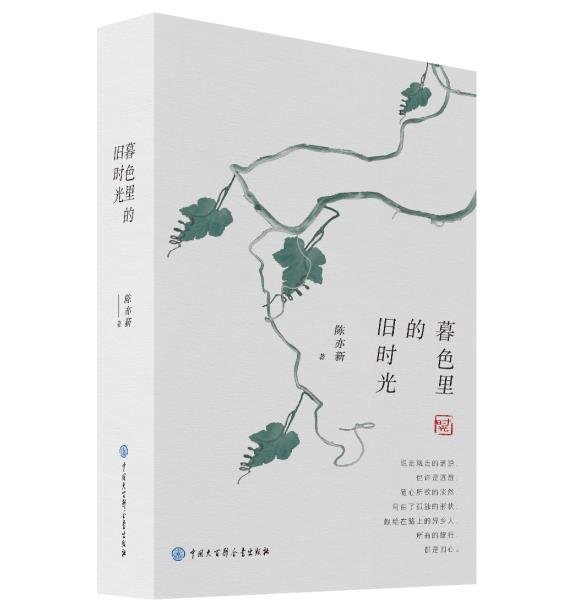
暮色里……
文\任冬云
2019年8月28日 星期三 蓝天白云
在这个夏末的暮色里,我拿到了陈亦新的《暮色里的旧时光》。陈亦新,甘肃凉州人,文学新秀,青年旅行家,《暮色里的旧时光》是他的散文集。
个人以为,散文不比小说,若非大家名篇,能静下心来整本品读的人不多。拿我来说,眼睛只过多地留驻于两位作家——余秋雨先生和蒋勋先生。但今年,2019年几个暮色里的阅读,给我又添新欢。
初始阅读,并不觉好,平平淡淡,山重复水重复的,有点读不下去,耐着性子。读到作者一行人从四川入藏时,感觉不一样了,文章一扫之前的风格,用全新的笔触,缓缓为读者拉开了一方神秘帷幕,那块辽远而庄严的土地慢慢呈现,藏地气息扑面而来,气势摄人。
世界漆黑而寂静,只有窗外的远方有星星点点的光……每一天都让人恍如隔世,那些身后的山水,仿佛是梦中遥远的记忆,化为烟雾摇曳着远去了。
——摘自《康定,情歌的故乡》篇
文字清新细致,文思幽远绵长,一切是那样的陌生而又似曾相识。
我没有去过四川,更不曾涉足藏地,是它把我带进康定,带进了情歌故乡的黎明。我又何尝不是依窗眺望的旅人,准备迎接一场期待已久的冲击和洗礼?
站在你的天边/触摸你的每一缕气息/刺骨的不是离别/是回忆……/诵五百年《金刚经》/不求成佛/只为下一世与你擦肩
写下以上文字时,我恍若看到一个背影,在青藏高原上匍匐,一步一步虔诚,那是我吗?
——摘自《世外山水》篇
是啊,那是我吗?
和着作者的心跳,不禁自问。
那匍匐在地的,是藏胞,是作者,是读者;那念诵真经、攀缘仰望的,是藏胞,是作者,是读者。
这一切,都是我想要的。
天边的风马,异域的风情击中了作者,作者的声声叩问击中了读者,击中了不敢目睹风马、不敢转动经筒的那一个卑微的、沾满尘垢的灵魂。这灵魂,尚存余温;这灵魂,无所依怙。
闭目掩卷,良久思忖:为什么你的字典中有太多的不舍?为什么你心存远方却屡屡举步维艰?为什么脚步和心总不在一起?
太多的掂量,只会迷失自己最初的模样。
读者的泪和作者的泪一起淌。
于是,我停止诉说/收起眼泪,静坐蒲团/却蓦然发现,大殿上佛的模样/竟变成了自己
——摘自《前世嘛呢(上)》篇
死亡,还是涅槃?作者在这里给了生命最深情的归路,这是骤雨后的宁静,千山万水后的坦然。这种灵魂层面的救赎,我把它读成是一种大悲悯,它终将生命引向喜悦和静默。
这份觉悟,是我所求。
此刻,不再流泪;此刻,不再有泪。

2019年8月29日 星期四 蓝天白云
《暮色里的旧时光》模糊了年龄、模糊了性别、模糊了族群,模糊了你我,模糊了红尘与净土。
喜欢了,就呆久了。住在藏民小院,落鸟、清晨,穿过小树林去打清冽的溪水;呆久了,自己也便成了烟雾缭绕经殿中转动经筒的白发老奶,成了放飞风马的人,成了“起伏在爷爷磕长头的那条路上虔诚的朝圣孙儿”;呆久了,就连“隔壁女人”金牙闪烁咧嘴一笑也成了一幅动人画面。
请允许我打个比方,假如说余秋雨先生的散文是一袭华美的中华衣袍,蒋勋先生的散文是迷人的耳畔丝竹,那么,我想这么说,陈亦新的散文则是来自雪山的梵音清凉。
一般,文人偏于飘渺,学者过于干巴,而陈亦新则舍弃了过多的飘渺干巴,把那些迷离和艰涩自然融合,让它们对坐相视而笑,这种包容和气质实属可贵。
默然相爱,寂静欢喜。
感谢遇见《暮色里的旧时光》,感谢遇见陈亦新。
忍不住,再用一段引用来作为本篇的结束语:
一声声呐喊,一次次抛起,我觉得放飞的不仅是风马,还有我们自己。其实,我们都是风马,在宇宙和轮回中,生生世世地翻飞飘荡着,一次又一次,永不停息。
——摘自《风马灵魂》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