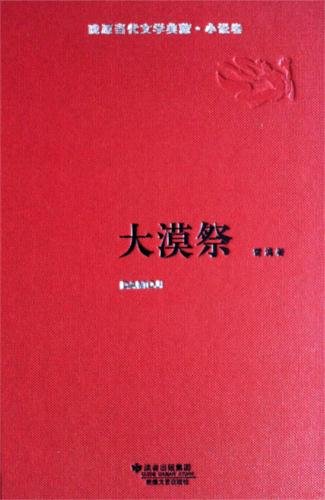
西部,苦难的召唤
——读雪漠《大漠祭》
我不知道该怎样去记录那一串串文字。在生活的苦难中间,一切的呻吟都是虚假的,唯独那健壮的肌肉与之搏斗的雄壮才值得大书特书。也许,面对苦难,我常常在逃避,因而我的笔下也就难以流泻出足以震撼人心的文字。但是,这么一个人,这么一本书,让我找回了对自己的信心。源自对西部人生活的苦难的记忆,亦源自我自小所经历的苦难的磨练,我像吸吮奶汁一样阅读着雪漠以及他的《大漠祭》。在荒凉的腾格里沙漠的边缘,居民们延续着祖辈传承了几千年的生活,狩猎、耕作、结婚、生子、送葬、祭祀……这样的生活从来没有人打扰,它因而显得平淡,如细水涓涓流淌,闭塞与落日相辉映,愚昧与长河相永存。由于恶劣的自然环境,生存起来是那么的艰难。在居民们的意识里,苦难一如家常便饭,没有什么命运不公的喟叹,他们只是这样一如既往的生活着。
长久以来,我视这样的生活如一潭死水,污浊、封闭、愚昧、落后,没有生机和希望。大山隔断了视野与天际一线的牵连,生存的欲望把人们和土地牢牢的捆绑在一起,逃离土地意味着背叛,翻越大山意味着死亡。沙漠无情的吞噬着一个个脆弱的生命,没有理由,只是因为它是沙漠,有着强大的摧毁力而已。于是,我一直尝试着丢弃这样的生存方式,甚至剥掉身上那层“农民皮”。那一年秋天,在绵绵的细雨中,我拎着行李包踏上了南下的列车,像逃命一样逃离了生我养我的土地。从此,我开始把自己塑造成为一个城里人,我用知识填充我贫瘠的大脑,甚至在心里深处排斥与农民相关的一切。土地,我不再眷恋;粮食,我也不再关心。城里人关心的是钱,有钱就有了一切。因而,生存危机在金钱的拯救下一次次化解,在危机化解之后享受着充裕的物质世界,却忍受着精神空虚的煎熬。在这样的生活中,人们渐渐变得麻木,消蚀了理想,习惯了虚假与欺骗。但是,读雪漠的《大漠祭》,给我的心灵带来了很大的震撼。当自己在生活中迷失了方向,握起笔不知道该写下怎样的文字的时候,这部小说让我猛然之间醒悟了过来,一种强烈的罪恶感和内疚感向我袭来。背叛带给我的是无以复加的痛苦,如慢慢长夜阻遏着行路人。
雪漠被认为是当代西部最有原创力的作家,他积十二年之功创作《大漠祭》,在国内文坛奠定了他作为有分量作家的地位。作品出版之后,好评如潮,一时间人们把视野伸向了小说中所描绘的那片世界——腾格里沙漠。小说的基调是向人们展示生活在那里的人们面对苦难所表现出的乐观、豪迈、独立、坚韧、自足。作者近乎白描的笔触,细致入微的描绘了村落里人们的生活状况。在西部,贫穷是压在农民头上的一座大山,恶劣的自然环境,造成了农民普遍的贫穷,如同小说中写的,那亘古如斯的戈壁大漠的寥廓与寂静,同西部地域环境所特有的广袤、本真、神秘,乃至原始自然的特征,与人类的生存本性达成了对应和同构,这种生存本身就带有一种对抗,在对抗中追求一种超越。作者能够十二年如一日,超越浮躁回归大化淳流的境界,正是这种自我超越精神的极致表现。
雪漠无疑是伟大的。他能够本真的写出农民的所思所想,所憎所爱。《大漠祭》完整的展示出苦难在农民的身上似毒瘤般蔓延,这源于他对农民的爱,源于他与农民父老乡亲心灵的相通。他曾说:“我的西部农民父老就这样活着。活的很艰辛,但他们就这样活着。”语气中透露出半点无奈,但更多的是爱,这种爱是他对苦难的讴歌,亦是他对苦难的诅咒,一个作家,能够把自己的创作同人类的生存相联系,就称得上是伟大的作家了,何况他是在一种生存意识强烈的促使下,一个人孤独的对生存进行漫无边际的思考,在思考的过程中一次次陷入精神的危机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与托尔斯泰、赫尔岑、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心灵上是相通的。前者是俄罗斯民族苦难的灵魂,而后者则是中国西部苦难精神的招魂人。
再回到《大漠祭》的文本构架内看雪漠对苦难的具体诠释。由于贫穷,兰兰与莹儿两个女人为了彼此的哥哥而换婚,这样的开头就已经为二人的悲惨命运埋下了伏笔。憨头老实,但他有身体痼疾,他与莹儿只是名义上的夫妻,而莹儿与灵官(憨头的弟弟)的媾和则是在满足人的一种本能需求,但这在道德上是不允许的。因此憨头的死,对莹儿和灵官来说便是永无止境的内疚与罪恶感。同样的,兰兰与白福的婚姻也因为兰兰没能为婆家生下男孩而备受磨难。除了这两段婚姻外,小说中对于“训鹰”、“抓狐”、“驱鬼”、“降妖”等民俗文化的描写亦让人深切的感受到作者对于主题的升华。不管是“训鹰”、“抓狐”等活动体现农民的勇敢与智慧,还是“驱鬼”、“降妖”这种近乎图腾崇拜的行为表露了农民的愚昧与落后,作者都是在一种理性的克制下,平静的向人们诉说着西部人生活的原貌。控诉是多余的,悲悯则令人窒息,在这样一种迷乱的情绪中,作品流露出的是人作为生命个体往往是脆弱的,在自然生命和社会生命的双重压制之下,人的坚韧和激情趋于柔弱,人的道德趋于失衡。作者所描绘的西部民俗文化的原始面貌,也是他在思考农民生活的过程中,渗透了个人苦苦的挣扎乃至心灵的裂变。他一方面说明作者与西部乡土文化母体之间的复杂关系;另一方面也是作者如同广大的农民父老一样,在这种精神活动中净化渐趋麻木的灵魂。白福把自己的女儿亲自扔进了沙漠,仅仅因为女儿出生的时候他恰好打死了一只狐狸。他相信狐狸精转世的说法,因此这样做就是给自己心理上一个安慰,这与《圣经》里亚伯拉罕杀子献祭上帝的宗教迷狂行为是不同的,前者是一种精神安慰,而后者是一种宗信仰。
生存是西部最为沉重的话题,尤其是农民的生存,雪漠以诗意的笔触探寻生存的艰辛。他特殊的人生经历,使他对人生的苦难有切肤的体悟。而希望在哪里?是灵官的出走吗?这是否是鼓励农民逃离土地,抑或是灵官作为有文化的人,他的出走是为了引进知识文化,改变农村贫穷落后的面貌。
我久久不能语之。
阅读《大漠祭》,它迫使我时不时停下来去思考农民的出路和农村的希望。苦难并不卑贱,但高贵的苦难从何而来?贾平凹在描写农民离开土地,涌向城市追寻梦想的时候,却被城市无情的撕裂身体和灵魂,身份的认同,观念的转变等深层次问题不是用物质手段就能解决,而生活在不断卷入市场化和城市化的农村,物质生活的满足却带来了精神文化的缺位。疾病折磨着农民的肉体时,也拷打着他们的灵魂。这些问题在我阅读《大漠祭》时不断的侵袭着我的灵魂。逃离土地之后换来的不是身份的改变,而是一种深深的内疚感和罪恶感。我的父母以及成千上万像我父母一样的农民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在贫瘠的土地上耕耘,换来的不是舒适的生活,而是苦难漫无边际的延续。我突然想起鲁迅的一句话来,他说:“希望之于虚妄,正与失望相同。”站在一种无以复加的沉重的肉体折磨之上,精神的虚妄却以失望为地基。只是,《大漠祭》给了我勇气,我将敢于正视西部那苦难的召唤,用笔记录西部人生存的意志和愿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