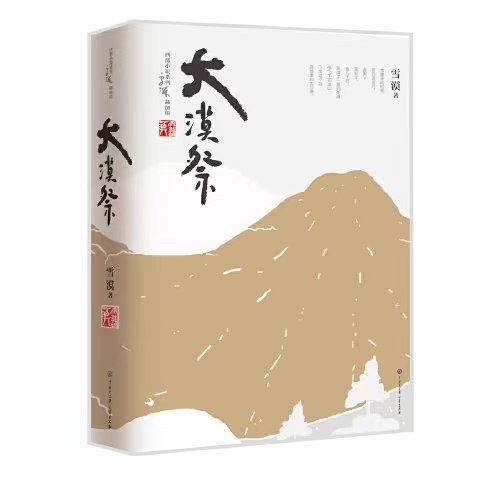
论雪漠《大漠祭》中的精神民俗书写
杨皓喻(兰州大学文学院)
雪漠的《大漠祭》是一部内涵丰富的民间文化巨作,忠实记录了西域乡村一家人一年的生活。首先,通过作家的文化认同,孕育出独特的民俗意识,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其次,深入探讨了精神民俗在现实空间与梦境空间中的表现形式,从而全面感知不同心理层次的精神力量。最后,探索了后全球化时代下全球与地方的关系,以及地方文化在全球化挑战中如何实现突围。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西部经济边缘化形势愈演愈烈,许多致力于以文学作品指涉西域文明形态的作家纷纷转向。在这种情况下,甘肃作家雪漠却始终将创作理想根植于西部大地,在苦修几十载后最终创作出了真实再现西部生存图景的“大漠三部曲”。《大漠祭》作为该系列的开篇之作,通过长篇故事叙事、日常生活展现和西部乡民的人物群像描绘,定格了在现代化冲击下四散飘零的边地民风民情,为“大漠三部曲”确立了整体基调,也为大众开启了洞悉凉州乡民精神世界的大门。
雪漠的乡土民俗书写看似是对过去的缅怀,实际上是一种关注文化建设的积极姿态。在众多民俗类别下,精神民俗由于其特殊的内在属性,更容易与作者及作品本身达成深层次的文化贯通。本文聚焦 《大漠祭》 中的精神民俗书写,探索其中深刻的精神文化内涵以及蕴含的对民族文化精魂和话语构建的关切与思考。
一、由文化认同生发的民俗意识
现代性的发展引发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危机,尤其是对于较为弱势的文化而言,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现代性文化往往容易导致人们产生自我认同的困惑,在各种认同中,“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1],其主题通常围绕自我身份和身份正当性的问题展开,是人们对自我身份的确认。
认同过程一方面需要通过自我向外扩大进行确认。雪漠少时在甘肃凉州一座西部小城长大,后来迁居广东东莞,但他总将自己说成是“一头见到光明的驴子”[2],把城市生活视为一种近乎耻辱的异乡体验,足见他深厚的乡土情结和“农民的儿子”[3]的身份归属。西北乡村的地域文化是雪漠承认并接受的文化内容,他通过赋予文化形态将其翻译成现在的语言,并以此找到了回到生命最深处的本源的道路;另一方面通过“排他”划清了与“他们”的界限。虽然雪漠迁居东莞,但他仍坚定地表示:我还要扎根于这种文化,热爱这种文化。[4]文化认同往往就是在与异质文化的交流、冲突或互动中显现的,地域文化认同是一种在特定地区内形成的对该地区事物的积极体认,核心在于对地域文化和基本价值的归属以及自我身份的确认。
地域文化特质会深深嵌入人们的社会互动和生存状态之中,对其文化心理和价值观念产生潜在持续的影响,不同的地理和人文环境又会产生表征各异的民俗文化。雪漠在 《大漠祭》 中对西北民俗的书写,便是在特定历史语境和地域文化中孕育的一种特殊文化现象。民俗化的生活场域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形塑着雪漠的艺术气质,为他的民俗书写提供了独特的写作背景和故事素材,注定了其民俗书写的多重精神维度。少时在凉州的生活经历使雪漠在体味底层生活艰苦的同时,收获了丰富的民俗文化体验,生发一种血肉相连的情感,并且能够站在民间立场以农民的视角,记录西域乡民的生活,也书写着自己的生命历程。
“有一个记者问我,你是怎么想出这些故事的?我告诉他,这不是我拼凑着想出来的,我生存的那块土地上本来就充满着这样的故事,在民间以‘潜文化’‘隐文化’的方式影响了当地一代又一代民众的风俗和生活。”[5]归根结底,雪漠的民俗意识来自特定生活场域下的文化认同,是作家站在民间立场的地域归属。作家以作品为媒,从具体描绘到抽象表达,全面揭开了西部大漠的神秘面纱,并真实再现了西北农民的日常生活。这样的呈现让读者深刻体会到西部大漠的地域特色,感受到一个充满生命力的凉州地理区域。“我想写的,就是一家西部农民一年的生活 (一年何尝又不是百年),……换言之,我写的不过是生之艰辛、爱之甜蜜、病之痛苦、死之无奈而已。”[6]雪漠所坚持的是在西部大漠这一特定“地域”里展现着“民间”特有的民俗文化,同时在民俗特有的“民间”基础上,更加眷注西部大漠的“地域”,形成一种相辅相成的特殊文化形态。
雪漠之所以进行西部乡村的精神民俗书写,根源在于其对于西部大漠文化的深刻认同。在现代性文化冲击传统文化秩序、破坏文化生态平衡的背景下,文化认同与文化冲突相互交织,难以分割。雪漠的文化认同虽缘起于地方文化间的碰撞与交锋,但最终却与抵御现代性文化冲击密切相关。在文化认同的再发现和再确认中,雪漠生发出对西部乡村精神民俗的深刻书写,这既是对地方弱势文化生存权的维护,更是对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和传承。通过这些民俗书写,雪漠试图展现西部乡村特有的精神世界,凸显其文化价值和独特性,不仅记录了一个濒临消逝的文化世界,更表达了对地方文化根基的深切认同和热爱。
二、双重空间呈现的精神民俗书写
钟敬文认为:“精神民俗主要包括民间信仰、民间巫术、民间哲学伦理观念以及民间艺术等等。”[7]与其他民俗不同,精神民俗由于和情感紧密联结,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与作品深层的文化精魂达成某种内在一致。“我们在任何地方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抓住精神的本质,而只能在它的多种多样的表象中遇到它。”[8]这种有明显目的和自觉形态的产物会藏匿于各个空间,所以从现实空间与梦境空间,双重空间出发进行捕捉,或许可以更全面地发掘 《大漠祭》 中的精神民俗书写。
首先,精神民俗是传统社会乡民美好愿望的投射。民间信仰往往在各种特定的仪式活动中形成相应的精神民俗。在 《大漠祭》 中雪漠描写了“打醋弹”仪式,所谓的“打醋弹”是指祭神结束后驱赶屋内野鬼的一系列活动:
醋弹神得请。平时不知它身居何处,用时只要到河滩上找一个圆溜溜烧不烂的青石头,跪下叩请,即是醋弹神……
他往铁勺里放些头发,倒点醋,将那烧红的圆石头放进勺里。酸溜溜的焦毛味伴随嗤啦啦腾起的雾气顿时弥漫全屋。老顺的身子变得异常敏捷。他猴子似的进屋上炕,上蹿下跳,把冒着白气怪味的铁勺探向每一个角落。而后,在门槛上倒一点醋,又风一样卷进另一个屋。
醋弹神一出,猛子马上关门,以防野鬼再次溜进。
灵官则负责放炮。一个个炮飞上夜空,炸响。一股浓浓的火药味,将驱出屋的鬼又撵到院子外面。[9]
“打醋弹”仪式符合交感巫术的逻辑,旨在揭示人类在面对未知和不可控因素时,通过文化和精神手段寻求理解和控制的努力。交感巫术包括两类分支:一类是顺势巫术,通常将相似的事物当成相同的事物;一类是接触巫术,往往将事物过去的联系作为永久的联系[10]。这里充当醋弹神的青石头作为一种自然物,因其“烧不烂”的特性,同醋弹神被鬼惧神怕的强大属性具有相似特征,遂被赋予了神圣和不可摧毁的象征意义,后乡民们通过跪拜叩请的方式与其产生“接触联想”,从而达到与神圣力量建立联系的目的。这一仪式通过挥舞放有头发、醋和烧红的圆石头的铁勺驱赶鬼魂祈求平安,酸溜溜的焦毛味和嗤啦啦的雾气不仅带来视觉和嗅觉上的具身性体验,更是精神上的反身性安慰。“不是所有的传统巫术完全是百分之百的装神弄鬼。有些巫术经过调查,在跳神和唱神歌的仪式里,有大量的心理治疗功效。”[11]如作品中写到,“灵官感兴趣的不是‘打醋弹’的过程,而是氛围。他很惊诧这种仪式独特的氛围带给人的心理效果”[12]。仪式中的各个角色分工明确,老顺负责在屋内驱鬼,猛子负责关门防止鬼魂再入,灵官则在院子里放炮进一步驱散鬼魂,这种精密配合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乡民间的合作精神以及对仪式的虔诚态度。
作为特定历史阶段民众的生活表现,这些充满神秘色彩的文化传统可能会被视为与现代背道而驰的封建迷信。然而,对于身处偏远闭塞的西域乡村的人民来说,这些神圣庄重的祭祀信仰习俗,往往承载着深厚的精神寄托。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些信仰习俗对民众的生活具有一定的教育和引导功能,不仅揭示了乡民们的精神世界,展现了乡民躲灾辟邪以求得安稳的最朴素愿望,也体现出精神民俗对于重建文化认同的功用。
其次,精神民俗也是传统社会乡民生命意识的体现。生命意识往往是人类对于生命所产生的一种自觉的情感体验和理性思考。雪漠作为一名文化学者型作家,他毫不掩饰对自我情感的审度和对伦理道德的批判,不遗余力地在《大漠祭》 中书写着西域乡村中当地人的精神民俗,彰显着自我和乡民的生命意识。
除了前面祭神、“打醋弹”等祭祀活动,雪漠还着重描写了神婆为憨头燎病禳解的过程:
齐神婆扔了烟头,吩咐猛子搬来八仙桌,上了盘每副盘有十五个馒头,占了大半个八仙桌。齐神婆摆上香炉、鸡血酒、蜡烛、羊肉祭祀等,然后燃香,点蜡烛,焚表纸,口中念念有词。
神婆的禳解仪式简单,不写牌位,不念祷文,向来是直趋目标。焚香燃表之后,齐神婆上了炕,拿过一叠五色纸,在憨头身上绕来绕去,念叨。[13]
齐神婆的禳解仪式通过一系列交感巫术,反映了传统社会乡民对生命的关注和重视。仪式准备阶段,猛子搬来八仙桌,摆放着十五个馒头、香炉、鸡血酒、蜡烛和羊肉等祭祀用品,象征着丰收和生命的延续。齐神婆点燃香烛,焚烧表纸,口中念念有词,通过这些行为与神灵沟通,祈求庇佑憨头。随后,齐神婆拿着五色纸在憨头身上绕来绕去,念叨着咒语,象征着驱除病魔和邪气。作为一种精神民俗,禳解仪式通过代代相传,一定程度上保持了文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这种超越现实服务于乡民精神生活的信仰行为,犹如在艰苦岁月中克服无法逾越困难的强心剂。虽然作品中神灵并没有阻止憨头被病魔吞噬,这一结果直白地批判了民间信仰、民间巫术等对乡民生命意识的桎梏,但精神民俗带来的向心力却有力地支撑着人们在艰难环境中顽强生存,昭示着乡民的生存之道。又如应事的老道为憨头做起灵前的最后一道仪程,为亡灵念 《指路经》,这一过程作为一种民间艺术是精神民俗的体现,经文内容是对亡灵的开解与命由天定的心理暗示,超脱生命躯体,否定他存在的证据,延续生命本真的存在形式,这是人必然面对的命运,是悲剧也同样具有崇高的美学价值。
极度艰苦的生存环境造就了西域乡村人民对精神民俗的坚守和笃定,在这些民俗中具有对有限的超越,更是对虔诚信仰和纯净灵魂的无限追求。雪漠在 《大漠祭》 中对这类精神民俗的书写,不仅揭示了乡民的精神世界,也提醒现代读者重新审视传统精神民俗在过去社会中不可替代的心理力量,这种敬畏生命、尊崇自由的生命意识不仅在传统社会中具有重要意义,在现代社会中同样值得反思和继承。
再次,心理空间中的精神民俗书写也侧面反映了民间哲学伦理观念。神话传说、巫术仪式等精神民俗,在荣格看来是某种内部经验的象征,是集体无意识的意象。[14]通过民俗,集体无意识的原型得以在文化中传布,为群体提供心理调适和社会认同机制,同时为理解精神民俗的深层内涵提供一个有力的框架。
在梦境空间中,精神的产物浮到了表面。现实空间与梦境空间的悬殊差异标志着创作的心理模式与幻想模式之间的差距。心理模式的创作方式,其素材来源往往是人类的有意识的生活;而后者的素材往往来源于人类心灵深处的某种奇异的事物。[15]
在 《大漠祭》 中,作者总共创作了五场梦境。小说开篇便通过梦境为读者引出了老顺的日常生产生活:“他梦见千万只兔子张着血红大口向他扑来,铺天盖地的。”[16]老顺不止一次做这个梦,惊醒后,他认定那是死在他手里的兔子来索命。老顺反复梦见千万只兔子张着血红大口向他扑来,这一梦境象征着他内心深处的愧疚与恐惧,“重复梦”的梦境空间对梦者老顺自身有明确的补偿效果,现实中他以放兔鹰狩猎为生,久而久之总有抹不掉的杀生阴影。梦境中铺天盖地的兔子代表着老顺过去狩猎行为的报应,这种不断重现的梦境在心理上对他进行着深刻的审视和补偿。民间哲学认为,“举头三尺有神明”,一切行为都有其后果,这一信念在老顺的梦境中得到了具象化的体现。老顺的无意识在梦中进行了干预,补偿了现存世界的情感欠缺以及不愿面对的“杀生”的因果报应。通过这种方式,雪漠揭示了乡民内心深处对因果报应的敬畏和对自身行为的反思。梦境空间不仅是一种心理暗示,更是对乡民生命意识和伦理观念的深刻描写,展现了民间哲学如何在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中发挥作用。老顺的梦境通过象征性的叙述,体现了乡民对生命意义的探索和对自身行为的道德审视,深化了作品对精神民俗的书写。
其余几场梦境如出一辙,分别为白狐复仇、白虎叼走憨头、憨头死而复生等。这些梦境内容不约而同地表达着民间哲学伦理观念,民间伦理的核心内容往往与家庭的生存、发展密切相关。[17]作品刻画了为维持温饱而辛勤劳作的普通底层群像,因为地理气候条件相对艰苦,造就了生活在西域乡村的人民把生存繁衍当作人生大计,所以当白福杀生后,一家人担心白狐会让家族断后,甚至认为引弟是狐妖投胎来复仇的。在民间伦理中,延续香火是家族存在的证明,是西域乡民的最大愿望,他们与生俱来的恐惧便投射到了梦境空间。
双重空间呈现的精神民俗书写揭示了精神民俗如何反映乡民的信仰和心理需求。现实空间中的信仰习俗和梦境空间中的心理象征,展示了不同维度的精神民俗书写,呈现了“民众”独特而深刻的文化画像,阐明了惯常的信仰习俗如何衍变成“精神民俗”,同时其又如何反作用于信仰,从而深化了读者对《大漠祭》中精神民俗的理解和认识。
三、后全球化时代下精神民俗书写的深层价值
作为民间文化形态之一的精神民俗为民族共同文化奠基,是民族文化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展示了中华民族的独特风采。新时期以来全球化进程势不可挡,这股强大势力必然会带来“全球”与“地方”的相互适应与博弈,探寻“全球”与“地方”间过度消解与冲突割裂的破局,成为地方文化立足全球思考的关键。全球化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区隔,不同文化模式展开了多元的融合交流,这意味着在交融过程中将不可避免地造成原有文化秩序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精神民俗的重要性愈加凸显,它不仅作为文化传承的载体,维系着民族的文化根基和精神认同,同时也在全球化的冲击下,提供了一种稳固的文化依托,使得地方文化在全球语境中得以保存和延续。
“地方感”是人类生命体验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与个体心理因素紧密相关成为新的核心议题。其中值得思考镜鉴的是多琳·马西提出的“全球地方感”理论,该理论阐明了在全球化时代,地方如何在与全球产生联系的同时不被征服。“地方是开放的,是从正在进行中的故事之中编织出来的,是权力几何学内部的一个瞬间,而且是处在进行之中的,是尚未完成之物。”[18]不同于海德格尔所构建的静态、稳定和边界的保守地方观,她不再拘泥于地方感的根着性,而是追求地方在与全球互动过程中的动态独特性。在她的理论中,地方之所以不受全球征服是因为多元的地方认同,而形成地方认同的关键要素之一就是本土文化。
一个多元文化融合的文化,不同文化通过不同的地方性生活加以区分,“民俗作为传承性生活方式,是一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层,也是多元文化中特定民族的精神基因”[19]。精神民俗更是展现人民生活、文学表达和文化意义的重要载体,《大漠祭》中的民间信仰、民间巫术和民间哲学伦理观念等,不仅反映了乡民的日常生活和心理需求,还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在与外界互动过程中的凝聚和显化。通过具体的精神民俗描写,雪漠令读者深刻感受到地方文化的丰富内涵和独特魅力。这种精神民俗不仅在维系乡民的文化认同和精神归属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还在全球化进程中,通过展示地方文化的独特性,促进了地方与全球的良好动态关系的建立。《大漠祭》 中精神民俗的描写,彰显了地方文化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坚韧与活力,体现了文化多样性和民族精神的价值,从而在文化传承和现代化之间建立了一种平衡。
“在初版中,许多民间文化是被删了的,如二舅帮老顺家祭神的详细经过,如牌位的内容,如齐神婆给憨头燎病禳解的详细经历,如憨头的丧仪经过和老道念的 《指路经》,等等。我想,多年之后,再找这类东西,也只能在我的作品中找了,就留下了。”[20]这些“文化密码”正逐渐随着地域性的消失丧失寄身之地,雪漠深谙西部民俗生活场域,对民俗与本土文化间的联系有着深刻认识,他意识到民俗之于民俗文化的重要性,更忧虑民俗消散背景下民族精神的文化缺失,于是在创作中有意地进行民俗的深度展现。虽然不是所有的精神民俗书写都彰显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文明,对中华民族的精神文明建设也不一定完全只有正面价值,比如一些迷信和宗教仪式导致乡民忽视科学和理性的力量,对家族和宗族观念的过度依赖压抑个体的权利和发展等,但在此之外,作家通过民俗书写唤起读者对地方文化的关注与重视,以及作者对深度精神文化缺失的担忧和重建的诉求,才是他呈现精神民俗书写追求的意义。
雪漠在 《大漠祭》 中的精神民俗书写,“表达了一种尤为深刻、鲜明而有力地表达本民族生活的美学理想,这种本土化不仅体现在作品坐标线的生活内容,也显示在它的表现形式方面。在这一意义上,本土化经常与民族性、乡土化的意义重叠”。[21]尽管外界空间对地方的影响在短期内无法完全避免,但民俗文化作为本土文化的核心,一定程度上能够协调二者之间存在的可伸缩张力。通过精神民俗的书写,挖掘国人丰富的精神世界,探寻中国社会变迁的轨迹和未来走向。从本土视角出发,关注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真实问题,才能在内在发展历史与社会关系吻合的基础上加深地方的独特性,形成更开放多元的地方认同感,保证地方在与全球产生联系互动时不被征服,从而最终构建全球地方感抵御全球化对地方文化的冲击。
《大漠祭》 中的精神民俗书写,不仅具有深厚的文学价值,还包含了重要的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为文化传承和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在地方开放、联系、流动的后全球化时代下,注入民俗意识进行多元本土文化的阐释,并“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22],更有利于中国与世界对话,将本土话语融入世界文化中,在展示中华民族精神文化多样性和独特性的同时,共同参与世界多元话语体系构建。
注释:
[1]彭飞:《增强各族群众的中华文化认同》,《人民日报》2024年 6 月 11 日。
[2][3][6][9][12][13][16][20]雪漠:《大漠祭》,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 年版,第 1 页、第 1 页、第 14 页、第 264—265 页、第265 页、第 420—421 页、第 1 页、第 4 页。
[4]雪漠:《文学朝圣(上卷)》,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3 年版,第285 页。
[5]雪漠:《前言后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243 页。
[7]钟敬文:《民俗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5 页。[8][14][15]〔瑞士〕荣格著,姜国权译:《人、艺术与文学中的精神》,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11 年版,第 106 页、第 121 页、第112—113 页。
[10]〔英〕詹姆斯·乔治·弗雷泽著,蘑菇姑姑译:《金枝》,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0 年版,第 18 页。
[11]乌丙安:《民俗遗产评论》,长春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71页。
[17]贺宾:《民间伦理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8 年版,第120 页。
[18]〔英〕多琳·马西著,王爱松译:《保卫空间》,江苏教育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80 页。
[19]陈勤建:《文艺民俗学》,上海文化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页。
[21]陈晓明:《剩余的想象:九十年代的文学叙事与文化危机》,华艺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30 页。
[22]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 441 页。
——刊于《文艺论坛》2024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