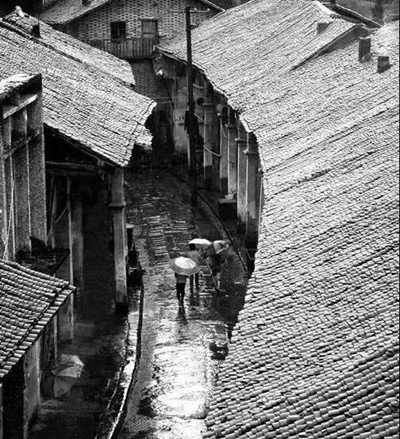
汪曾祺:七里茶坊
这样的天,凡是爱喝酒的都应该喝两盅,可是上哪儿找酒去呢?
吃了莜面,看了一会书,坐了一会,想了一会心事,照例聊天。
像往常一样,总是老乔开头。因为想喝酒,他就谈起云南的酒。市酒、玫瑰重升、开远的杂果酒、杨林肥酒……“肥酒?酒还有肥瘦?”老刘问。
“蒸酒的时候,上面吊着一大块肥肉,肥油一滴一滴地滴在酒里。这酒是碧绿的。”
“像你们怀来的青梅煮酒?”
“不像。那是烧酒,不是甜酒。”
过了一会,又说:“有点像……”
接着,又谈起昆明的吃食。这老乔的记性真好,他可以从华山南路、正义路,一直到金碧路,数出一家一家大小饭馆,又岔到护国路和甬道街,哪一家有什么名菜,说得非常详细。他说到金钱片腿、牛干巴、锅贴乌鱼、过桥米线……“一碗鸡汤,上面一层油,看起来连热气都没有,可是超过一百度。一盘子鸡片、腰片、肉片,都是生的。往鸡汤里一推,就熟了。”
“那就能熟了?”
“熟了!”
他又谈起汽锅鸡。描述了汽锅是什么样子,锅里不放水,全凭蒸汽把鸡蒸熟了,这鸡怎么嫩,汤怎么鲜……老刘很注意地听着,可是怎么也想象不出汽锅是啥样子,这道菜是啥滋味。
后来他又谈到昆明的菌子:牛肝菌、青头菌、鸡土从①,把鸡土从夸赞了又夸赞。
“鸡土从?有咱这儿的口蘑好吃吗?”
“各是各的味儿。”
老乔百刂话的时候,小王一直似听不听,躺着,张眼看着房顶。忽然,他问我:
“老汪,你一个月挣多少钱?”
我下放的时候,曾经有人劝告过我,最好不要告诉农民自己的工资数目,但是我跟小王认识不止一天了,我不想骗他,便老实说了。小王没有说话,还是张眼躺着。过了好一会,他看着房顶说:
“你也是一个人,我也是一个人,为什么你就挣那么多?”他并没有要我回答,这问题也不好回答。
沉默了一会。
老刘说:“怨你爹没供你书①。人家老汪是大学毕业!”
老乔是个人情练达的人,他捉摸出小王为什么这两天老是发呆,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说:“小王,你收到一封什么信,拿出来我看看!”
前天三套大车来拉粪水的时候,给小王捎来一封寄到所里的信。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小王搞了一个对象。这对象搞得稍微有点离奇:小王有个表姐,嫁到邻村李家。李家有个姑娘,和小王年貌相当,也是高小毕业。这表姐就想给小姑子和表弟撮合撮合,写信来让小王寄张照片去。照片寄到了,李家姑娘看了,不满意。恰好李家姑娘的一个同学陈家姑娘来串门,她看了照片,对小王的表姐说:“晓得人家要俺们不要?”表姐跟陈家姑娘要了一张照片,寄给小王,小王满意。后来表姐带了陈家姑娘到农科所来,两人当面相了一相,事情就算定了。农村的婚姻,往往就是这样简单,不像城里人有逛公园、轧马路、看电影、写情书这一套。
陈家姑娘的照片我们都见过,挺好看的,大眼睛,两条大辫子。
小王收到的信是表姐寄来的,催他办事。说人家姑娘一天一天大了,等不起。那意思是说,过了春节,再拖下去,恐怕就要吹。
小王发愁的是:春节他还办不成事!柴沟堡一带办喜事倒不尚铺张,但是一床里面三新的盖窝,一套花直贡呢的棉衣,一身灯芯绒裤袄、绒衣绒裤、皮鞋、球鞋、尼龙袜子……总是要有的。陈家姑娘没有额外提什么要求,只希望要一枚金星牌钢笔。这条件提得不俗,小王倒因此很喜欢。小王已经作了长期的储备,可是算来算去还差五六十块钱。
老乔看完信,说:
“就这个事吗?值得把你愁得直眉瞪眼的!叫老汪给你拿二十,我给你拿二十!”
老刘说:“我给你拿上十块!现在就给!”说着从红布肚兜里就摸出一张十元的新票子。
问题解决了,小王高兴了,活泼起来了。
于是接着瞎聊。
从云南的鸡土从聊到内蒙的口蘑。说到口蘑,老刘可是个专家。黑片蘑、白蘑、鸡腿子、青腿子……“过了正蓝旗,捡口蘑都是赶了个驴车去。一天能捡一车!”
不知怎么又说到独石口。老刘说他走过的地方没有比独石口再冷的了,那是个风窝。
“独石口我住过,冷!”老乔说,“那年我们在独石口吃了一洞子羊。”
“一洞子羊?”小王很有兴趣了。
“风太大了,公路边有一个涵洞,去避一会风吧。一看,涵洞里白糊糊的,都是羊。不知道是谁的羊,大概是被风赶到这里的,挤在涵洞里,全冻死了。这倒好,这是个天然冷藏库!俺们想吃,就进去拖一只,吃了整整一个冬天!”
老刘说:“肥羊肉炖口蘑,那叫香!四家子的莜面,比白面还白。坝上是个好地方。”
话题转到了坝上。老乔、老刘轮流说,我和小王听着。老乔说:坝上地广人稀,只要收一季莜麦,吃不完。过去山东人到口外打把势卖艺,不收钱。散了场子,拿一个大海碗挨家要莜面,“给!”一给就是一海碗。说坝上没果子。怀来人赶一个小驴车,装一车山里红到坝上,下来时驴车换成了三套大马车,车上满满地装的是莜面。坝上人都豪爽,大方。吃起肉来不是论斤,而是放开肚子吃饱。他说坝上人看见坝下人吃肉,一小碗,都奇怪:“这吃个什么劲儿呢?”他说,他们要是看见江苏人、广东人炒菜:几根油菜,两三片肉,就更会奇怪了。他还说坝上女人长得很好看。他说,都说水多的地方女人好看,坝上没水,为什么女人都长得白白净净?那么大的风沙,皮色都很好。他说他在崇孔县看过两姐妹,长得像傅全香。傅全香是谁,老刘、小王可都不知道。
老刘说:坝上地大,风大,雪大,雹子也大。他说有一年沽源下了一场大雪,西门外的雪跟城墙一般高。也是沽源,有一年下了一场雹子,有一个雹子有马大。
“有马大?那掉在头上不砸死了?”小王不相信有这样大的雹子!
老刘还说,坝上人养鸡,没鸡窝。白天开了门,把鸡放出去。鸡到处吃草籽,到处下蛋。他们也不每天去捡。隔十天半月,挑了一副筐,到处捡蛋,捡满了算。他说坝上的山都是一个一个馒头样的平平的山包。山上没石头。有些山很奇怪,只长一样东西。有一个山叫韭菜山,一山都是韭菜;还有一座芍药山,夏天开了满满一山的芍药花……老乔、老刘把坝上说得那样好,使小王和我都觉得这是个奇妙的、美丽的天地。
芍药山,满山开了芍药花,这是一种什么景象?
“咱们到韭菜山上掐两把韭菜,拿盐腌腌,明天蘸莜面吃吧。”小王说。
“见你的鬼!这会会有韭菜?满山大雪!——把钱收好了!”
聊天虽然有趣,终有意兴阑珊的时候。天已经很黑了,房顶上的雪一定已经堆了四五寸厚了,摊开被窝,我们该睡了。
正在这时,屋门开处,掌柜的领进三个人来。这三个人都反穿着白茬老羊皮袄,齐膝的毡疙瘩。为头是一个大高个儿,五十来岁,长方脸,戴一顶火红的狐皮帽。一个四十来岁,是个矮胖子,脸上有几颗很大的痘疤,戴一顶狗皮帽子。另一个是和小王岁数仿佛的后生,雪白的山羊头的帽子遮齐了眼睛,使他看起来像一个女孩子。——他脸色红润,眼睛太好看了!他们手里都拿着一根六道木二尺多长的短棍。虽然刚才在门外已经拍打了半天,帽子上、身上,还粘着不少雪花。
掌柜的说:“给你们做饭?——带着面了吗?”
“带着哩。”
后生解开老羊皮袄,取出一个面口袋。——他把面口袋系在腰带上,怪不道他看起来身上鼓鼓囊囊的。
“推窝窝?”
高个儿把面口袋交给掌柜的:“不吃莜面!一天吃莜面。你给俺们到老乡家换几个粑粑头吃①。多时不吃粑粑头,想吃个粑粑头。把火弄得旺旺的,烧点水,俺们喝一口。——没酒?”
“没。”
“没咸菜?”
“没。”
“那就甜吃!”②
老刘小声跟我说:“是坝上来的。坝上人管窝窝头叫粑粑头。是赶牲口的,——赶牛的。你看他们拿的六道木的棍子。”随即,他和这三个坝上人搭口格起来:“今天一早从张北动的身?’“是。——这天气!”
“就你们仨?”
“还有仨。”
“那仨呢?”
“在十多里外,两头牛掉进雪窟窿里了。他们仨在往上弄。俺们把其余的牛先送到食品公司屠宰场,到店里等他们。”“这样天气,你们还往下送牛?”
“没法子。快过年了。过年,怎么也得叫坝下人吃上一口肉!”不大一会,掌柜的搞了粑粑头来了,还弄了几个腌蔓菁来。他们把粑粑头放在火里烧了一会,水开了,把烧焦的粑粑头拍打拍打,就吃喝起来。
我们的酱碗里还有一点酱,老乔就给他们送过去。“你们那里今年年景咋样?”
“好!”高个儿回答得斩钉截铁。显然这是反话,因为痘疤脸和后生都噗嗤一声笑了。
“不是说去年你们已经过了‘黄河’了?”
“过了!那还不过!”
老乔知道他话里有话,就问:“也是假的?”
“不假。搞了‘标准田’。”
“啥叫‘标准田’?”
“把几块地里打的粮算在一起。”
“其余的地?”
“不算产量。”
“坝上过‘黄河’?不用什么‘科学家’,我就知道,不行!”老刘用了一个很不文雅的字眼说:“过‘黄河’,过的个河吧?”老乔向我解释:“老刘说的是对的上的土层只有五寸,下面全是石头。坝上一向是广种薄收,要求单位面积产量,是主观主义。”
痘疤脸说:“就是!俺们和公社的书记说,这产量是虚的。他人家说:有了虚的,就会带来实的。”
后生说:“还说这是:以虚带实。”
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以虚带实”是这样的解释的。
高个儿沉重地叹了一口气:“这年月!当官的都说谎!”老刘接口说:“当官的说谎,老百姓遭罪!”
老乔把烟口袋递给他们:“牲畜不错?”
“不错!也经不起胡糟践。头二年,大跃进,大炼钢铁,夜战,把牛牵到地里,杀了,在地头架起了大锅,大块大块煮烂,大伙儿,吃!那会吃了个痛快;这会,想去吧!——他们仨咋还不来?去看看。”
高个儿说着把解开的老羊皮袄又系紧了。
痘疤脸说:“我们俩去。你啦①就甭去了。”
“去!”
他们和掌柜的借了两根木杠,把我们车上的缆绳也借去了,拉开门,就走了。
听见后生在门外大声说:“雪更大了!”
老刘起来解手,把地下三根六道木的棍子归在一起,上了炕,说:
“他们真辛苦!”
过了一会,又自言自语地说:“咱们也很辛苦。”
老乔一面钻被窝,一面说:“中国人都很辛苦啊!”
小王已经睡着了。
“过年,怎么也得叫坝下人吃上一口肉!”我老是想着大个儿的这句话,心里很感动,很久未能入睡。这是一句朴素、美丽的话。
半夜,朦朦胧胧地听到几个人轻手轻脚走进来,我睁开眼,问:
“牛弄上来了?”
高个儿轻轻地说:
“弄上来了。把你吵醒了!睡吧!”
他们睡在对面的炕上。
第二天,我们起得很晚。醒来时,这六个赶牛的坝上人已经走了。
一九八一年五月十一日写成
【汪曾祺短篇《七里茶坊》首刊于1981年第5期《收获》】
雪漠文化网,智慧更清凉!www.xuemo.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