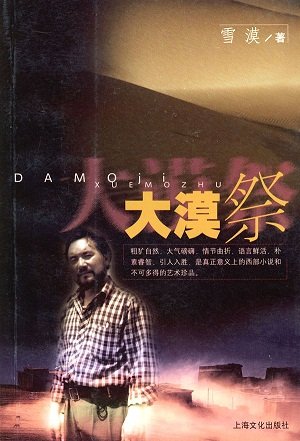
生命是一根绳子——关于《大漠祭》的对话
◇记者:自本报连载《大漠祭》以来,读者反响强烈,纷纷向我们寻问《大漠祭》的一些情况。今天,我们专门谈一些读者关心的问题。
首先,请你简单谈一谈《大漠祭》的写作过程。
●雪漠:1988年初,中篇小说《长烟落日处》完成之后,我就写了一部反映西部农民生活的小说,篇幅不长,也取名为《大漠祭》,用的是《长烟落日处》的那种浓缩笔法。完成之后,不满意;又写了一遍,仍不满意;后来,写了废,废了写,说不清写了多少遍。终于发现,用《长烟落日处》的那种笔法,很难写出优秀的长篇小说。我毅然抛弃了我写得很顺手的笔法,重新练了五年笔。这是个单调乏味的过程,十分艰苦。练笔的同时,我开始跑遍武威,深入生活。等我练好了笔,我对武威了解程度,也几乎等同于自己的家了。30岁那年,在我生日那天,我剃光了头发和胡须,离开了家,躲到了一个地方,开始了几乎与世隔绝的四年。每天,由我的妻子送一次饭。此外,不见任何人,从而完成了作品的主要部分。此后几年,我利用业余时间,进行修改。前前后后,大约用了十二年时间,原名《老顺一家》。
发表的《大漠祭》,只是《老顺一家》的一部分,原稿是一部大长篇,一百多万字。发表时,为方便读者购买,把大长篇改成了三部相对独立的长篇。第二部《猎原》,和第三部《西夏的岩窟》,已基本成型,正在修改。
◇记者:写作《大漠祭》时,你在哪儿工作?
●雪漠:刚开始写《大漠祭》时,我在乡下一所偏僻闭塞的小学任教。如果我一直待在那个小学,是很难完成后来的《大漠祭》的。因为,以一个小学教师的目光和见识,不可能对凉州文化和凉州百姓的生存状态进行全面而准确的把握。后来,当时的武威市教委主任蒲龙破格把我从小学调到了教委,基本没安排具体事务,并为我提供了下乡体验生活的方便和大量的创作时间。没有他的帮助,就没有今天的我。借此机会,我向蒲龙和帮助过我的人致谢。
我在武威市教委工作了近十年时间,从而完成了《大漠祭》的主要部分。后来,我到武威市东关小学任小学教师。教委和学校领导也为我提供了许多方便。
◇记者:你如何安排自己的写作时间?
●雪漠:每天早晨,我3点多钟起床。若是上班,就写到7点半左右;若是不上班,我就一直写到中午12点,下午处理一些事务和搞一些采访。夜里,重点读书。
◇记者:请你谈谈你的家庭。
●雪漠:我的父母是农民,年过六旬,还种着八亩地,养活着我死去的弟弟留下的儿子。我的工资不高,基本上都资助了父母,自己则利用周末和假期搞些家教,生活上也能过得下去。妻子没有工作,除做家务外,还为我打字,整理些写作资料。她为我做出了很大的牺牲,是我生活上和创作上最有利的助手。
◇记者:能否谈谈《大漠祭》出版时的情况?
●雪漠:《老顺一家》完稿之后,我首先寄给了上海文化出版社,他们马上表示出极大的热情,按总编辑郝铭鉴的说法,他一直想找一部能够“留下去”的书,但一直没有找到。见到《老顺一家》原稿,他说他感到了“意外的惊喜”。从责任编辑的初审,经过编辑室主任、副总编辑,到总编辑终审定稿,前后不足一月时间。两位总编辑是利用五一节放假的七天时间完成审稿的:总编辑郝铭鉴是在92岁高龄的母亲的病榻前审稿;副总编辑戴俊的女儿正要考大学,他是在接送女儿补习的路灯下完成审稿的。终审只用了七天时间,他们就答应出版,并请我去上海改稿。
◇记者:听说,出版社还邀请了你的父母,参加了上海的“《大漠祭》新闻发布及研讨会”?
●雪漠:是的。在上海,这是破天荒的。我本想在收到《大漠祭》的稿费后,请父母去上海等地转转,了却我的一个心愿。因为父母不识字,无法读我的小说,但总可以通过我的努力,叫他们读外面的世界。郝总编看了《大漠祭》“后记”后,决定由出版社出钱,请我的父母去上海,既帮我了却一个心愿,也向西部农民父老表达一点心意。出版社派吴金海老师陪我和父母去上海外滩、城隍庙、杭州西湖、南京中山陵等景点旅游,还请他们住了高级宾馆,品尝了各种南方小吃。因为,此前,父母的最大奢望是,在我领到稿费时,请他们尝尝凉州街头的那些小吃。出版社做得更好,请他们尝了许多南方名吃。
后来,上海电视台、《文汇报》等几十家新闻媒体都报道了《大漠祭》出版情况,却丝毫没有提到出版社提供经费,邀请我父母的事。出版社也只字不提,仿佛他们觉得帮助一位作者了却心愿是他们应尽的义务。同时,我还得到了上海寻常市民的许多帮助。我很是感动,才向上海市委书记黄菊寄去的感谢信并赠送了作品。黄菊书记批复《文汇报》处理。《文汇报》又安排了追踪报道。没想到,这成了后来的一个热点新闻,除上海连篇累牍地报道外,北京、南京等地的新闻媒体也纷纷报道了。
◇记者:读《大漠祭》,除感受到那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外,还有一种浓郁的文化气息。你能否谈谈家乡文化对你的影响?
●雪漠:我很系统地研究了家乡独有的打着“凉州”烙印的佛道文化。这些文化,是敦煌学和凉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被“凉州”异化了的佛道文化,影响了那儿的民俗风情和民众心态。不研究它们,你很难进入老百姓的灵魂。对它们,我进行过系统的研究和考察。它们带给我的,不仅仅是创作上的收获,还有一种豁达的胸怀和利众的精神。像孔繁森的精神,就是佛教所提倡的“菩萨”精神,所以孔繁森被藏族老百姓称为“菩萨”。严格说来,佛教不仅仅是一种信仰和文化,更是一种精神,一种利众的精神。我的作品,无论大小,都有一种隐在文字背后的东西。一些评论家称为“大气”。一个作家,如果人格修炼达不到一定层次,不会有那“气”。他可以文字玩得非常好,但就是没有那种“气”。佛道文化,首先给我的,是精神境界上的升华,和一种悲天悯人的胸怀,。我的文字都很朴素,都很淡,但它又不是一般的淡。它的背后,有一种我独有的东西。
◇记者:从《大漠祭》“后记”中得知,你的房间里有一个死人头骨。请问,这有何象征意义?
●雪漠:这头骨,代表着“死亡”。每当我看到它,仿佛就听到它叫:“死亡!死亡!”它提醒我,死亡随时随地,都会降临到我的头上。所以,我每天给自己打的考勤,是以小时来计算的。那头骨老提醒我:珍惜生命。
生命是一根绳子,就那么一点长度,浪费一截,就少一截。闲事上用多了,正事上就不够用了。我的好多朋友和亲戚都说我有些不近人情。原因是我从来不愿在应酬上多花时间。这源于我对生命的感悟。好多人生悲剧,就因为不珍惜生命。谁明白了这一点,其人生无疑会更有质量。
那头骨,是我的警枕,像司马光的那个警枕一样。
◇记者:你在《大漠祭》“后记”中,特别地谈到了几次上海之行。上海之行,是否真像你所说的,对你的创作有较大影响?
●雪漠:有很大影响。当我站在上海外滩,反思甘肃,反思武威的时候,我感受到的,是一种灵魂的颤栗。这颤栗,让我在艺术上有一种新的升华。毕竟,我在武威那个小地方生活了太长的时间。那儿的生活,为我提供了大量的创作素材,但也相应地限制了我的思维和视野。去了几次上海,东西部文化的巨大反差,对我的灵魂撞击比较大,使我胸襟大阔,眼界顿开,也会在艺术上相映地反映出来。这一点,你会在后面的作品中看到。
《大漠祭》出版之后,我奇怪地发现,自己竟然没啥惊喜。原因很简单,我去了上海,看了那么多的“大”书和“大”人,觉得自己写本书,实在没啥了不起。真的,在上海,尤其是面对虚怀若谷的郝铭鉴先生,我每每为以前的张扬无地自容。
好在我对家乡有太深的了解,也很有感情。当我把这种感情说出来的时候,一些文人都认为我在说假话。其实不然,一部作品要是没有爱,那是十分苍白的。而连家乡都不爱的人,是不可能成为优秀作家的。
甘肃的文化特别厚实,只“敦煌学”就叫世界目瞪口呆了。此外,还有包括“凉州文化”在内的许多文化遗产没被发现,更没有被挖掘。外面对甘肃的了解很不够。甘肃人对自己的了解也很不够,需要一大批甘肃的文化人去努力地劳动,发掘这儿的文化,去努力地向这个世界宣传甘肃的文化。
西部大开发,最应该开发的,是西部人的心灵。最应该开发的,是西部的文化。
我会用我的毕生精力来写这块土地,要是因了我的努力,因了我和许多甘肃同行的努力,使外面的世界了解了甘肃,并能为甘肃的老百姓带来些新的东西,也算没白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