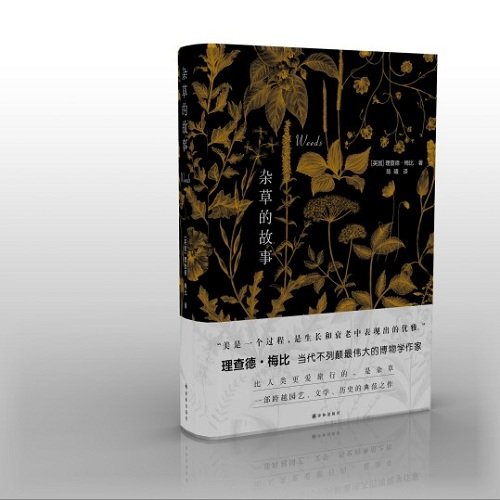

△ 《杂草的故事》作者理查德•梅比
比人类更爱旅行的,是杂草
从古至今,哪里有人类的足印,哪里便是杂草的温床。充满野性的植物总是出其不意地越过自然与文明的边界,与我们比邻而居:欧洲的蓟草躲在压舱石下漂洋过海,从殖民者的车辙中探头张望新大陆;虞美人在古老的土层里沉睡,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炮火让它们重见天日;来自中国的醉鱼草被火车搅起的气流牵引着,沿着铁路在英国一路扩散……
英国作家理查德•梅比在《杂草的故事》中就为我们描绘了以上奇妙的旅行。杂草是某种类型的植物还是一种人类的思维?它们是生物品种还是文化的产物?它们为何存在?如果没有它们,世界将会怎样?……这本书讲述了四处流浪的杂草是如何被定义、被诠释、被限制和被不公平地对待,又是如何冲破文明的边界并影响人类对自然的看法。

△ 蓝铃花(Hyacinthoides non-scripta)
在杂草的定义中,最为人所熟知也是最简单的一种当属“出现在错误地点的植物”,也就是说,杂草长在了你本希望长出其他植物或者根本不希望长出植物的地方。这个定义还算贴切,也能解释一些事情。比如英国蓝铃花本属于森林,可一旦到了花园里,它们往往会疯狂地长满整个园子,变成招人烦的杂草;而来自地中海地区的西班牙蓝铃花一旦从花园逃逸,就会变成可怕的入侵者,进入当地的树林,威胁到当地“真正”的蓝铃花。但这些例子中的“适宜”与否有许多微妙之处,并不是简单的一个生物归属地就可以解释的。花园是私人领地,蓝铃花入侵时人们会感觉自己那份私密仿佛也被入侵;同样,入侵到英国的西班牙蓝铃花可能会激起你的民族主义情怀,甚至激发出一种审美上的爱国主义:看哪,土生土长的蓝铃花多么柔软,它们弯曲的花茎充满凯尔特风情,与不列颠的树林如此协调,哪像西班牙的花朵那样唐突,花茎弯得也不像样子。

△ 翼蓟(Cirsium arvense)
杂草的判定标准也可能随时间发生戏剧性的变化。一名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的早期移民就还清楚地记得,一种与他们一起来澳大利亚的苏格兰植物,是如何从故国情怀的纪念品变成非法入侵者的:“有一天我们看见一株翼蓟长在一根圆木旁边,离马厩不远——很明显是有种子从马饲料中漏出来,在这里生根发芽了……我们把它用报纸小心翼翼地包起来,并用石头压住。没几天工夫,这株小草就长得十分漂亮,我们四处向人炫耀,自豪得不行。可当时谁也没想到,二十多年以后这种来自苏格兰的蓟草会遍布整片大陆,而且这种草成了有害物种,一些郡县和地区甚至需要设立特殊法案,以强制性地从私人空间中拔除它们。”
人类时常太过狭隘,倘若有什么植物妨碍了我们的计划,或是扰乱了我们干净齐整的世界,人们就会给它们冠上杂草之名。很多时候,杂草的定义都是从人类角度出发的。它们是妨碍了人类的植物。它们抢夺农作物的营养,破坏园艺设计师精心的布置,不按我们的行为准则生存……可如果你本没什么宏伟大计或长远蓝图,它们就只是清新简单的绿影,一点也不面目可憎。

△ 宽叶羊角芹(Aegopodium podagraria)
有些杂草的定义,着重表达了杂草在文化上的其他不适宜性或不利性。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倾向于从可用性的角度出发,将杂草简单地定义为“优点还未被发现的植物”。这个定义给得既慷慨又友善,暗示即便是已被定罪的植物也还有翻身的可能。但就像藜的故事告诉我们的那样,有没有优点全在于当时的人们如何看待。有许多植物曾一度被认为是有用有益的,可一旦这些益处过时了,或是人们发现享受这些益处需要付出不小的代价,它们便会立即失宠。罗马人把宽叶羊角芹引入英国,本是冲着它既有缓解痛风的药效,又可当作食物。但两千年转眼过去,经过几场医学革命的洗礼,这种植物再无药用价值,却变成了英国花圃中最顽固难除、惹人厌恶的杂草。

△ 毒漆藤(Rhus radicans)
杂草另一个不受欢迎和饱受诟病的特征是毒性。美国最臭名昭著的杂草是毒漆藤,尽管它造成的经济损失远不是杂草中最多的,但它的形象已经随着杰瑞•莱贝尔和迈克•斯托勒制作的歌曲而深入人心。这对搭档曾制作过几首以杂草为主题的摇滚歌曲,如托尼•乔•怀特原唱、猫王多次翻唱的《做野菜沙拉的安妮》(“Polk Salad Annie”)。在关于毒漆藤的那首歌中,毒漆藤被比作一个惯耍心机的女人,她会“深入你皮肤”,然后“你会需要一片海洋/炉甘石洗剂的海洋”。实际上,炉甘石洗剂对皮肤接触毒漆藤后的症状没什么用处。不管你跟这种植物的接触多么短暂,接触的地方都会立刻变红。只要一片破损的叶子轻轻扫过你的皮肤,噩梦般的体验就会随之而来。皮肤会红肿、起水疱,并且无法控制地发痒。如果你对这种毒素敏感(通常来说胖人比瘦人更容易敏感),你的发热和水肿可以持续好几天。你不需要跟毒漆藤直接接触,一次握手,一条毛巾,甚至只是不小心摸到刚从树林里回来的人所穿的鞋,就足以染上“漆酚接触性皮炎”。即使你足不出户,只要窗外的篝火里有几片毒漆藤的叶子,飘过来的轻烟也足以让你染上这种皮炎。

△ 常春藤(Hedera helix)
有些植物被贬为杂草,只是因为我们在道德层面不赞许它们的行为。寄生就是个十分昭著的恶名,寄生者从其他植物那里夺取营养,罔顾寄主的安危。常春藤更是冤枉,明明不是寄生植物却被人诬为寄生植物。它们依附在树上单纯是为了获取支撑,并未从树木身上拿走半点营养。常春藤若是长得过于茂盛,它们的重量确实可能给树木造成伤害,但这个平淡的事实哪有树汁吸食者、植物吸血鬼来得更有话题,更适合做妖魔化的基础呢。
《杂草的故事》作者理查德•梅比被《泰晤士报》誉为当代不列颠最伟大的博物学作家,他有一种令人羡慕的本领,既能正襟危坐以写史,又可像个精灵般潜入林间,把我们也一起带到植物身边,亲眼看着它们的颜色、光影和纹理。
在理查德•梅比眼中,杂草并非农夫和园艺爱好者的敌人,而是机敏顽强的漫游者,是年年岁岁与我们照面的邻人,是野生与驯养交汇处的游民,是饱受严重污染摧残的大地向人类发出的警示。
杂草并不是寄生虫,因为即便没有了人类它们一样可以生存,但我们就像它们的绝佳拍档,只要有我们在侧,它们就能发挥出最好水平。我们砍伐森林,我们刨地挖土,我们耕种,我们丢弃富含营养成分的垃圾——无论我们对脚下的土地做什么,它们总会跑来添情增趣。它们从耕地里冒头,它们在战场边发芽,它们点缀在停车场里,它们不识趣地挤进绿草带。它们利用着我们的运输系统、我们对烹饪美食的热情、我们对包装分类的痴迷。最重要的是,它们利用了我们搅乱世界、打破所有常规的时机。
假如告诉你,如今世界上杂草生长最繁盛的地方正是那些除草最卖力的地方,你可能会觉得这是句废话;但这句废话应该引起我们的思考,除草是不是令杂草越除越多?

△ 绿草带
雪漠文化网,智慧更清凉!www.xuemo.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