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这些东欧作家是如何传播、感染并且影响中国的。
记忆中的东欧文学图谱

上星期去世的波兰诺奖女诗人希姆博尔斯卡

捷克首都布拉格的“赫拉巴尔纪念墙”,绘有赫氏及其生前最喜欢的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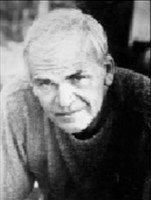

昆德拉与其名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该书曾被翻译为多个译名

赫拉巴尔的《我曾侍候过英国国王》
波兰作家斯坦尼斯罗·罗姆曾有过一个著名的隐喻,在遥远星球上的某个国家,居民们被迫像鱼一样生活在水下,嘴里吐出的泡是唯一的谈话。官方说,水下生活才是最美好的,浮出水面呼吸就是犯罪。而所有的居民都患上风湿病,梦想着有一天过上岸上的生活……
而20世纪末大事记之一,就是这群水下的人们浮出水面呼吸——冷战的铁幕撤下,东欧解冻,岸上的生活来临了——东欧诸国迎来了民族自决与思想解禁。
“东欧文学”随着带有冷战色彩的“东欧”一道,正成为过去式。然而,当代文学史却注定无法忘记——在这块弹丸之地,曾经的东欧七国,捷克、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前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如何向世界奉献了一批当代思想学术史独有的概念:流亡作家,地下写作,心灵献祭。一大批优秀作家们以不屈的个人抗争,深刻的历史反思,以及对自由的强烈追求,赢得了世界性赞誉,其中不乏优秀的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与获得者。
最近重入视野的是花城出版社的“蓝色东欧”丛书。作为现当代东欧文学一次整体性的巡礼,入选“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七国文学作品中的近百部佳作,将借此机缘再次呈现在中国读者面前。
回顾20世纪80年代,有感于与这一地区微妙相似的历史经验和社会状况,国内的翻译者们开始大量翻译东欧文学作品。捷克的塞弗尔特、赫拉巴尔、伊凡·克里玛、哈维尔、昆德拉;波兰的米沃什、希姆博尔斯卡、舒尔茨、贡布罗维奇、斯坦尼斯拉夫·莱姆;匈牙利的凯尔泰斯,塞尔维亚的帕维奇;罗马尼亚的诺曼·马内阿、赫塔·米勒等等。其中,上星期去世的波兰诺奖女诗人希姆博尔斯卡,唤起了最新一波的对东欧文学的记忆。
这些东欧作家是如何传播、感染并且影响中国的。记者访问了多位译者和作者,从他们的东欧文学情结中,可窥一二。
捷克 昆德拉在中国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后,所有抱有文学梦的中国年轻人,都很难避开两个外国人的启示。一个是南美的马尔克斯,另一个是捷克斯洛伐克的,被称为流亡者的米兰·昆德拉。
昆德拉在中国,首先是一张悲情脸,流亡法国,一度不为本国认可。其次是一个营销奇迹。所有昆德拉作品在华各种销量加起来有上千万册。仅《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现译《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一部就高达数百万册。
在1985年,美籍学者李欧梵在武汉某学报上首次向中国正式介绍昆德拉时,还并未引起什么注意。1986年,刚取得南京大学硕士学位的景凯旋从一位美国访问学者那里得到了《为了告别的聚会》,作者昆德拉。一直受精英文学观和欧陆美学教育的他,从索尔仁尼琴“人性向上的沉重”中走出来,第一次领略到昆德拉对价值失落的反讽,同时不乏深刻的批判,顿时觉得耳目一新。为了能让更多人看到,他开始为这本书的翻译工作而奔走。
几乎与此同时,赴美访问归来的作家韩少功开始关注并翻译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听说了景凯旋的事情,就反映给作家出版社,韩景二人先后把手稿带到了北京,其后,《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与《为了告别的聚会》陆续面世。昆德拉真正来到了中国,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景凯旋历经波折,又翻译了《玩笑》、《生活在别处》等作品。
90年代初,刚经历过短暂风波的中国人在昆德拉式的调侃与哲理中,似乎找到了某种命运相惜和寄托,所以,“生活在别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媚俗”成为流行语。中国文学思想界言必称昆德拉。
在90年代末,知识界还有一场“昆德拉、哈维尔之争”。捷克剧作家哈维尔坚持留在捷克,昆德拉移民法国,哈维尔坐过牢,昆德拉虽受过监控,但没坐过牢。当时有一篇文章《我们选择什么?我们承担什么?》认为哈维尔比昆德拉更有担当,更有牺牲精神,昆德拉是逃避的犬儒主义者。景凯旋却认为,昆德拉并非犬儒,对集权主义和西方价值观的思考都是深刻的,学界也发现了这一价值。
不管怎样,变化是巨大的,2002年,上海译文出版社买下昆德拉全部13部著作的版权,根据法文版重新出版。可以说,是昆德拉最先使得中国人将目光转向捷克与东欧文学。
捷克 安贫者赫拉巴尔
和他声名赫赫的捷克同胞昆德拉相比,赫拉巴尔是一位被中国大陆忽略了太久的伟大作家。为更好感受作家的生存状态,已两赴捷克的龙冬不止一次表达了这样的感慨。
1993年,还在中国青年出版社任编辑的龙冬偶然从《世界文学》第2期上读到了赫拉巴尔的《过于喧嚣的孤独》、两个短篇、一段创作谈,译者杨乐云。不同于昆德拉浓厚的政治意味,龙冬从赫拉巴尔那里读到了生活的趣味、幽默和更为宽泛的思考。“十几年前,捷克的一个汉学家访问我,问为什么要翻译赫拉巴尔,我说,我就想让中国的知识分子们知道,人家是怎样对待生活、对待写作的。如何把生活和写作结合的。”
彼时,龙冬对捷克文学还毫无概念,直到2003年第一次去捷克时,只有赫拉巴尔本人是让龙冬坚持下去的唯一理由。这名出身与教育都良好的作家一生坎坷,安贫乐道,49岁才正式出版了第一本书——《底层的珍珠》,一生都坚持了对底层群体的欣赏和热爱,描写底层人民的真实生活。“他笑着看卓别林,在艰辛的生活里发现乐趣。”有过底层生活体验的龙冬对赫拉巴尔倍感亲切。他于2008年2010年两赴捷克,去了作家出身地和写作的小酒馆,只为了更好地体验赫拉巴尔的生存状态。
引进赫拉巴尔的过程并不顺畅,直到1997年中国青年出版社才具体操作引进事宜,其后为翻译和版权购买又花了3年,到2003年1月才推出《过于喧嚣的孤独》和《我曾侍候过英国国王》。次年5月,又推出另五本赫拉巴尔作品。《赫拉巴尔精品集》成为世界上首部赫拉巴尔作品中译本。
龙冬亲睹改变的悄悄发生,在出版赫拉巴尔第一部稿子前,他在网上百度“赫拉巴尔”,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十条,而如今,关于赫拉巴尔的报道已如海洋。2007年,赫拉巴尔逝世十周年纪念会,聚集在现场的粉丝遍布了知识出版界和普通人群体。

塞尔维亚作家帕维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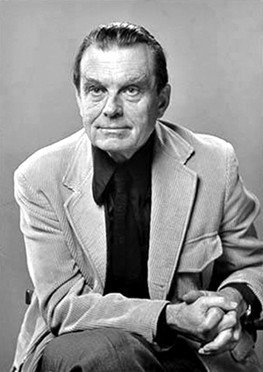
波兰诗人米沃什

罗马尼亚裔德国诗人赫塔·米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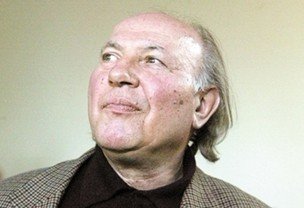
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

帕维奇小说《哈扎尔辞典》

米沃什《诗的见证》

10卷本《赫塔·米勒文集》之《呼吸秋千》

凯尔泰斯的小说《英国旗》
塞尔维亚 帕维奇与《马桥辞典》
1996年,较早把目光转向东欧文学的作家韩少功创作上先人一步,《马桥辞典》的出版刷新了写作范式,(2010年借此获得了第二届纽曼文学奖),还引发了一段公案。学者张颐武在其出版后不久,指责韩少功抄袭了当时尚未出版的一本译作,闹上公堂,最终韩少功胜诉。该译作就是塞尔维亚作家帕维奇的《哈扎尔辞典》。
帕维奇以奇书《哈扎尔辞典》开辞典式小说先河,1984年出版后获南斯拉夫最佳小说奖。这部包罗万象的小说糅合古今、幻想、梦境与实现,复活了中世纪消失于中欧大地的哈扎尔民族。
7世纪到10世纪,在黑海和里海间的游牧民族哈扎尔人,放弃了原始宗教信仰不久后突然消失,成为史上悬案。帕维奇以深厚人文功底的学者知识背景、雄奇的想象力和后现代主义创作精神,在集权和文化审查的高压下,反思并复活了这段历史,因其历史责任感、勇气和新颖手法,成为堪与博尔赫斯并称的文学大师。
2009年帕维奇逝世,十几年前的公案又被重提。译者之一戴骢表示,《哈扎尔辞典》出版前,只在《外国文艺》于1994年有选译。韩少功的《马桥辞典》除了形式上偶有相似外,内容完全不一样,加上一贯的创作思路深受昆德拉理念的影响,很难说是抄袭。而帕维奇与他的后现代主义却因此为中国读者熟知。
学者张颐武在悼念帕维奇的博文中有一段话,或可反映帕维奇对中国知识界的影响:“通过阅读这部书,我们了解的是一种文化的特殊命运。这种命运是帕维奇的想象,也解放了我们的想象,给读者提供了无限的想象空间,也反思了‘语言’本身的限度和可能。”
波兰 政治延续与多元变化
上世纪60年代,留学生林洪亮离开波兰时,已感受到这片大地的文学新气象。1957年波兰政局解冻,古典主义和现代派的潮流同时在这里涌动。那时,带着一些宝贵的波兰当代文学资料,林洪亮返回祖国。经历了十年动乱,以社科院小语种翻译交流学者的身份重回波兰,时隔近20年,他看到了一个再次解冻的波兰文坛。
彼时,冷战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影响还在——1980年,流亡诗人米沃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波兰出版了获奖诗集《拆散的笔记簿》。由于米沃什1950年就离开祖国,作品被禁,林洪亮此前一直无缘看到他的作品。到了1989年,由诗人绿原首度将这本诗集翻译引进中国,收在漓江出版社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集里。
出版人林贤治读到这本诗集之后深受震撼,尤其是流亡者米沃什严肃的命运反思,深刻的社会批判和自由意识,启发了他日后研究东欧地下文学的兴趣。其后,诗人北塔、西川和张曙光,陆续翻译了《米沃什词典》和《切·米沃什诗选》。其代表作《被禁锢的头脑》即将在今年3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在审美接受方面,林洪亮更偏爱小米沃什12岁的波兰女诗人希姆博尔斯卡,她于199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人因对50年代波兰的政治宣传假话失望,后来的创作跳出了政治性视野,关心哲理、日常生活、人类命运和世界性话题。林洪亮精心收录了她85%的诗作,收在2000年漓江出版社出版的《呼唤雪人》集中。
林洪亮介绍,相比同时代的捷克作家以强烈政治色彩著称,波兰作家创作却更倾向多元。原因是70年代后团结工会出现,工人与知识分子联合。同时,宗教也起了作用。
米沃什在诗歌创作中有对斯大林时代的揭露,希姆博尔斯卡则升级到对越战的关心中去。林贤治则认为波兰民族在创作上有一致的延续性,他们的不屈抗争精神,不管在对政治体制的鞭策上,还是在对自由的追求上,都是世所罕见的。
同样是流亡者的贡布罗维奇则表现出先锋创作理念方面的才华,《费尔迪杜凯》于2003年由译林出版社引进中国。让作家余华爱不释手的布鲁诺·舒尔茨最早在1992年出现在第三期《外国文艺》上,这位在余华眼中可媲美卡夫卡的后现代小说大师,在2009年和2011年,《鳄鱼街》和《肉桂色铺子》分别由新星出版社和浙江文艺出版社引入中国。林洪亮介绍,另一位著名的波兰科幻小说大师斯坦尼斯拉夫·莱姆,目前还没有长篇作品翻译引进国内。
萨米亚特族 东欧文学内核
2010年,一本名为《地下——东欧萨米亚特随笔》的出版物引发了学界关注。编译者景凯旋,筹划者是时任花城出版社编辑的林贤治。林贤治拿到中译本时62岁,但对于东欧知识分子地下写作的关注,已持续了二十多年。
萨米亚特(地下出版物)是前苏联、东欧特有的文化现象,针对书报检查制度而来。其中捷克的萨米亚特最发达。捷克作家们普遍内心经历过乌托邦的幻灭,转而遵循19世纪以来的欧洲文化传统:当社会遭受压迫时,知识分子必须承担起社会良知的角色。
“不管地域国别,东欧的作家共同特点,是在前所未有的制度下,追问人的身份和归属感,包括文化和人性归属。”景凯旋说,地下写作虽然不能包括东欧文学的所有,但最体现东欧知识分子的精神内核。
林贤治旗帜鲜明地表示自己更为关注流亡作家,如波兰的米沃什,匈牙利的凯尔泰斯,罗马尼亚的赫塔·米勒。“因为在他们的作品中,政治,合法暴力,对于人性的扭曲和压抑,比一般的作家表现得更复杂微妙,惊心动魄。”在这几位诺奖获得者中,匈牙利的凯尔泰斯最为典型。有奥斯威辛情结的凯尔泰斯在德国坐过牢,2002年因作品《命运无常》获奖,作为一个内心流亡的知识分子,国人对苦难过去的无视更令他痛苦。凯尔泰斯的系列作品《英国旗》、《命运无常》、《惨败》等从2003年起,由作家出版社引进中国。
“这两年中国知识界开始关注东欧文学,是因为看到了社会和历史背景的相似性。”林贤治说,“凯尔泰斯觉得奥斯威辛是现在的,而不是过去的。赫塔·米勒这些作家看到的苦难对于整个人类历史来说远远还没有过去。诺奖能关注他们,说明人类是有共同命运的。”
林贤治还表示,东欧文学虽然引起了关注,但在出版界仍被视为赔本买卖。很难拿下版权,消费主义盛行,无视深刻和苦难,导致轻松和消解的出版物占大多数。“价值多元往往成为一种逃避的借口,多元只有成为一种大的认识背景的时候,才是多元的。”他说,东欧知识分子的困境,也就是我们和全人类的困境。
(记者 刘雅婧)
(本文根据受访者口述与提供的文字资料撰写而成)
原文地址:http://www.gdwxsj.com/news/2012-3/515279438.html
附:
●雪漠(XueMo)作品专卖:http://shop35991997.taobao.com/
●雪漠(XueMo)墨宝义卖:http://www.xuemo.cn/list.asp?id=89
●《无死的金刚心》卓越网专卖:http://www.amazon.cn/%E6%97%A0%E6%AD%BB%E7%9A%84%E9%87%91%E5%88%9A%E5%BF%83-%E9%9B%AA%E6%BC%A0/dp/B007VX0VSU/ref=sr_1_1?ie=UTF8&qid=1335400266&sr=8-1
●《无死的金刚心》当当网专卖:http://product.dangdang.com/product.aspx?product_id=227269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