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scription:写《野狐岭》是差不多30年前的想法,我一直在积累,慢慢发酵,发酵了30年,很多东西才可能真正地成熟,真正地变成生命的一部分。
《野狐岭》的雪漠:诸多幽魂的载体
文/重庆青年报 记者 冯建龙
百年前,西部最有名的两支骆驼队,在野狐岭失踪了。百年后,“我”遇到了它们的生命记忆,在荒无人烟的大漠深处,收获了27次“生命体会”和“心灵对话”。一个跨越阴阳、南北、正邪、人兽的故事,揭开了序幕……
这是作家雪漠的新作《野狐岭》。在写就“大漠三部曲”和“灵魂三部曲”后,雪漠有数年时间淡出读者视野。在接受重庆青年报记者专访时,他表示,自己不曾离开过,一直坚守在反思西部文明消失的大漠之中。

雪漠,原名陈开红,甘肃武威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甘肃省作协副主席,国家一级作家。主要著作有“大漠三部曲”《大漠祭》、《猎原》、《白虎关》和“灵魂三部曲”《西夏咒》、《西夏的苍狼》、《无死的金刚心》等。现居东莞。
新手法才能完美描绘大自然
◎重庆青年报:《野狐岭》又回到您熟悉的大漠,在手法上是“大漠三部曲”和“灵魂三部曲”二者之上的合体,在思想上是什么样的架构?
●雪漠:写《野狐岭》的时候,我一直在反思仇杀现象,人类历史上发生过那么多著名的的仇杀,如岭南的土客仇杀、西部的回汉仇杀。但是,即使是这样的仇杀,一旦离开当下的经历、当下的环境,就会失去意义。所有的仇杀,只要放进历史的时空,用稍微长远一点的眼光来观照它,就会发现它仅仅是一种情绪,除了给当事人造成巨大痛苦之外,没有任何意义。一直这样反思下去,世界上一切的仇杀、纷争,都会在终极意义上被消解。
不过,我并没有直接在小说中写出这种反思,而是用一种艺术的形式,比如用形象和故事去表现它,描写一种存在,描写我们眼前的世界消失之后的一种存在,描写过去的世界消失之后的一种存在。那存在,是一切都消失之后出现的一种巨大的混沌的可能性。
◎重庆青年报:怎么理解这种“草蛇灰线”笔法?
●雪漠:这种埋伏笔的手法,使小说环环相扣、前后呼应、浑然一体,但又不动声色。通过这种手法,《野狐岭》中埋下了很多机关,有些发动了,有些没有发动。
比如,木鱼妹有个姨我曾经设想过很多关于她的故事,我只写了一点点。还有对沙眉虎的描写,也有很多没有解释清楚的内容,例如他究竟是男是女,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等。
◎重庆青年报:很难想象在那个与世隔绝,生命脆弱之地,人类还有那么多的爱恨情仇和欲望粉墨登场。如此塑造,您想传递怎样的印记?
●雪漠:我更多的其实不是传递,而是展示。《野狐岭》从艺术的角度是创造,对我自己来说则是展示。因为,在我心中,“野狐岭”其实早就活了。
我无法用传统的手法来表达它的这个存在,因为传统的艺术手法不易完美描绘大自然,所以,我不得不用一种新的手法,才能表达我感受到的巨大的世界、巨大的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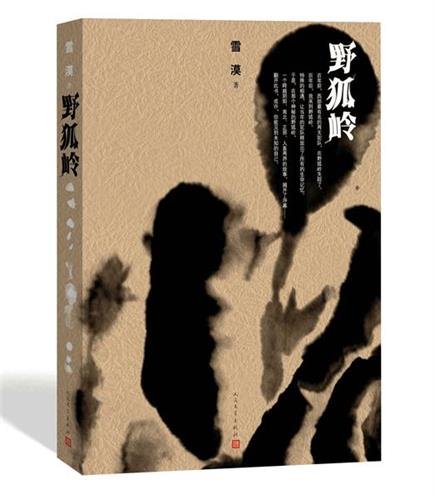
《野狐岭》 雪漠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人性可以展示整个宇宙
◎重庆青年报:您在书中以第一人称介入,“我”是一个神奇的人,有些疯癫,善于臆想,似乎具有超能力。这么设置是否无意中虚化了故事的真实性,对引述的历史背景有所冲击?
●雪漠:真实分为两种:艺术真实和生活真实。《野狐岭》属于后者。我们不能因为吴承恩写了一个神话故事,就觉得《西游记》不真实。同样,我们不能因为《野狐岭》出现了一个独特的“我”,就否认它的真实。在艺术层面,“我”的介入反而是非常真实的,这是心灵的真实、灵魂的真实,这种处理是艺术上的需要,不会显得虚假。
◎重庆青年报:那个“我”与现实中信奉宗教的您有多大联系?写作以来,您体会到了宗教与文学的哪些共通点?
●雪漠:有一定联系。小说中的“我”,在某种程度上,既是另外一个人物,又是雪漠在文学上的另外一种展示。曾经有无数的雪漠,我小说中所有的人物都是我自己,是我自性的流露。人性可以展示整个宇宙,每个人都是宇宙的全息(编者注:全息,是一种利用干涉和衍射原理记录并再现物体真实的三维图像的记录和再现的技术。
宗教对于我来说,既是一种灵魂的滋养,又是一种文学的营养。我对宗教哲学只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关注。
◎重庆青年报:为什么说《野狐岭》是“大漠三部曲”和“灵魂三部曲”的又一个升华,能做个比照解读吗?
●雪漠:“大漠三部曲”以展示一种老百姓的存在和时代的存在为主线,“灵魂三部曲”以描写心灵的向往和追求为主线,而《野狐岭》则将二者糅为一体,在小说形式和心灵层次上,当然也进行了探索。
另外,《野狐岭》显得含蓄,它不是作者想要表达某个主题的产物,反而在尽量地拒绝思想和主题,所以它没有明显的主题,而是在展示一种存在,展示诸多的人物,展示诸多的灵魂。这些人物,共同在展示一种形象,在激活一个世界。
虽然《野狐岭》中也有无数谜团,但总的来说,它既有自由心灵所导致的独特形式,也有接地气的内容,而且将两者结合在一起,所以吸引了批评家的目光。
宗教文化教会我反省
◎重庆青年报:巴尔扎克说:“恶习是瞬息的结局,宗教是毕生的苦楚。”这种意义在“大漠三部曲”和“灵魂三部曲”中,在您反思和内省的时候都有所体现,所以也就显得作品苦大仇深,厚重苍凉?
●雪漠:有道理。“宗教是毕生的苦楚”是巴尔扎克对宗教的理解,不一定错。因为,本质上来说,正是毕生的苦楚催生了宗教。按照佛教的说法,人只有感受到苦,才会向往解脱,才会拥有一种解脱的可能性。所以,我在作品中谈到宗教,但它是解脱意义上的宗教。
◎重庆青年报:泰戈尔说:“宗教就会像财富、荣誉或家族那样,仅仅成为一种人们引以自豪的东西。”你对大手印文化的研究和在文本中的楔入都有尝试,这种不同于常规的文化心理,对写作有哪些裨益?
●雪漠:宗教文化对我的滋养,主要是教会我反省自己,反思自己,追求一种更高意义上的精神,而不是混同于一种世间法的、低层次的、形而下的追求。所以,在小说中就有了一种超越的气息,这是宗教文化带给我的,而不是宗教组织带给我的。释迦牟尼佛说过一个故事:有一天,有个小鬼告诉魔王,有个人证道了,他叫释迦牟尼,魔王对小鬼说,不要怕,我会让它变得制度化。事实上,我不喜欢任何宗教的标签。因为,对我来说,宗教就是人格的修炼,是自己的事情,跟别人没有多大关系。
◎重庆青年报:为什么您的重心一度向宗教文化偏移,或者说一度远离您熟悉的生活、熟悉的叙事场域?
●雪漠:我没有向宗教偏移,对所有文化,我都很感兴趣,不仅仅是宗教文化,也包括希腊哲学等西方哲学,以及各地独有的民俗文化。宗教文化只是我感兴趣的文化之一,我并没有拒绝其他文化。
海德格尔对终极真理的表述,跟道家、禅宗很像,但是他从严格意义上说,不能算是宗教家,而是哲学家。所以,哲学研究到最高境界,也跟宗教文化是一样的。人类文化的最高境界都是殊途同归的,区别仅仅是:有些研究者只是学者,而有些研究者既是学者又是行者。佛教修炼到一定的时候,就会强调一种实践性,强调改变生命的本体,强调改变行为。
西部文化正消失,作家能做的有限
◎重庆青年报:您曾表示,西部大地上的一切都在飞快地消失着,主要指的是什么?一个作家在其中到底能承担什么?
●雪漠:主要指的就是目前的这种农耕文明、农业文明,还有一些地域文化。作家能承担的,就是在它们消失之前,尽量保留一些对人类有用的东西,比如一种文化精神,一种文化营养,等等。不过,能承担固然很好,承担不了也不要紧,作家嘛,力量其实很有限,跟政治家是不能比的。作家只要做好自己,力所能及地做些该做的事情,就已经很好了。
◎重庆青年报:对西部的书写还有哪些可能?目前您在采访什么,下一步有哪些计划?
●雪漠:我写作时会做大量调查,为了熟悉生活。比如,写《野狐岭》是差不多30年前的想法,我一直在积累,慢慢发酵,发酵了30年,很多东西才可能真正地成熟,真正地变成生命的一部分。这时才能让它流淌出来。当然,我也可以编一些东西,但这样味道不对,因为仅仅停留在表层。深层次的东西,需要一个作家用生命去感悟,用生命去体验。
目前,我的采访重点仍然在西部,下一步仍然会写西部。明眼人都可以看得出,我在发生着蜕变,从“大漠三部曲”、“灵魂三部曲”到《野狐岭》,一直在蜕变。在我看来,这种蜕变不是技术上的玩弄,它追求本体的超越。当然,对我来说,这也是一个巨大挑战。如果能实现进一步的升华,我就今生无憾了。
转载:http://www.cqqnb.net/ebook/201432/12929.html 重庆青年报 2014.08.21期